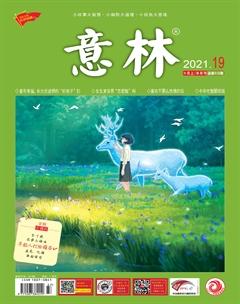草木恩典
草的香,似乎只有在兩個時間可以聞出來。
一是在被碾軋或攔腰斬斷的時候。這時候的草,像是慷慨就義,被鐮刀、被車輪,割斷、碾軋,散發出奇特的生命的香。這香味,讓人覺得有一種拿生命才換得來的美。我追求這種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人是具有動物性的,格外愛這些草木滋味。
另一是在草被熬煮的時候。我的父親是一位中醫,小時候,我常常愛在他的中藥櫥邊轉悠,可以聞到與眾不同的草木香氛。
秋天到了,草木走向成熟,似一個男孩走向青年,一個女孩發育完善。舊時,在鄉間,我喜歡睡在小溪邊的草甸子上,一邊看藍天白云,一邊嚼草根,我覺得,這簡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小時候放羊,我把羊拴在溪邊的小樹上,就往地上一躺,看著羊羔吃奶,母羊反芻;我呢,則效仿羊的樣子,去嘗一嘗草根。
草木的根深深扎進土地,它是最能吸納天地靈氣的,牛羊通過青草來攝取營養,我們再通過牛羊的肉來攝取營養,然后,牛羊和人的糞便又可作為肥料給青草帶去營養。這個循環看起來有些吊詭,實際上,又是多么巧妙的一個輪回。
青草,在這樣一個輪回中,無疑扮演了“雙面人生”。成全人畜,又替人畜打掃垃圾,還這個世界天藍水碧,它們的一生近乎偉大。
我有一位詩人朋友,他有種奇怪的感覺,每次在城市里居住久了,吃得大魚大肉,詩性會逐漸泯滅,寫不出東西。這個時候,他就會到山區的寺院里,找一處周遭長滿茂密樹木的禪房來住,日日食蔬,這樣,就能詩性重返。他說,他獲獎最多的詩作,是寺院里的那些草木和蔬菜給予的。這是何其美妙的草木恩典!
有時候,我實在羨慕那些古人,居住的全部是木材架構的房子,戴的帽子是斗笠,披的是蓑衣,穿的是木屐或草鞋,這樣,才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瀟灑。現如今,你披著滿是塑料味道的雨衣,穿著不透氣的膠鞋,能“任平生”嗎?我不是過激,只是想表達,人一親近草木,就滋生了健康,培育了高雅,構建了和諧。
草木的恩典,也許是它們自己都不知曉的義舉,但,它們一直在做。也多虧了草木的這份堅守、這種任性,才讓我們有機會——食草,刷新自己;聞香,愉悅心智;觀色,養眼醒神。
(本文入選2019年湖北省鄂州市中考,文章有刪減)
李丹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散文集《草木恩典》《胃知的鄉愁》《歲月輕狂,縱步過高崗》 等 26 部,散文集《胃知的鄉愁》 曾榮獲第八屆冰心散文獎等。
《意林》:為什么給文章取這樣一個名字?您覺得草木能給人帶來“恩典”嗎?
李丹崖:與人和動物相比,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最與世無爭的是草木。人在花草前駐足、深思、發呆,哪怕什么都不做,以花草打底來拍張照片,也是動人的。所以說,我認為草木是“恩典”。
《意林》:您想在草木本心之外,透露給讀者以怎樣的精神寄托呢?
李丹崖:芳草碧連天,是自古以來多少人向往的詩和遠方;懷草木心、鮮花意也是很多文人雅士內心修煉的一種境界。在草木之外,還有很多可以提取的心靈寄托,就是從一草一木中尋找自然界的天機意趣,從周遭的斑斕花叢中覓得人性芬芳。
《意林》:您是怎樣構思這篇文章的?和自己的生活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系?
李丹崖:所有寫作都源于生活。我從小在農村生活,花花草草于我,是舊時玩伴。同時,我的父親也是中醫,風干或被炮制以后的草木香氛也令人著迷。我是著眼于生活,從蒔花弄草到割草喂養牲畜,從草木時蔬到中藥之香,不同狀態的草木給人一以貫之的感受,那就是草木本心。這也是這篇文章的靈感,繼而產生了對此文的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