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友似流螢
易禾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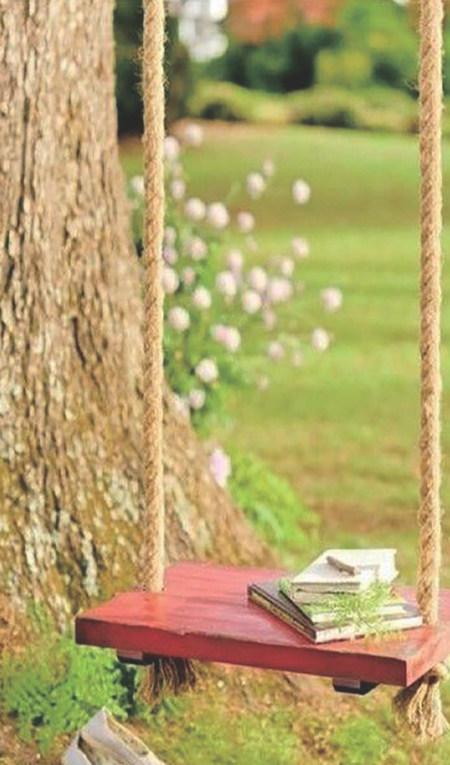
三年前的夏日,友人攜女來京旅游。
幼女牽友人手,怯怯依身后。引她喚人,她促著啟唇,聲若蚊蚋。那一刻,我好似看到二十年前的舊友——
同是盛夏,蟬鳴不絕,你站在老舊校門一側,身旁是一大片野生木槿,開大朵大朵如碗狀的花,枝干足有一人高。你剪齊耳短發,戴印有白色小圓點的紅色發箍,眉微皺,右手不安地捏裙布,捏緊、松開。正值放學,經過的學生無不投以注視,有人漠然,有人竊竊私語,有人起哄戲弄,你將頭埋得更深。
這是一所工人子弟小學,學生們大多相熟。而你的父親從省城來,母親風雨無阻地接送,初來乍到,你大概沒什么朋友,我暗想。
遙遙相忘
我們正式相識緣于我的“行俠仗義”,出聲斥退一名在路上擾你的男生。不記得事隔多久,臨近初一下學期結束,你跑來問我:“放學可不可以一起回家?”你眸如流螢,我猛點頭。那一年,我們十三歲。
熟識后,你溫和好相處,甚是健談。
同路兩年,我們聊深淺心事。你家藏書多,我常管你借。你偏科嚴重,我在路上給你講題。你教我打扮,囑我不要把一套衣服拆開另配,我只不理,頂嘴說“自由搭配也是一種創意風格”。我們議論男生,你喜歡陳浩南,《古惑仔》里的陳浩南。你喜歡夜星,說它們是遙掛的流螢,我便嗤笑。
中考結束,我考進市一中,你聽從父親安排赴省城讀中專,學幼師專業。我想未來當幼師也許很適合你,給稚童講你的“原創故事”。
初去省城,你每周必寄來一封信。你說省城五顏六色的屋頂,像動畫片里的城堡。我從題海中抬頭讀信,撲哧一樂,想起你一激動便手舞足蹈的模樣。
回什么呢?筆懸半空,總是難續。我的生活乏善可陳,上課、下課、做題,再無其他。有時也聊起疲累發酸的校園生活:我的未來在哪兒,會考去哪里?讀什么專業,從事什么工作?那里也有如你筆下畫就的五彩屋頂么?
不知從哪一天起,你的信漸少,而我們從哪一天開始疏遠。我不止一次想過,卻不敢開口。
你舉家搬至省城,小城你再不回。小學門外大片大片的木槿已被修成規整的綠化帶。我們往日回家踩踏的土路已鋪上水泥。
記得那時,你約我高考完去省城玩,提前感受大學校園的氣息。我總是一應再應,但未動身。等來大學錄取通知書,我向你道別:遺憾,去不了省城,我要去北方了。
你發來一大段祝福,我將鼠標移至輸入框,推敲良久,留下簡潔的“好的謝謝,你也是”。
幾年未見,時光幻作河流。年少的我們已站在遙遙相望的兩岸。
我們鮮有聯系。我從你的朋友圈獲知:你從幼師畢業,順利進入幼兒園實習。聽從父親建議,邊工作邊讀本科提升學歷。再之后經人介紹結婚。每一步行得踏實穩當。看你上傳到網絡空間的結婚照,長發披肩,是小時文靜溫柔的模樣。“新婚快樂!”我寫下庸常留言。
我在外打拼多年,三十有余仍未成家。你問是否需要幫忙留意適齡男生,又怕友誼已生疏,緊補一句“自己過得開心也很好”。
我們確如兩株樹木,越往后越呈不同樣貌,我是巖上瘦松,你是門前佳槐。
久別重逢
前些年春節,你總來問探親是否在省城轉車,“我們好多年沒見了,找個時間聚聚吧!”我不無抱憾實則婉拒:“是啊,確實很久了,春運的票太難買。來日方長,再約再約。”
這一約,直到你攜女來京,說趁暑假帶孩子來北京旅游。少時伙伴,理應接待。
別后再見也需勇氣。你坐定看我,未語先笑:老樣子,沒怎么變。我笑笑,趁勢捋順額發。
我怕冷場,在來的路上,已暗自擬好聊天提綱。父母身體可好,他們都退休了吧?工作累不累,當幼教挺操心吧?孩子很乖,平時很聽話吧……
你極少問我,只說別太忙,注意身體。我們沒有談過去,倒聊起頭條新聞、養生保健、網絡八卦,熱絡又生疏。
飯畢,你提議:照個相吧!我猛然察覺出門太急,穿的還是公司的文化衫,頭發胡亂扎個馬尾,不禁苦笑。你會意地點頭,遂張開臂,用夸張的話劇腔調說:那——親愛的,抱一個吧!
此時的你像舊日校門口盛放的木槿,不再拘謹瘦弱。我咧開嘴打著哈哈上前,恍若少時結伴回家在路上打鬧。
淚似乎將盈滿眼眶,你的小女兒忽然指著向南的天空:“媽媽,星星好亮!小時候你騙我是螢火蟲掛上去的。”
我們同時抬頭,晚八點的天空,看得見溫軟的云朵與淺淡的微藍,一星遙掛。
那一刻,我們同望天空,倏而互望,驀地感動。此刻一如年少,眼眸天真,足以填滿別后二十載的空白光陰。
少年相識又別離。誰會料到性情迥異的我們會成為朋友?誰又料到二十年后,他鄉重逢,我們仍有如此意趣,同望一顆微星。
三毛談待友時說:“該來的朋友,時間到了自然而來,該去的朋友,勉強得如果吃力,不如算了。抱著這種無為而治的心情去對待人際關系是再好不過。不執著于任何人事,反倒放心……”
何為“該去的朋友”?是否是鮮有往來,不再交匯的老友?漸行漸遠之后,那些念念的過往依然成為當下生活的草蛇灰線。那時我們彼此懂得,然后你成為你,我成為我。
重逢那天,我在日記里這樣寫:“謝謝你出現在我的少年、青年。過往與友誼都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