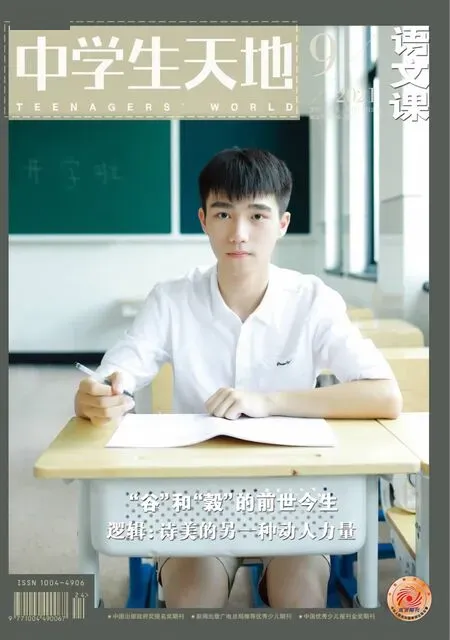邏輯:詩美的另一種動人力量
金華市湯溪高級中學 楊建華

圖/榆木先生
戲答元珍
宋 歐陽修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這是宋代文學大家歐陽修的名作。其中頸聯有不同版本:“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一作“鳥聲漸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現代通行本大多采用“夜聞”說。愛琢磨的讀者朋友可能會產生疑問:兩種表達究竟孰優孰劣?為什么多數版本會采用“夜聞”說?
經過仔細欣賞,詩心細膩、敏銳的朋友可能會感覺到“夜聞”聯在詩中的突兀。時間變化突兀,這是其一。詩歌首聯、頷聯寫詩人看到殘雪壓橘、聽到凍雷催筍,所見所聞都是日間情景,尾聯則根據日間情景生發聯想,表示無須感嘆山城野花開放太晚;而“夜聞”句突然竄入夜間景物描寫,給人以生澀不自然,甚至硬湊不倫的感覺。“病入”句,“新年”與前述“二月”也未免有點小小的齟齬。情感銜接突兀,這是其二。本詩是作者貶謫峽州夷陵縣令后次年(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春所作。首聯寫謫居的山城荒僻冷落,暗點自己遭貶謫后的寂寞情懷和迷惘心境。頷聯寫自己感知殘雪、凍雷中孕育的生機。尾聯據此寬慰自解,表明山城野花雖晚,但自己堅信美好必至、前景可期、無須嗟嘆之意。全詩感情先抑后揚,低開高走,走勢明朗。但“夜聞”“病入”兩句,破空插入思鄉、嘆病等低沉情緒,整個情感流向為之一抑,讓人措手不及——讀詩至此,讀者會覺氣息一窒。詩歌情感豐富多元、曲折變化,本是詩歌藝術水平較高的表現,但在具體表達中,情感不能“平地生波”,或切斷、阻絕全詩內在的情緒流或情感流。“夜聞”兩句,恰好有這樣的嫌疑。
反觀“鳥聲”聯,其內容與前后文緊密勾連,表達情感也自然符合情理。“鳥聲漸變”緊承“凍雷驚筍”,讓人感知山城雖還在春寒料峭中,春意未明,但春天正在堅實地一步一步走近,從而自然引起尾聯中“野芳雖晚不須嗟”的議論。同時,“知”字照應首聯“疑”字。從“疑”春風不到天涯,到“知”美好時節漸至、必至,既是詩人對山城春天特點的認識過程,也是詩人對自己人生、情感的體悟過程,過程展開水到渠成,貼切自然。而“人意無聊感物華”句,它的內在邏輯也較“病入新年感物華”更加嚴密:貶謫山城,公事輕簡,在百無聊賴中更易感知外界事物的變化和外在景物的美好。當然,從詩歌藝術角度看,“鳥聲”聯似乎也略有不足,句中的“芳”字與尾聯的“芳”字微有相犯之嫌。
《戲答元珍》頸聯的版本差異存在已久,有人斷定,“夜聞”聯的選擇是歐陽修自己的“手筆”。假如確乎如此,這個事例倒是可以作為洪亮吉“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北江詩話》卷二)的一個論據。歐陽修“不善評詩”在學界不是秘密,洪亮吉就舉例說他“自詡”極高的“《廬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屬中下”;而錢鍾書在選宋詩時,也不認可歐陽修的評詩,直言不諱,“他還有幾首極自負的作品,這里都沒有選”。當然,我們在這里并不是要討論歐陽修鑒賞詩歌的水平,也不是要評價歐陽修詩歌的藝術水準,而是想借此梳理出一個值得注意的詩歌鑒賞原則:賞析詩歌時,要關注作品的內在邏輯。情感邏輯綿密,事理邏輯嚴密,才能較好地彰顯詩美,體現詩歌的藝術性。
有的讀者朋友會疑惑,詩歌是留白的藝術,講究情感發散,追求思維跳躍,我們欣賞詩歌注重探究其內在邏輯,是不是“倒行逆施”或者“緣木求魚”了?其實,詩歌因思維跳躍、想象空間廣闊產生詩美或藝術性,是以其敘述或感情符合內在邏輯為前提的。富有邏輯的表達,往往更能打動讀者。我們以《離騷》選段為例來說明。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詩中的表達表面上似乎散漫無羈,有如天馬行空,不著邊際,但其實卻有著非常嚴謹的行文思路。詩人因朝取木蘭、夕采宿莽(草名),而感知日夜更替,時光匆促;又因日夜更替進一步聯想到季節流轉;因季節流轉而有草木凋零,因草木零落念及人生短暫而擔心美人遲暮;因擔心美人遲暮而建議美人趁著年少自圖修潔,并自薦甘為導引。整段文字語意連貫,句子銜接緊密,可以說是一氣呵成。其語言表達雖然極盡浪漫想象之能事,但內里卻有一種強大的邏輯。這一邏輯使得上述選段除了擁有以情動人的效果外,還額外增加了以理動人的魅力,使詩歌得以向更高的境界邁進。
邏輯能增加或放大詩歌的動人力量。我們從歌曲《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歌詞修改中得到佐證。這首歌作為1960年中國香港電影《苦兒流浪記》的主題曲,感動了無數聽眾。其歌詞如下: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塊寶,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沒有媽媽最苦惱,沒媽的孩子像根草,離開媽媽的懷抱,幸福哪里找?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不知道。要是他知道,夢里也會笑!
時光荏苒,到了1989年,內地上映 《媽媽再愛我一次》,《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旋律再次響起。曲還是那首曲,詞卻精簡成了這樣: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塊寶,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根草,離開媽媽的懷抱,幸福哪里找?
聽過兩個版本歌曲的聽眾,眾口一詞,都認為后者更加感人。原因何在?后者的邏輯更加清晰、嚴密!
根據上面所述,我們想對愛好詩歌的朋友做個溫馨提示:欣賞詩歌時,除了重點關注詩歌的意象運用、手法選擇、感情表達之外,還應適當關注一下詩歌內在的邏輯。在閱讀律詩時,除了要關注上文所述的情感邏輯、事理邏輯,還要特別注意它的結構邏輯。律詩的寫作有一定的范式,它的四聯安排一般需滿足“起、承、轉、合”這一結構。下面我們小試牛刀,看看能否梳理王安石《葛溪驛》的寫作思路。
葛溪驛
宋 王安石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
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
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涼。
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