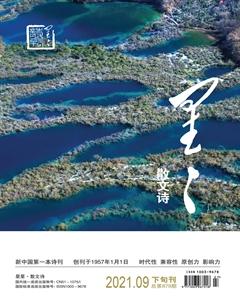白龍江畔(組章)
阿垅
源 頭
多像一個人,一條大江也有名有姓。
多像一個人,一條大江的姓氏也會粘連著它的祖籍。
無論荒蕪、清冷和孤寂,一旦提起定會心生暖意。
夢想總是美好的開始,有時是一根繩索,有時是一束光。
千里迢迢的牽掛,可以倒敘、追憶,帶來永無止境的啟示和召喚。
這樣的場景過目,就會有淚濕了衣襟。
這樣的場景,嵌入了生死之間的輪回——
每個人的身上都有一個留住鄉音的村口,那里大樹參天,落葉滿地,一個老人走了,又一個老人緩緩坐下來,在一塊磨光的石頭上,替補時光的空白。
那逆流而上張望的神情,保持著相同不變的姿勢……
馬掌鋪
還記得,那個吸著鼻涕的小男孩,癡迷于叮叮當當的敲擊聲。
還記得,落滿灰塵的風箱、燒旺的土爐,漫天的火星飛濺,又一次灼傷了千瘡百孔的麻布圍裙。
不打別的,專打馬掌。
他埋下頭,多像暗夜里披著火光的神祇,將一塊鐵板從生打到熟,將一條條泥濘、冰雪和孤單的路打進去。
現在,主人已不在。
一個簡陋的遺址,破敗不堪。
如能回到從前,我定會討要幾副,給身體里那些日益懶惰和頹廢的馬穿上鐵制的鞋子。
麗莎咖啡屋
咖啡屋與女主人的年齡和容貌無關,但與她好聽的名字有關。
在郎木寺鎮,因為只此一家,沒有第二。紛至沓來的游客,會踩響小街的石板路面,準確無誤地找尋到這個散發著異國情調的地址。
門口白樺制作的招牌有些發黃,風吹日曬的痕跡像淡淡的插花。
室內的擺設簡單又雅致,木質桌椅攜有大自然的情愫,餐盤刀叉折射出誘人的光亮。休憩當中的留言、小面值的紙幣,以不同的文字和筆跡發音,參差不齊地貼滿了兩面墻壁。
除了咖啡,還有蘋果派、豪牛肉漢堡、巧克力開開等必備的西餐,還有英、法、德、俄、日五國日常交流的語言,那是她十多年來以聰慧一點一滴、日積月累的手藝和財富。
倚著木窗,穿過雨霧的遮簾,看清新的草地、悠閑散步的馬、寺院的白塔,聆聽遠處隱約的鐘聲和流水,咖啡的焦苦留在舌尖,那是怎樣的一種心境和滋味?
美國傳教士羅伯特·埃克瓦爾也曾到過這里,以理想與現實、夢境與真實碰撞的筆墨,寫下了風靡一時的《西藏的地平線》,相信打動了許多不安分的人們,嘗試著開始新的旅途。
但那時還沒有這個咖啡屋,麗莎還沒有在臨潭縣的一個家庭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