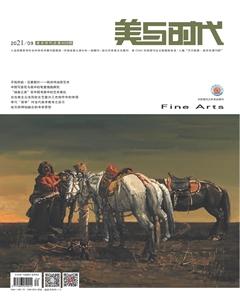出位之思的藝術創作方法研究
劉寶蘭


摘 要:“出位之思”源于錢鐘書對德語Andersstreben的翻譯,指藝術間相互交流、借鑒的藝術現象。同時這一概念也是符號學理論中的重要構成。但結合近年來國內外藝術家的創作發現,出位之思不僅僅是符號學的理論知識,還可以作為藝術創作的方法論來指導藝術創作。基于此,通過對出位之思創作概念的辨析與歸納,以期在藝術創作中提供一個較為新穎的觀察視角,為藝術創作提供新的指導方法。
關鍵詞:出位之思;媒介材料;藝術創作
目前當代藝術發展迅猛,各藝術體裁、媒介材料之間的壁壘在藝術的發展與變革中不斷被打破。而在求新求變的藝術創作氛圍下,涌現了大量優秀的藝術家,亦有著大量獨特的藝術語言和創作方法不斷被挖掘。在藝術的發展中,思維和觀念在作品中的體現必然需要相應的媒介為載體。因此,藝術創作媒介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的媒介之間也相互滲透、相互關聯,像電影這門藝術就融合了影像、音樂、繪畫、文學等媒介。
一、從康定斯基看出位之思
繪畫也可以有“音樂性”。許多杰出的畫家把色彩與聲音相互比擬,認為色彩與聲音一樣可以給人以激動、柔和、歡快和悲哀等感覺。康定斯基的藝術主張是“畫”音樂,他認為色彩和聲音、線條與節拍的韻律之間邏輯相似。其作品《構成第八號》(圖1),主要由點、線、面等元素構成。其中每一個大小不一的點都會產生不同效果的音律變化,不同寬度、銳度的線可以表示樂器的高低音與聲音的強與弱,面的分布可以想象成一個個音樂片段。點構成線,線又組成了面,作品中充滿著點、線、面的“交叉回響”。畫家保羅·克利同樣愛好音樂,在包豪斯學院任教時,常常借用音樂“旋律”授課。后人曾把他的繪畫作品與莫扎特的歌劇《魔笛》(夜后詠嘆調)相結合,展示于法國波爾多,通過現代媒體呈現出音樂與色彩交相輝映的藝術效果。
另一位抽象大師蒙德里安的繪畫作品《百老匯爵士樂》直接用音樂命名,其以顏色為主要構成,由大量的黃色為主,少量的紅色和藍色為輔。這種色彩帶給視覺的快感,就像音樂給聽覺以快感一樣,營造出了極強的節奏變換。節奏不只是音樂的概念,在繪畫藝術中也經常被用來表達對畫面的感受。
試圖在繪畫中采用特殊的構成形式以達到一種音樂效果與出位之思的藝術追求相吻合。趙毅衡在《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中指出,出位之思是任何藝術體裁中都可能有的對另一種體裁的仰慕,是在一種體裁內模仿另一種體裁效果的努力,是一種風格追求。佩特把出位之思定義為藝術部分擺脫自身局限的傾向。為此,本文從藝術部分擺脫自身局限的角度出發,探索出位之思的藝術創作方法。
二、藝術體裁與出位之思
音樂對繪畫有著同樣的仰慕。繪畫作品中的節奏的變化,就像音樂中的不同節拍。在色彩音樂的發展中,亞歷山大·拉茲羅進行了大膽的實踐,他把音樂和現代媒體相結合,發明出了色彩鋼琴,它能在演奏過程中投射彩色圖像來配合音樂,達到聽覺與視覺相互交融的藝術效果。他的著作《彩色光線-音樂》對后世音樂與色彩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拉茲羅在音樂中追求色彩的視覺體驗,正是音樂對繪畫的“出位之思”。
藝術間相互交融、模仿的現象,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得以體現。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畫派畫家喬爾喬內曾與一些雕塑家發生過爭論,爭論的內容是繪畫與雕塑這兩種造型藝術在表達方面的優劣問題。英國思想史研究者彼得·沃森也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一書中提出:到底是繪畫高于雕塑還是雕塑高于繪畫?眾所周知,14世紀之前的繪畫與雕塑不同,繪畫是趨于平面的,而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喬托最早開始用明暗來表現立體的空間感,進行透視的探索,直到達·芬奇時,科學透視法正式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繪畫與雕塑之爭使畫家不僅突破了傳統繪畫的觀看方式與思維模式,還發明了科學的透視法則,讓二維平面的繪畫呈現出三維的立體效果,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
繪畫在模仿雕塑,是否也存在雕塑模仿繪畫的藝術現象呢?格林伯格把“新雕塑”定義為繪畫式雕塑。格林伯格認為,現代主義的感受力盡管拒斥任何種類的雕塑式繪畫,卻允許雕塑成為它想成為的繪畫。在這里,由于雕塑這種媒介獨一無二的具體性和真實性,禁止一種藝術進入另一種藝術領域這一點就被懸擱了。雕塑可以將自己限定在二維的平面上(就像大衛·史密斯的某些作品那樣),而不需要感到跨越了其媒介的界限,因為眼睛能夠識別二維平面中所提供的東西(事實上呈現出三維的樣子)。由此可見,雕塑正是通過強化線條進而模仿繪畫的。“新雕塑”將作品呈現在二維平面上,突破了傳統雕塑的限制。
出位之思的藝術追求不僅出現在西方藝術中,早在中國的北宋時期就有所體現。蘇軾曾這樣評價王維:“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文人畫的出位之思體現了詩與畫的融合,畫家通過削弱畫面的線條、色彩、明暗等忠實再現客觀事物的因素,使畫面疏簡而富含意趣,趨向表現,從而達到“畫中有詩”的藝術效果。
而詩情畫意不僅體現在文人畫上,還多次用于建筑中。如杭州市富陽區東梓關村的設計,房頂與墻面形成了強烈的灰與白、線與面的對比關系,徽派建筑中的留白與極簡主義的審美主張在其建筑物中大膽呈現,使其表現出了江南地域的傳統建筑韻味,亦符合當下時代的審美潮流。
三、媒介材料與出位之思
出位之思的創作方法在媒介材料上同樣適用。在傳統觀念中紙本材料作為繪畫的載體,一張空白的紙就是二維空間,而當紙張變為三維立體時,則呈現出紙本材料對自身特征和用途的跨越,即“跨媒材”。“跨媒材”審美既是對創作思維方式的革新,還帶給藝術家全新的藝術體驗。在《我的玫瑰》作品中,林延就將紙張層層折疊變幻成玫瑰的造型,使得原本平面的紙張變得有空間感。這使紙張突破了平面的限制,成為有真實空間的實體。總之,在保持紙張本身特征的同時,林延試圖模仿雕塑的空間感。在這里,“跨媒材”創作不單單是二維平面對三維立體的仰慕和模仿,其實質是紙本材料對雕塑材料的出位之思。由此可見,出位之思不僅體現在藝術體裁中,還經常作用在不同媒介材料上,起到突破材料限制的作用。
藝術家胡偉在他的“海礁”系列作品中,廣泛地使用宣紙。他把宣紙和纖維混在一起碾壓,再經過土質顏料、水與金屬渣的混合浸泡,利用宣紙柔軟、易產生不同肌理質感的特性,把原本輕薄的宣紙制作成金屬般的厚重感。這樣既保留了紙張的松弛與形狀的多變,同時又有金屬般的堅硬和做舊,這種創作方法就是宣紙材料對金屬材料的出位之思。
報紙是藝術家王雷創作的主要材料,他以報紙為原材,用紙搓成“線”,再由“線”去編織“堅固鎧甲”。王雷的《兵者無形》(圖2)中鎧甲象征著英雄,英雄被符號化了。由無數英雄事跡堆砌成英雄的具象,那么這是真實的英雄還是被塑造而成的英雄呢?紙張會消逝,英雄也不知所蹤,一切歷史都會成為過眼云煙,只剩下一具空殼鎧甲,似乎還在傳承著不屈的精神和英雄的遺志。報紙對編織材料的仿制而制成的織物材料與金屬材料屬性的矛盾對比,形成了多元的指向和隱喻。
四、結語
不難發現,在藝術創作中,藝術家們經常使用“出位之思”的創作方法,在遵循原本體裁、媒介材料特征的同時,還追求另一種體裁、媒介材料的藝術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藝術創作中,媒介材料一直作為創作中的手段和工具隱藏在畫面中,而在材料藝術中,媒介材料從“幕后”走上“舞臺”,功能身份從原先的透明媒介轉化為語言主體,其自身的語言價值得以突破。
出位之思作為藝術創作方法,不僅提供了跨體裁、跨媒介材料的思維方式,而且打破了體裁、媒介材料之間的界限,為當代藝術創作開啟了新世界的大門。
參考文獻:
[1]龍迪勇.“出位之思”與跨媒介敘事[J].文藝理論研究,2019(3):184-196.
[2]潘建偉.論藝術的“出位之思”:從錢仲書《中國詩與中國畫》的結論談起[J].文學評論,2020(5):216-224.
[3]張天佐.物的詩意:當代綜合材料繪畫的物質語言嬗變[J].美術觀察,2019(12):70-71.
[4]康定斯基.論藝術里的精神[M].呂澎,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
[5]格林伯格.藝術與文化[M].沈語冰,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6]弗萊.羅杰藝術批評文選[M].沈語冰,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7]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
海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