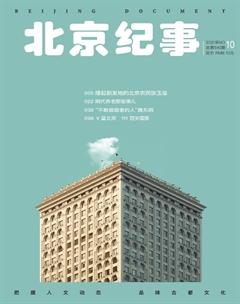糧店的記憶
何羿翯
小時候,離我家不遠處,有一家糧店。糧店,顧名思義是賣糧食的地方,現在糧店在北京已經絕跡了,然而,我對它的記憶還在。
記得小時候,我常跟著奶奶去糧店買糧食。印象中,那時候糧店只賣大米、白面和棒子面,小米、高粱米這些粗糧沒有。偶爾帶賣散裝的食用油,有菜籽油、豆油和花生油。這三種油可不是常有,不能隨時供人們挑選,而是趕上什么是什么。那時候可不像現在,人們只有被動選擇的份兒,哪有隨心挑選的自由。糧店物品種類雖然少,那我也愿意出去跟著跑一趟。
過去在糧店買糧食得用糧票。我印象中的糧票比郵票長,是長方形的,也像郵票一樣,周圍有鋸齒,因為得撕著用。糧票的顏色有紅的、綠的、藍的、淺粉等;面值有一兩的、二兩的、半斤的、一斤的、五斤的、十斤的、二十斤的。糧票分全國和地方兩種,全國糧票就是全國通用,地方糧票相當于市級的,在本地區內通用。糧票還分粗糧和細糧,買米和玉米面算粗糧,買面算細糧。糧票是每人定量供應,根據個人的工作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核發的數量也不同。比如煉鋼廠的工人一月糧票有45斤的;醫療衛生行業有32斤一月的,其中按摩科、骨科醫生的糧票數會高一些;家庭婦女每月是28斤。
糧票是每月發放一次,一般是在本月25號左右發放下月糧票,當月糧票只在當月有效。那時候家里人口比較多,不少人家的糧票都不夠用,有的人家就去糧店或是辦事處,用下月的糧票換當月的糧票花,等于是提前支出,一個月壓一個月的。糧票花不完的現象很少,偶爾有當月沒用完的,肯定不能浪費,就得想辦法調劑。
我還趕上過用糧票,只不過是個尾聲。后來物資豐富一些,糧票不那么緊俏,可是還有用。記得家長用錢搭糧票換過不少東西,一開始是三斤糧票換一斤雞蛋,后來是四斤糧票換一斤。活雞是13斤到15斤糧票不等,一般母雞貴點,公雞便宜,與現在的行市正相反。
每次買了米或面,稱完了,就會看到家人用從家里帶去的米口袋或者面袋子罩在漏斗的底部,售貨員在柜臺里面問:“好了沒有?”買主要是說行了,米或者面就順著漏斗,進到了口袋里。要是買米就能聽到唰唰唰,大米在漏斗里下滑的聲音;面就會安靜不少,直接落到口袋中。
回家后,奶奶會把米和面分別倒在兩個缸里。我還記得,我家的面缸就放在操作間外面的臺階上,上面還蓋著一個蓋簾。上小學之前,米缸面缸對我來說有點大,我從來不碰,也就是去糧店買米買面時,才有機會碰到散米散面。到了二年級左右,我知道了面缸的位置,也能搬動上面的東西,偶爾會偷偷從面缸里抓一點面,接點水,捏一些小面人玩。
在20世紀80年代,糧食還是限量供應的,要憑糧票憑本購買,一戶幾斤。那時候要是能認識個在糧店工作的人,可是太幸福了,只有認識人才可以多買不少好東西。平時家里都吃機米,有一毛五分二一斤的,還有一毛六分一一斤的。最好的大米兩毛零五分一斤,得憑本購買,還得看供應情況,一般一家只能買二三十斤。但要是糧店有熟人,就能多買點。
我還記得上小學的時候,食堂吃的就是機米,比家里吃的米,粒長,蒸出來的飯松散不成團。回來跟奶奶報告:“學校吃的米粒大,還是一粒一粒的不成飯團。”后來我才知道,那是機米,沒有油性,不如家里的米好。過去百姓家里吃的面都是標準粉,也叫“八五粉”,這種面粉顏色發暗。富強粉顏色發白,吃著筋道,甭管做什么吃食,有咬頭,但是不經常有。
印象中,糧店應該是在我小學還沒畢業就消失了,因為上了初中,就有超市了。超市物品琳瑯滿目,價格相對便宜,關鍵是什么物品都在貨架上,等著消費者隨意挑選。而這個現象的根源是,改革開放以后,取消了統購統銷,后來又取消了糧票,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糧油及物品供應市場化了。這時每家每戶習慣從超市挑選、購買成袋的米和面粉。再后來,超市里還有了五谷自選稱重區,不光有大米、小米,還有各種豆類、雜糧,糧食的種類越來越多。
現如今,不光是超市糧食種類齊全,自由市場里,賣糧食的小攤販都有不下20種商品:江米、薏米、大麥米、紫米、紅豆、蕓豆、黑豆……物資真是豐富,連玉米面都能分為粗細兩種。小販們也懂得大家健康養生的需求,會在薏米下面寫著“除濕”,黑豆下面寫著“補氣”,每種糧食下面都標注著功效,好像我們買的吃的不再是糧食而是營養和健康。
現在不僅糧食種類多,運輸也發達,我們能親自挑選來自各地的物產。還可以通過網購、微商等多種渠道,買到當地的特色食品,比如我們能吃到山西的小米,四川的黍麥……看來,時代發展了,計劃經濟的產物之一糧店也只能存在于我的記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