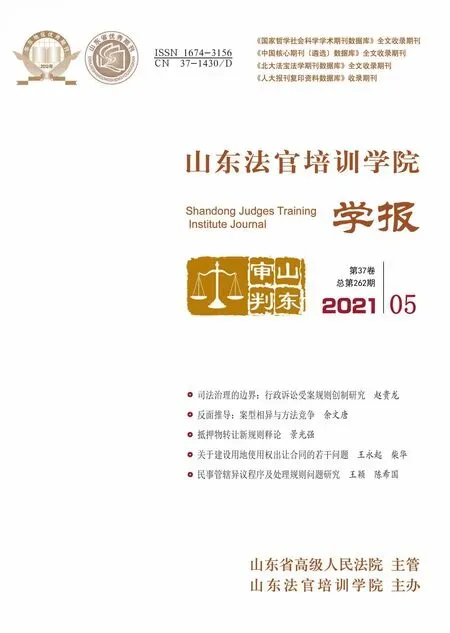論行政非訴不予執行裁定對行政機關的效力
韓利楠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97條和《行政強制法》第53條的規定,行政相對人在法定期限內,既不申請復議、也不提起行政訴訟又不履行行政行為,且行政機關自身不具有強制執行權時,行政行為的實現主要依靠行政機關申請法院執行,即學理上的行政非訴執行制度。此時法院的裁定決定著行政行為能否實現。當行政行為存在“三明顯”或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情形時,法院應裁定不予執行。①參見《行政強制法》第58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8〕1號)第161條。但若違法狀態繼續存在并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或公共利益,應如何救濟第三人或維護公共利益?通常而言,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后,若利害關系人未在法定期限內提出復議或訴訟,該行為原則上不得隨意改變,行政機關也無需就同一事項再次作出行政行為。①參見王運生訴西安市灞橋區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職責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4294號行政裁定書。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是否應負有相應的后續義務?實務中,有法院認為,行政機關應當負有后續處理的義務,②參見廣州市白云區人民檢察院訴廣州市國土資源和規劃委員會不履行職責案,廣州鐵路運輸第一法院(2017)粵7101行初252號行政判決書;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檢察院訴武漢市國土資源和規劃局不履行查處違法用地法定職責公益訴訟案,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法院(2018)鄂0107行初144號行政判決書。也有法院持相反觀點。③參見張禮亭訴濱州市國土資源局濱城分局、濱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職責及行政復議案,山東省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魯16行終43號行政判決書;朱德廣訴鹽城市大豐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不履行法定職責案,江蘇省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蘇09行終496號行政判決書。學理上,雖有學者討論了不予執行裁定對行政行為的效力,④相關討論參見信春鷹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93頁;向忠誠、鄧輝輝:《非訴行政執行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198頁;黃學賢:《非訴行政執行制度若干問題探討》,載《行政法學研究》2014年第4期。但關于不予執行裁定對行政機關的效力則少有關注。
不予執行裁定是否會引發行政機關的后續義務實則涉及司法裁判對于行政機關的效力,我國臺灣地區及日本行政訴訟中判決的拘束力可資借鑒。本文擬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研究,嘗試借鑒行政判決拘束力的理論,將該問題歸為不予執行裁定對行政機關產生的拘束力,通過證成并展開,以期引起理論和實踐的關注,促進行政非訴執行制度的有效落實。
二、拘束力的內容及功能
《行政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未明確規定法院裁判的拘束力,⑤雖然《行政訴訟法》第94條規定了當事人必須履行生效裁判,但考慮到這一條款規定在“執行”章中,其更多是對裁判執行力的規定,而非拘束力的肯定。另外,第71條所規定的重作判決與拘束力有相近之處,但其他判決是否具有拘束力仍留有疑問,因而也不適宜將其視作拘束力的法律依據。因此有必要首先從學理上對拘束力的內容和功能做一介紹。
(一)拘束力的內容
目前行政訴訟法學界關于拘束力的涵義存在幾種不同的理解,具體而言,行政判決的拘束力約束當事人、法院和其他主體,⑥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6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12頁;趙清林、彭代兵:《預防性行政訴訟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162頁。約束法院,⑦參見梁鳳云:《行政訴訟判決研究》,中國政法大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田勇軍:《論行政判決之既判力——以與民事判決既判力比較為視角》,載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頁。約束當事人,⑧參見楊建順:《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拘束力》,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9月16日,第3版。值得注意的是該學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認為行政訴訟判決的拘束力是指“行政訴訟判決的內容必須得到尊重,關于該案件的判決內容必須得以遵守,當事人等負有按照該判決采取行動的義務的效力”。一個“等”字似乎將拘束力的對象進行了擴張。參見楊建順:《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既判力》,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約束相關行政機關。⑨參見應松年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詞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19頁;王貴松:《行政訴訟判決對行政機關的拘束力——以撤銷判決為中心》,載《清華法學》2017年第4期。此處主要在約束相關行政機關層面使用“拘束力”一詞,拘束力是指行政判決所具有的要求案件相關行政機關尊重法院判決意旨采取行動的效力,包括禁止反復的消極效力和重新處理的積極效力。
1.消極效力:禁止反復
拘束力的禁止反復效力是指法院作出判決尤其是撤銷判決后,禁止相關行政機關依據同一事實理由作出與原行政行為相同的行為,這也是拘束力的消極內容,我國《行政訴訟法》第71條所規定的重作判決與此處拘束力的消極效力具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外,現行立法并未規定其他行政判決的拘束力。那么應如何理解行政判決拘束力的禁止反復效力?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8〕1號)(以下簡稱《行訴解釋》)第90條第1款的規定,禁止反復效力所規定的事實和理由,應當是主要事實和主要理由,而非不影響案件定性和處理結果的枝節性事實和理由。①參見王貴松:《行政訴訟判決對行政機關的拘束力——以撤銷判決為中心》,載《清華法學》2017年第4期。實踐中也有法院持此觀點,如湖北福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訴國家稅務總局云夢縣稅務局稅務行政處罰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鄂行申357號行政裁定書。同時結合與原行政行為相同的行為這一要件,此處該效力所禁止的行為,應當是與行政行為實體上相同的行為。另根據《行訴解釋》第90條第2款的規定,若法院以程序違法為由作出撤銷判決,行政機關后續以同一事實和理由,但適用不同的程序,也不違反禁止反復的效力。簡言之,此處禁止反復效力包括兩層內容:一是對于法院因實體問題而作出的行政判決,行政機關后續不得依據同一主要事實和理由,對同一相對人作出與原行政行為相同的行為;二是針對法院因程序問題所作出的行政判決,行政機關后續可依據同一事實和理由,但適用不同的程序作出與原行政行為相同的行為
2.積極效力:重新處理
除禁止行政機關在行政判決生效后,依據同一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行政行為相同的行為外,為保證行政判決的實效與爭議的解決,相關行政機關還負有對相關行政行為重新檢討并作出處理的義務。有觀點將其稱之為“不整合處分(關連處分)之調整義務”②賴恒盈:《行政訴訟裁判拘束力之研究》,載《臺灣本土法學雜志》第103期(2008年)。,這也是行政判決拘束力的積極效力。此處相關行政機關不僅包括作為案件當事人的行政機關,還包括與案涉行政行為有關的行政機關。
一方面,作為案件當事人的行政機關重新處理案涉行政行為的情況,具體又可區分為依職權行政行為的重新處理和依申請行政行為的重新處理。針對依職權的行政行為,法院作出撤銷判決或確認無效判決,若違法狀態依舊存在且行政機關對該事項具有法定權限時,其應當負有主動消除違法狀態、重新處理的義務。這不僅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司法權監督行政權的體現。針對依申請的行政行為,若行政機關對該申請作出拒絕或駁回決定,在此情況下,由于拒絕或駁回決定并不改變法律關系的現狀,此類行政行為被撤銷或被確認無效后,回到了相對人提出申請而行政機關尚未對其進行審查的狀態。①參見王天華:《行政訴訟的構造:日本行政訴訟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頁。此時相對人的申請依舊存在,行政機關應服從判決,對相對人申請的事項重新審查并作出處理。
另一方面,其他相關行政機關重新審視與行政判決相關聯的行政行為系指法院作出相關行政判決后,行政機關對于與該判決中行政行為相關的其他行政行為,比如與案涉行政行為具有共同實體要件、存在違法性繼承關系或有表里關系等的行政行為,②參見王貴松:《行政訴訟判決對行政機關的拘束力——以撤銷判決為中心》,載《清華法學》2017年第4期。負有重新審查這類行政行為是否與判決相抵觸的義務。對于相抵觸的行政行為,行政機關應予以主動撤銷,以消除違法狀態。原則上,行政判決拘束力的主觀范圍應僅及于作為案件當事人的行政機關,而不應擴張至案外的其他行政機關。但在行政訴訟中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只不過被賦予了訴訟當事人的能力和資格,實質上的權利義務歸屬者是國家或公共團體,③參見吳東都:《論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臺灣大學1987年碩士學位論文。而且各個行政行為之間并非是完全獨立的,比如在規劃許可領域就涉及多個有關聯的行政行為,一個行政行為被撤銷或被確認無效很可能導致與之相關的行政行為的效力受到影響。因此,為提高訴訟效率,消除違法狀態,更好地發揮行政判決解決行政爭議的功能,行政判決拘束力的主觀范圍應包括相關行政機關。
(二)拘束力的功能
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在行政訴訟相關立法中均確立行政判決的拘束力制度,通過分析其立法意旨可以發現行政判決拘束力的制度功能。
戰前日本《行政裁判法》第18條規定:“行政裁判所之判決,就其事件有羈束關系行政廳。”戰后日本《行政事件訴訟特例法》第12條規定:“確定判決,就其事件拘束關系行政廳。”現行的《行政事件訴訟法》承襲前兩部法律的規定,于該法第33條第1款規定:“撤銷處分或者裁決的判決,就其事件,拘束為當事人之行政廳或其他關系行政廳。”日本在《行政裁判法》時代明確判決的拘束力,是因為當時行政裁判所屬于行政權之一環,就行政一體而言,行政機關應當尊重行政裁判所為判斷之內容,④參見賴恒盈:《行政訴訟裁判拘束力之研究》,載《臺灣本土法學雜志》第103期(2008年)。后日本一切法律爭訟均由司法權之普通法院審理,此時仍規定行政判決有拘束相關行政機關的效力,其目的在于“保證行政行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實效性”⑤王天華:《行政訴訟的構造:日本行政訴訟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頁。。
受日本法的影響,我國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16條規定了判決的拘束力。⑥我國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16條規定:“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系機關之效力。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后,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前二項判決,如系指摘機關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該機關即應受判決之拘束,不得為相左或岐異之決定或處分。前三項之規定,于其他訴訟準用之。”該條款的立法目的是“為使行政法院所為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對于原告之權利救濟具有實效,應課原機關以尊重判決內容之義務,以防杜原機關依同一違法之理由,對同一人為同一之處分或決定”①翁岳生主編:《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593-594頁。。換言之,判決拘束力的制度目的在于使行政法院判決能充分發揮其解決糾紛實效。對于該實效的實現,我國臺灣地區有學者從結果除去請求權的角度加以論證,為了完全去除因違法的行政處分所殘留的違法狀態,行政機關不得不受拘束,并基于該拘束力遵照原判決意旨,為種種相配合及相對應的適當的對策及相關處置。②參見曾華松:《論行政訴訟撤銷判決之拘束力(上)》,載《軍法專刊》第36卷第4期(1990年)。
結合日本法及我國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判決拘束力的規定,可以發現拘束力的功能反映出具有拘束力的裁判須對行政行為進行了司法審查,進而能夠實現救濟原告合法權利。換言之,法院未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所作裁判原則上不具有此種效力。
三、不予執行裁定拘束力的證成
結合拘束力的制度功能,拘束力原則上是行政判決的一項效力,至于法院所作裁定包括其在行政非訴執行程序中所作不予執行裁定是否也具有拘束力,目前尚未有明確答案。一般而言,行政非訴執行中不予執行裁定具有拘束力。但要證成這一觀點,需要從不予執行裁定與行政判決的相似性以及我國行政訴訟的特殊構造兩方面予以論證。
(一)不予執行裁定與行政判決的相似性
根據《行政強制法》第58條和《行訴解釋》第161條的規定,不予執行裁定是指法院對被申請執行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時,發現該行政行為具有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或“三明顯”情形,為阻止此類行為進入執行環節所作出的裁定。行政判決是指法院在審查、判定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的基礎上,對行政爭議所作的實體處理結論。③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6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頁。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8條、第69—79條分別規定了幾種典型的判決形式,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判決、撤銷判決等。單從名稱、形式及程序上來看,不予執行裁定與行政判決存在較大差異。特別是法院在作出行政判決時,往往需要開庭審理,兩造到庭進行言詞辯論,程序要求較高;法院作出不予執行裁定時,多采用書面審理,不需要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出庭進行言詞辯論,且法院應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是否準予執行的裁定,程序要求相對較低。
盡管如此,二者之間仍具有一些實質相似之處,正是這種相似為不予執行裁定具有行政判決的拘束力提供了前提及可能。具體而言,這些相似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適用事項相似。關于裁定適用的事項,不論在我國民事訴訟領域抑或行政訴訟領域,學者多認為裁定主要用來處理程序性問題,①民事訴訟領域持此觀點的參見宋朝武主編:《民事訴訟法學》(第5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頁;《民事訴訟法學》編寫組:《民事訴訟法學》(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頁。行政訴訟領域持此觀點的參見關保英主編:《行政六法簡明教程》,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頁;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法學》(第2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頁;《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編寫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29頁。判決主要用來處理實體性問題。但并非所有裁定均不處理實體問題,不予執行裁定即為一種例外。雖然不予執行裁定適用于行政非訴執行程序,解決是否執行生效行政行為的問題,但根據《行訴解釋》第160條第1款的規定,法院在作出不予執行裁定前應當由行政審判庭來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即需要處理實體問題。雖然法院最終以裁定的形式決定是否準予執行,但該裁定本身包含著對行政行為效力的判斷,否則將會導致被法院裁定不予執行的行政行為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與該行政行為相關的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或公共利益得不到及時維護,司法的權威得不到體現。也有觀點主張,鑒于行政非訴執行程序的特殊性,應當準許在該裁定的說理部分明確被申請執行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并認為不予執行裁定徹底否定了該行政行為的法律效力,②參見婁小平、郭修江:《非訴執行若干問題研究》,載中國法院網2002年10月25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2/10/id/16566.shtml。進而肯定了不予執行裁定對行政行為效力所作的判斷。
第二,司法審查程度相似。根據《行政訴訟法》第6條的規定,法院在作出行政判決時主要采用合法性審查標準,但學界對于法院作出不予執行裁定所采用的審查標準則存在一定的爭議,③如有觀點認為行政非訴執行的審查標準為“明顯違法”[參見江必新、梁鳳云:《行政訴訟理論與實務》(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2頁。],也有觀點認為應構建多元化審查標準(參見李清宇:《非訴執行行政案件司法審查標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頁。)。故在此主要通過對比不予執行裁定和相關行政判決的適用情形,來發現這兩種裁判的審查強度的相似性。根據《行政強制法》第58條和《行訴解釋》第161條第1款的規定,不予執行裁定的適用情形主要包括“三明顯”情形及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四種,其中“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以及“明顯缺乏法律、法規依據”與《行政訴訟法》第75條所規定確認無效判決的適用情形重合;“明顯缺乏事實根據”及“其他明顯違法并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則可視情況被納入撤銷判決或確認無效判決的適用情形之中。就此而言,法院在作出不予執行裁定時,與其作出撤銷判決或確認無效判決時所采用的審查程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二)“準雙向”的行政訴訟構造
盡管不予執行裁定與行政判決具有實質相似性,但二者適用階段和程序的不同,能否構成不予執行裁定具有拘束力的障礙呢?答案是否定的,這需要對我國當下特殊的行政訴訟構造予以考察。
1.行政訴訟程序:“民告官”
行政訴訟制度被稱為“民告官”的制度。根據《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款、第25條、第26條的規定,當下我國行政訴訟的原告為行政相對人及特定的行政相關人,而被告為行政機關。即不同于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是對等的,一方當事人起訴,另一方當事人可以進行反訴,我國行政訴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原被告恒定,行政機關處于被告地位,行政相對人、行政相關人處于原告地位。同時結合《行政訴訟法》第1條的規定,我國行政訴訟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和救濟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結合以上兩點,可以大致得出當下我國的行政訴訟構造為“民告官”式的單向訴訟,不包括行政機關為維護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而起訴行政相對人的“官告民”式訴訟。
對于為何不將“官告民”納入到行政訴訟中這一問題,有觀點認為:“主要考慮到‘官治民’的手段已經非常多了,如果允許‘官告民’將會導致本已強大的行政權通過司法權進一步強化,既背離了設置行政訴訟制度的初衷,又不利于切實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①江必新編著:《行政訴訟法修改資料匯纂》,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也有觀點認為,將“官告民”納入到行政訴訟中的必要性不足,如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屬于執行問題不是訴訟,《行政強制法》已經作了規定,不應納入行政訴訟法調整。②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
以上說法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社會改革的進行、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將行政訴訟定位為單向訴訟有些不合時宜。實踐中出現的“官告民”需求,及相關的“官告民”案例,③參見李騰飛:《家長放任子女輟學被政府起訴 這種“官告民”值得推廣》,載中國新聞網,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0/01-02/9049394.shtml。也證明了行政訴訟的單向構造在某些情況下已經捉襟見肘。④參見閆映全:《反向行政訴訟研究》,中國政法大學2018年博士學位論文。比如針對行政非訴執行制度,就有學者建議打破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中只作被告的觀念,適用公訴程序解決行政相對人不履行義務所引起的行政爭議;⑤參見楊立新、張步洪:《行政公訴制度初探》,載《行政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也有學者建議建立“官告民”的簡易訴訟制度;⑥參見馬懷德:《修改行政訴訟法需重點解決的幾個問題》,載《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還有學者根據行政非訴執行審查標準的不同,提出建立執行訴訟這一種“官告民”的訴訟。⑦參見劉東亮:《官告民訴訟制度設立之構想——非訴行政行為申請執行程序改造與完善》,載《行政與法制》2003年第8期。但我國《行政訴訟法》在修訂時,并未采納這些建議引入“官告民”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仍遵循1989年《行政訴訟法》所確立的單向行政訴訟構造的傳統。
2.行政非訴執行程序:“準官告民”
雖然我國在《行政訴訟法》中規定了行政非訴執行制度,但考慮到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構造仍為典型單向訴訟,故不能將行政非訴執行制度當然地視為“官告民”式訴訟。盡管如此,結合《行政強制法》及《行訴解釋》的相關規定,行政非訴執行制度與我國現行的單向行政訴訟構造相比,呈現出某種特殊性。
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在確立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現有行政訴訟構造之時,還在第八章“執行”中設置第66條,初步確立起行政非訴執行制度,對于該條款后續《行政訴訟法》在修改時仍沿襲之。雖然行政非訴執行制度被規定在《行政訴訟法》的“執行”章節,但結合《行政強制法》和《行訴解釋》的規定,發現行政非訴執行具有類似“官告民”的特點。還有學者直接將其稱為“官告民”的執行,與“民告官”訴訟引發的執行區分。①參見王華偉:《試論非訴行政執行體制之改造——以裁執分離模式為路徑》,載《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9期。但我國《行政訴訟法》并未明確承認“官告民”式訴訟的存在,將其稱之為“官告民”的執行與現行法律有所抵牾。結合《行政強制法》和《行訴解釋》的相關規定,將行政非訴執行稱之為“準官告民”或者“準反向訴訟”更為妥當。
一方面,行政非訴執行不具有行政訴訟的外觀特征。首先,根據《行政訴訟法》第97條的規定,行政非訴執行的提起采用的是“申請”而非“起訴”,用詞不同于行政訴訟;其次,法院在行政非訴執行案件中通常采用書面審查的方式,除特別規定外不要求兩造到庭進行言詞辯論;再次,行政非訴執行條款位于《行政訴訟法》的“執行”章節中,而不是典型的訴訟程序之中;最后,學界對這一制度的命名即“行政非訴執行”,也體現著其與行政訴訟程序的不同。因而行政非訴執行原則上不具有行政訴訟的外觀特征。
另一方面,行政非訴執行本質上具有“官告民”的特點。首先,從結構上看,行政非訴執行中的申請人是行政機關,被申請人或被執行人是行政相對人,法院居中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這與行政訴訟典型的“民告官”構造截然相反。其次,從目的上看,沒有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提起行政非訴執行申請表明的是,其對行政相對人不服從生效行政行為的不滿,并請求法院對生效行政行為予以執行,以實現行政行為所要維護的公共秩序。因此,行政非訴執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時維護客觀秩序,而非單純為個人提供救濟,這顯然不同于“民告官”主要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目的。而且此時行政相對人已經放棄法定救濟權利的行使,若將行政非訴執行制度目的定位為救濟相對人權益,則會放縱相對人“躺在權利上睡大覺”,也會使當下行政訴訟、行政復議的期限制度虛置。最后,從審查程序上看,行政非訴執行程序中,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帶有解決行政爭議的意味,即通過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來判斷是否支持行政機關的執行申請,同時考慮到“涉非訴執行的行政決定事關重大,而‘執行’又天然帶有對公民財產乃至人身侵犯的可能”①解志勇、閆映全:《反向行政訴訟:全域性控權與實質性解決爭議的新思路》,載《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3期。,在特定情形下法院還可以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
實踐中,部分法院的司法性文件還規定,特定情形下法院在作出是否準予執行裁定前,應當進行聽證。②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規范行政非訴案件受理和審查工作的指導意見〉的通知》,粵高法〔2012〕1號,2012年1月29日發布。這就使得行政非訴執行審查程序具有和行政訴訟相似的雙方當事人參與的特點。此外,也有學者呼吁優化行政非訴執行程序,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準庭審程序,從而達到事實上的“雙向機制”。③參見王敬波:《行政協議助推行政訴訟構造變革》,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6月5日,第5版。
綜上,基于不予執行裁定與行政判決的相似性,以及我國當下“準雙向”的行政訴訟構造,行政判決的拘束力可以適用于行政非訴執行中不予執行裁定。
四、不予執行裁定拘束力的展開
不予執行裁定可適用于行政判決的拘束力,換言之,不予執行裁定對于行政機關具有積極效力和消極效力。但由于行政非訴執行案件的法定結案方式有限,實踐中不予執行裁定的適用情形并不限于《行政強制法》和《行訴解釋》所列舉的四種,部分法院利用其中的兜底條款直接將不予執行裁定適用于其他情形,因此對于不予執行裁定的拘束力不可一概而論,需要結合具體情形具體分析。
如前所述,拘束力的制度功能是為確保行政判決救濟行政相對人權利實效的實現,因此拘束力主要適用于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審查后所作裁判,若法院裁判并不涉及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則該裁判通常不具有拘束力。具體到不予執行裁定,若不予執行裁定涉及到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這一實體問題,則該裁定具有拘束力;若僅涉及程序性事項的處理,則對行政機關不產生拘束力。
(一)拘束力之適用:無效或可撤銷事由
1.具體情形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75條及《行訴解釋》第99條的規定,若行政行為存在重大且明顯違法情形的,則其系無效行政行為。“無效行政行為自始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對于無效行政行為,相對人并無服從義務,行政機關也不得予以執行”④趙宏:《法治國下的行政行為存續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頁。。而且,“在行政強制執行中,由于無效行政行為自始無效,自然也就不能作為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⑤王貴松:《行政行為無效的認定》,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6期。。因而法律和司法解釋均規定,對于存在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明顯缺乏事實根據、明顯缺乏法律法規依據以及其他明顯違法并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行政行為,法院應作出不予執行裁定。
除以上四種無效事由外,行政行為客觀上不可能實施或者行政行為不具有可執行內容也是行政行為無效的一項事由。即若行政行為的內容構成客觀上無法實現,如命令行政相對人拆除一處已經不存在的違章建筑,或拆除建筑物的部分不可分割設施的,這類行為構成無效行政行為。①根據《行訴解釋》第99條的規定,“行政行為的內容客觀上不可能實施”屬于行政行為無效的一種情形。實踐中,對于此類情形,法院多裁定不予執行。②參見北京市國土資源局與北京市平谷區馬坊鎮人民政府行政非訴執行案,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2014)平執字第2653號行政裁定書。
除此之外,當行政行為存在可撤銷事由時,法院也會裁定不予執行,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一是適用法律錯誤,在蛟河市自然資源局與佟某非訴行政執行復議審查案中,法院認為,本案中佟某非法占用土地應當適用《土地管理法》第74條的規定,蛟河市自然資源局適用《土地管理法》第76條、《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42條的規定進行處罰,屬于適用法律錯誤,故維持不予執行裁定。③參見蛟河市自然資源局與佟某非訴行政執行復議審查案,吉林省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吉02行審復44號行政裁定書。二是超越職權,在巴彥縣環境保護局與黑龍江省興隆林業局非訴執行審查案中,法院認為,巴彥縣環境保護局對黑龍江省興隆林業局沒有行政執法權,其對林業局所作行政處罰屬超越職權,并裁定不予執行。④參見巴彥縣環境保護局與黑龍江省興隆林業局非訴執行審查案,黑龍江省巴彥縣人民法院(2018)黑0126行審53號行政裁定書。三是濫用職權,在佛山市南海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與梁杰洪非訴行政執行復議案中,法院認為,南海區衛計局針對梁杰洪所超生雙胞胎中的一名子女,認定為超生二個子女,并按照超生一個子女應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的基數的兩倍征收社會撫養費,認定事實明顯錯誤,適用法律不當,屬于濫用行政職權。⑤參見佛山市南海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與梁杰洪非訴行政執行復議案,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6行審復4號行政裁定書。四是違反法定程序,如在遼源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遼源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職工總醫院非訴執行審查案中,法院認為案涉行政處罰事項是從重處罰,應由集體討論作出,但從市發改委提交的討論記錄中未體現對礦醫院的從重處罰是由集體討論作出的決定,市發改委對礦醫院作出的從重處罰未遵守該法定程序,故裁定不予執行。⑥參見遼源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遼源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職工總醫院非訴執行審查案,吉林省遼源市西安區人民法院(2016)吉0403行審68號行政裁定書。此外,行政決定作出前未告知相對人、⑦參見輝縣市環境保護局與郭紅希非訴執行審查案,河南省輝縣市人民法院(2016)豫0782行審41號行政裁定書。聽證期限未屆滿作出處罰決定、⑧參見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與李言帥其他行政非訴審查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行非訴審字第2401號行政裁定書。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⑨參見洛南縣國土資源局與陳西嶺土地行政處罰非訴審查案,河南省洛南縣人民法院(2015)洛南行非審第00006號行政裁定書。以及行政決定送達程序不合法等,①參見新密市水務局訴河南伏羲山旅游開發有限公司行政處罰案,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鄭行復字第2號行政裁定書;德州市公路管理局德城公路局與山東新工起重設備有限公司非訴執行審查案,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魯14行審復1號行政裁定書。也是因違反法定程序而被裁定不予執行的事由。
2.拘束力的表現
當行政行為存在無效或可撤銷情形時,法院此時所作不予執行裁定或具有類似確認無效判決的效力,僅起到宣示或確認行政行為無效的作用,并不引起相關法律關系的變動;或具有類似于撤銷判決的效力,使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恢復到原行政行為作出之前的狀態。此時法院所作不予執行裁定對行政機關具有如下拘束力:
一是禁止行政機關以同一主要事實和主要理由作出與原無效行為相同的行為;二是若違法狀態繼續存在,行政機關在收到不予執行裁定后,負有對原違法事項重新或繼續處理的后續義務,以維護相關人的合法權益以及公共利益,此時并不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但其在后續處理過程中仍受禁止反復效力的拘束;三是若存在與該行政行為相關的行政行為,則相關行政機關有主動審查這些行政行為的義務,并根據情況采取相應的處理措施;四是若行政相對人并不存在違法事實的,則行政機關應在收到不予執行裁定后,及時撤銷原行政決定。一般而言,類似撤銷判決的不予執行裁定原則上具有使行政行為溯及既往失去效力的作用,但考慮到行政非訴執行程序中行政行為多已具有確定力,若由行政機關直接針對原違法事項再次作出行政行為,則可能有“一事二罰”之嫌,再次引發爭議,因此由行政機關在收到不予執行裁定后主動撤銷原行政行為更具合理性。
此外,若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機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過程中,已經部分或全部履行原行政行為,但法院以該行政行為存在無效或可撤銷情形而裁定不予執行時,行政機關原則上還具有返還或恢復原狀的義務,如退還行政相對人已繳納的罰款。但此義務并不屬于不予執行裁定的拘束力,應是不予執行裁定宣告行政行為無效或可撤銷的一種附隨效果。
(二)拘束力之排除:不符合受理條件
1.具體情形
盡管《行政強制法》和《行訴解釋》均規定了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應當滿足一定的條件,不滿足受理條件的法院應當裁定不予受理,但實踐中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案件可能進入審查階段,囿于行政非訴執行法定結案方式的限制,此時法院多選擇適用不予執行裁定結案。具體情形主要包括以下五種:
一是法定救濟期間尚未經過。根據《行政強制法》第53條規定,行政機關申請行政非訴執行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行政決定因當事人放棄訴權而具有了形式確定力。若行政行為尚未經過起訴期限,此時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則完全不符合行政非訴執行的申請條件,也有可能損害相對人的訴權,在此情況下部分法院多裁定不予執行。如起訴期限未屆滿申請行政非訴執行、①參見渭南市國土資源局臨渭分局與趙學仁其他行政非訴執行復議案,陜西省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陜05行審復1號行政裁定書。行政行為正處于復議或訴訟階段時申請行政非訴執行。②參見輝縣市環境保護局與湖南天心種業有限公司輝縣市分公司非訴執行審查案,河南省輝縣市人民法院(2015)輝行審字第67號行政裁定書。
二是行政機關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在違法建筑物、構筑物和設施強制拆除等特定行政管理領域,根據法律的授權行政機關可以自行強制執行其行政決定,一般不需要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若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則法院原則上不應受理;③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違法的建筑物、構筑物、設施等強制拆除問題的批復》,法釋〔2013〕5號,2013年3月27日發布。若法院已經受理,經審查法院多裁定不予執行。④參見鄭州市國土資源局與鄭州國際物流園區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非訴執行審查案,河南省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2016)豫0191行審16號行政裁定書。
三是申請主體不適格。《行訴解釋》第155條規定了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時應滿足的一些條件,其中第1款第3項是對申請人主體資格的限制,也即申請人須是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行政主體。如果該申請不滿足這一條件則可能被法院裁定不予執行。⑤參見南京市社會保險管理中心與南京液壓機械制造廠有限公司其他行政非訴執行審查案,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2014)江寧非訴行審字第40號行政裁定書。
四是逾期申請且無正當理由。《行政強制法》第53條和《行訴解釋》第15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在法定起訴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行政非訴執行申請,若行政機關逾期申請且無正當理由的話,實踐中法院有時會裁定不予執行,⑥參見魚臺縣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與劉景非訴執行審查案,山東省魚臺縣人民法院(2018)魯0827行審9號行政裁定書。不過是否具有正當理由同樣需要法院結合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五是催告程序違法。根據《行政強制法》第54條的規定,在行政非訴執行前,行政機關應當催告當事人履行。若催告程序違法,法院也會裁定不予執行,主要包括:法定起訴期限未滿即催告、⑦參見永吉縣林業局與張喜德非訴行政執行案,吉林省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吉02行審復82號行政裁定書。未經催告程序即申請強制執行、⑧參見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與鄭鐵輝行政處罰非訴行政執行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深中法行非訴審字第519號行政裁定書。催告期限尚未屆滿即申請執行等情形。⑨參見樂山市環境保護局與四川恒邦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非訴執行審查案,四川省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川11行審復1號行政裁定書。
2.拘束力的表現
對于以上五種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情形,法院所作不予執行裁定僅處理了是否受理這一程序性問題,尚未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故在此類情形下的不予執行裁定不具有拘束力。
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以上五種情形,法院在受理階段應裁定不予受理。囿于當下法定結案方式種類的不足,進入案件審理階段后,法院僅能作出準予或不予執行裁定,故而對于此類因不符合法定受理條件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執行的案件,此時不予執行裁定具有和不予受理裁定相似的效力。即此時法院僅對申請材料進行了形式審查,尚未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等實體性問題進行實質審查,尚不足以對行政機關構成某種約束。不過對于此類不予執行裁定,如有補正相關申請材料之可能,行政機關負有補齊相關材料重新提出行政非訴執行申請的義務,或者等待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再重新提起行政非訴執行申請,但這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原則和行政非訴執行制度的要求,而非不予執行裁定所生之拘束力。
簡言之,對于不予執行裁定的拘束力不可一概而論,應根據裁判理由具體分析(見表1)。因行政行為存在無效或可撤銷事由而作出的不予執行裁定,該裁定具有約束行政機關的拘束力,相關行政機關應根據案涉不予執行裁定的具體裁判理由,負有相應的積極和消極義務;因不符合行政非訴執行案件受理條件而作出不予執行裁定,該裁定不具有對行政機關的拘束力。

表1 不予執行裁定的拘束力
結 語
隨著行政非訴執行制度在我國的確立和發展,每年都有大量的行政非訴執行案件涌入法院,并產生大量的行政非訴執行裁定,這些裁定主要為準予執行裁定和不予執行裁定。囿于我國行政訴訟領域立法及學理層面對行政裁判效力關注的不足,不予執行裁定對行政機關的效力問題存在立法及理論空白,這一空白影響著行政非訴執行制度的有效落實、行政爭議的有效化解以及客觀法秩序的維護。未來在關注行政非訴執行這一具有中國特色制度運行的同時,不僅應完善行政非訴執行的法定結案方式,減少不予執行裁定的濫用,還應加強對行政裁判效力的研究,以推動法律對行政裁判效力的關注與完善,比如可以考慮在《行政訴訟法》或《行政強制法》中明確規定行政裁判的效力,特別是明確規定行政裁判對行政機關的效力,以促進法院裁判實效及相關法秩序的維護,實現司法權和行政權的良好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