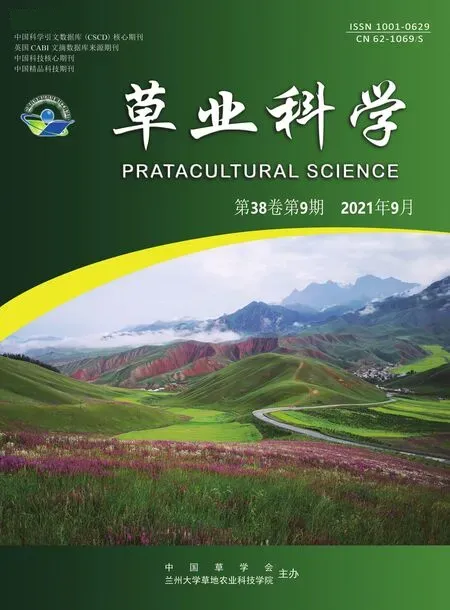基于無人機的東北鼢鼠種群數(shù)量調(diào)查最佳尺度選擇
孫珊珊,滿都呼,偉 軍,朝克圖,阿 焱,張 恒,付和平,5,武曉東,袁 帥
(1.內(nèi)蒙古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草原與資源環(huán)境學(xué)院 / 嚙齒動物研究中心,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2.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倫貝爾市草原工作站,內(nèi)蒙古 呼倫貝爾 021008;3.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鄂溫克族自治旗草原工作站,內(nèi)蒙古 呼倫貝爾 021100;4.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正鑲白旗草原工作站,內(nèi)蒙古 錫林郭勒 013800;5.內(nèi)蒙古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生命科學(xué)學(xué)院,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
呼倫貝爾草原總面積997.3 萬hm2,是內(nèi)蒙古最重要的草甸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其生物多樣性豐富,是我國草產(chǎn)業(yè)以及畜牧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基地[1]。近年來,呼倫貝爾草原出現(xiàn)草地區(qū)域性退化的現(xiàn)象,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除了氣候變化和草地過度利用以外,草原鼠害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東北鼢鼠(Myospalax psilurus)是呼倫貝爾草甸草原主要害鼠之一,是一類常年營地下生活的嚙齒動物。為獲取食物、繁殖和尋找合適的棲息地,東北鼢鼠會在地下挖掘土壤并推至地表, 形成土丘,加劇草地退化,造成草地生產(chǎn)力下降,從而制約了畜牧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2-3]。因此,及時獲取東北鼢鼠種群數(shù)量及動態(tài),對于預(yù)測其危害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東北鼢鼠常年棲息于地下,使用常規(guī)地上鼠數(shù)量調(diào)查法難以統(tǒng)計其種群數(shù)量,目前地下鼠種群數(shù)量調(diào)查方法包括人工捕盡法、土丘計數(shù)法等,但不適于草原地下害鼠大面積調(diào)查[4-5]。已有研究表明,鼢鼠數(shù)量與地上土丘數(shù)量間存在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6-7],但對大面積土丘數(shù)量進行調(diào)查時,不僅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存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困難、調(diào)查周期長、實時性差的缺點。
無人機在野外工作時不僅采樣周期短,而且能提供多角度、高分辨率影像,還可及時進行動態(tài)分析,具有受地面條件限制少、獲取信息量大、探測范圍廣等技術(shù)優(yōu)勢[8]。近年來,隨著無人機技術(shù)的不斷成熟和普及使用,已有不少學(xué)者將無人機技術(shù)應(yīng)用于嚙齒動物調(diào)查中[9-14],內(nèi)容大都集中于對鼠害評定、監(jiān)測以及鼠洞的識別。在種群數(shù)量調(diào)查方面,無人機主要應(yīng)用于較大型野生動物及鳥類[15-23],在小型哺乳動物尤其是嚙齒動物種群數(shù)量調(diào)查方面應(yīng)用較少。因此,本研究使用無人機航拍和地面實地調(diào)查相結(jié)合的方法,并采用不同飛行高度和拍攝面積進行航拍,一方面確定本研究所用型號無人機在東北鼢鼠種群數(shù)量調(diào)查中的最佳航拍高度,另一方面確定無人機在東北鼢鼠種群數(shù)量調(diào)查中的最小取樣面積,并提供無人機在地下鼠種群數(shù)量調(diào)查中的技術(shù)方法。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qū)自然概況
研究區(qū)位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額爾古納市、陳巴爾虎旗、鄂溫克族自治旗境內(nèi)草甸草原,氣候類型為溫帶大陸性季風(fēng)氣候,年平均氣溫在0 ℃以下,春季干燥風(fēng)大,夏季溫涼短促,秋季氣溫驟降,冬季寒冷漫長,雨熱同期。主要植物有貝加爾針茅(Stipa baicalensis)、羊草(Leymus chinensis)、糙隱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日陰菅(Carex pediformis)等。
1.2 無人機參數(shù)設(shè)置
本研究使用大疆精靈3 Professional 無人機對樣地進行航拍。該無人機為四旋翼飛行器,工作環(huán)境溫度0~40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16 m·s?1,最大上升速度5 m·s?1,最大下降速度3 m·s?1,單塊電池飛行時間約23 min,信號有效距離2 000 m,搭載4 k 鏡頭,照片最大分辨率為4 000 × 3 000。
1.3 試驗設(shè)計
2017年9月在呼倫貝爾草甸草原區(qū)進行無人機航拍,包括額爾古納市(1 個航拍樣地)、陳巴爾虎旗(7 個航拍樣地) 和鄂溫克族自治旗(5 個航拍樣地)(圖1)。以上航拍樣地,分別設(shè)置了3 個面積為30 m ×30 m 的固定樣方,樣方內(nèi)人工測定土丘數(shù)量,隨后,分別在30、50、100、150 和200 m 高度進行航拍數(shù)據(jù)采集(圖2),每個地點及高度重復(fù)拍攝3 次,共獲取有效航片195 張。對航片進行目視解譯,選擇8 名有著長期野外調(diào)查經(jīng)驗的專業(yè)人員對航拍影像進行判讀,標(biāo)記出錯判、漏判圖斑,最終確定其是否為鼢鼠土丘。統(tǒng)計航片中樣方內(nèi)土丘數(shù)量,并結(jié)合人工地面調(diào)查土丘數(shù)量,計算無人機土丘識別度(式1),進行最優(yōu)航拍高度的分析。以30 m 航片提取土丘數(shù)量為依據(jù)計算每公頃識別土丘數(shù)量,根據(jù)50、100、150 和200 m 航拍高度下土丘識別度依次計算每公頃未識別土丘數(shù)量,對不同航拍面積中未識別到的土丘數(shù)量進行校準(zhǔn)。使用巢式樣方對數(shù)模型[24-25](式2),對航拍面積與不同區(qū)域鼢鼠土丘密度進行回歸分析,確定最小取樣面積。

圖1 呼倫貝爾草甸草原無人機航拍點示意圖Figure 1 Map of the aerial photography locations in the meadow grasslands of Hulunbuir

圖2 不同航拍高度下土丘實拍Figure 2 Actual images of mounds photographed from different aerial heights

式中:a 和b 為常數(shù),S為土丘數(shù)量,A為取樣面積。
1.4 數(shù)據(jù)分析
使用Excel 進行初期數(shù)據(jù)處理;使用SPSS 14.0軟件對航拍高度和土丘識別度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利用SigmaPlot 14.0 軟件對航拍高度和土丘識別度進行作圖,對航拍面積與鼢鼠土丘密度進行回歸分析。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不同航拍高度與土丘識別度的關(guān)系
不同航拍高度下土丘識別度的結(jié)果顯示,無人機在30 m 高度航行時,土丘識別度最高,50 m 航拍高度土丘識別度與30 m 無顯著差異(P> 0.05),與100、150 和200 m存在顯著差異(P< 0.05),100 和150 m 之間無顯著差異(P> 0.05),但與200 m 存在顯著差異(F= 28.57,P< 0.05) (圖3)。結(jié)果表明,航拍高度為30 m 時,無人機識別土丘正確率最高,航拍高度50 與30 m 無顯著差異。因此,本型號無人機最佳航拍高度為50 m。

圖3 不同航拍高度的土丘識別度Figure 3 Degree of mound recognition at different aerial heights in Ergun city
2.2 不同航拍面積與土丘密度的關(guān)系
基于航拍高度與航拍面積的關(guān)系(表1),對航拍面積與校準(zhǔn)前后不同區(qū)域土丘密度進行回歸分析。結(jié)果顯示:額爾古納市航拍面積為2.210 hm2時,航拍土丘密度多且穩(wěn)定,校準(zhǔn)后,航拍面積超過2.210 hm2時土丘密度隨航拍面積增大而緩慢增加(圖4)。陳巴爾虎旗各航拍工作地點土丘密度隨航拍面積的增加而增長,且在航拍面積為0.205 和0.569 hm2時土丘密度增加趨勢明顯,在航拍面積為2.210 hm2時土丘密度增長趨勢變緩(圖5)。鄂溫克族自治旗無人機識別土丘密度增長趨勢與陳巴爾虎旗相似,均在航拍面積為2.210 hm2時到增長拐點(圖6)。

表1 無人機航拍高度與對應(yīng)航拍面積Table 1 UAV aerial photography heights and corresponding aerial photography areas
總體看,每個航拍點的土丘密度均隨無人機航拍面積的增加而增加,且隨面積的增加增速變慢,無人機最理想取樣面積應(yīng)為2.210 hm2(圖4 至圖6)。

圖4 額爾古納市航拍面積與土丘密度擬合曲線Figure 4 Fitted curve between the aerial photography area and the mound density in Ergun City

圖5 陳巴爾虎旗航拍面積與土丘密度擬合曲線分析Figure 5 Analysis of the fitted curves between the aerial photography area and the mound density in Chen Barhu Banner

圖6 鄂溫克族自治旗航拍面積與土丘密度擬合曲線分析Figure 6 Analysis of the fitted curves between the aerial photography area and mound density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3 討論
本研究航拍時間選擇為2017年9月,當(dāng)?shù)匾堰M入秋季,牧草枯黃,可以減少植被和植被陰影對土丘識別度的影響。其次,9月是東北鼢鼠活動高峰期[26-27],適合用土丘計數(shù)法來調(diào)查鼢鼠種群相對數(shù)量[28]。
孫迪等應(yīng)用無人機對新疆北部地區(qū)荒漠草原黃兔尾鼠(Eolagurus luteus)鼠洞進行監(jiān)測,認(rèn)為航拍高度低于54.8 m 時可以準(zhǔn)確識別鼠洞[29],與本研究結(jié)果相似。花蕊利用無人機對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鼠洞進行航拍最佳高度為20 m[30]。與本研究結(jié)果不同的原因在于兩種鼠類的鼠洞和土丘直徑存在較大差異。高原鼠兔鼠洞直徑平均在7.1 cm左右,而東北鼢鼠土丘直徑在30~110 cm,在航拍影像中識別點的面積不同,進而造成航拍最佳高度的差異。
最佳航拍高度基于土丘識別度確定,土丘識別度取決于無人機航拍土丘數(shù)量和人工調(diào)查土丘數(shù)量,無人機航拍土丘數(shù)量的提取受無人機型號、搭載平臺等的影響。因此,50 m 是此型號無人機最佳航拍高度,但研究中航拍高度的確定方法可以應(yīng)用與任何無人機。最小取樣面積的確定是基于巢式樣方的思想,其主要用于估算群落或區(qū)域的物種多樣性以及確定群落的最小取樣強度[31]。本研究將其應(yīng)用于東北鼢鼠土丘數(shù)量調(diào)查中,并確定無人機航拍最小取樣面積為2.21 hm2,是使用無人機技術(shù)對東北鼢鼠土丘數(shù)量進行調(diào)查時最理想的取樣面積。最小取樣面積的確定使研究人員在野外調(diào)查時不必在大于該面積的范圍外進行不必要的取樣,也可避免在低于最小面積的取樣時低估東北鼢鼠的土丘數(shù)量。
新土丘更能反映地下嚙齒動物的種群數(shù)量動態(tài)變化[32]。航拍圖片中的新舊土丘不易識別,而土壤水分含量和植物群落組成在新舊土丘上均不同[33-34]。高光譜遙感可以根據(jù)植被反射的光譜值以及土壤和植被的混合光譜對新舊土丘進行解譯與判別[35-36],后期使用無人機航拍調(diào)查時,可以搭載高光譜或多光譜相機等傳感器,進一步分辨新舊土丘。 目前,研究人員主要采用目視及機器學(xué)習(xí)方法解譯航拍影像。目視解譯雖然準(zhǔn)確率得到保證,但受解譯人員素質(zhì)等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且增加了處理數(shù)據(jù)的工作量。機器學(xué)習(xí)方法雖然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但準(zhǔn)確率方面相比目視解譯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已有學(xué)者將機器視覺與無人機遙感相結(jié)合的方法應(yīng)用于生物監(jiān)測方面的研究[37-38],二者結(jié)合能夠在保證準(zhǔn)確率的基礎(chǔ)上提高效率。后續(xù)研究中,可以采用機器視覺與無人機遙感相結(jié)合的方法來提高采集數(shù)據(jù)的精確度及航拍影像處理能力。
4 結(jié)論
本研究運用無人機航拍技術(shù)對呼倫貝爾草甸草原東北鼢鼠種群相對數(shù)量進行調(diào)查,得出以下結(jié)論:
1) 土丘識別度隨航拍高度增加而降低。航拍高度為30 m 時,土丘識別度最高,50 和30 m 無顯著差異。據(jù)此,無人機最佳航拍高度為50 m。
2) 各航拍點土丘密度隨航拍面積增大而增加。航拍面積為0.205 和0.569 hm2時土丘密度增加趨勢明顯,航拍面積為2.21 hm2時土丘密度出現(xiàn)增長拐點。因此,最小取樣面積為2.21 hm2。
致謝:本研究得到了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鄂溫克族自治旗草原工作站的大力支持,課題組研究生楊素文、紀(jì)羽、李鑫、徐凱、張昊婷、楊可、商正昊妮、白鈞元、劉啟富等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