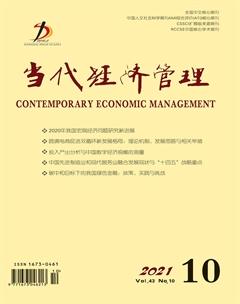我國供應鏈脆弱性緩釋與自主可控策略研究
沈小平
DOI: 10.13253/j.cnki.ddjjgl.2021.10.003
[摘 要] 面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我國供應鏈脆弱性風險問題凸顯,供應鏈自主可控、安全穩定面臨嚴峻挑戰。文章在分析當前供應鏈脆弱性風險產生的內外部環境因素的基礎上,闡述了國際環境沖擊的傳導效應與疊加效應對中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分工中的負面影響,使中國制造業供應鏈生態系統面臨破壞性的擾動,引致全球供應鏈遭受扭曲和重構秩序的困擾。提出了供應鏈脆弱性緩釋與自主可控策略與路徑,建立自主可控供應鏈戰略,打造雙循環供應鏈模式,發揮柔性與敏捷性優勢,增強供應鏈韌性與魯棒性,推進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創新供應鏈管理模式,優化供應鏈創新發展生態。
[關鍵詞]供應鏈;供應鏈脆弱性;風險緩釋;自主可控;策略與路徑
[中圖分類號]? F272.3;F27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0461(2021)10-0017-07
一、引 言
面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加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向區域化、多元化調整,我國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安全穩定面臨重大挑戰。中央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21)進一步明確“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政府工作報告》(2021)把“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列為重點工作之一。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和安全穩定是高度統一、一脈相承的。新冠肺炎疫情和貿易戰已經證實了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是后疫情時代的核心競爭力[1]。在國民經濟系統和現代產業體系中,產業鏈和供應鏈是緊密聯系、互相依存的兩個主線,產業鏈是中觀層面的產業之間建立的投入產出為主線的產業協作聯系,供應鏈是微觀層面的企業之間建立地以供需協作為主線的合作伙伴關系,供應鏈是產業鏈的基礎,供應鏈的安全穩定與自主可控能力建設是提升現代化水平的前提,是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和現代產業體系安全穩定的基石。
當前來自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困擾和不斷受到各種突發事件擾動的雙重挑戰,如國際貿易壁壘與貿易戰、關鍵核心技術主控戰、高端制造業爭奪戰等,疊加全球疫情,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全球統一市場將被貿易壁壘分割成為相對封閉的局部市場,這將直接和間接嚴重影響著我國供應鏈的安全穩定,中國高科技企業和現代制造企業受到的擾動尤為突出。這些擾動影響與破壞的不只是一個企業,而是每個行業龍頭企業代表的供應鏈網絡。因而,我國企業及其供應鏈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主要問題是供應鏈脆弱性問題,面臨的突出風險是同供應鏈脆弱性密切相關的新型風險。正如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所強調:供應鏈脆弱性風險在近十年將是一個影響世界經濟的新型風險問題。供應鏈脆弱性新型風險防范與管控和自主可控能力建設成為新時期關注的焦點和研究的重點。
二、研究進展文獻評述
(一)供應鏈風險因素與風險管理相關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供應鏈風險管理研究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隨后相關文獻數量每5年成倍增長,近些年來出現激增[2],成為國際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現有相關文獻主要從供應鏈風險的內涵、來源及影響因素、風險識別、評估、決策、控制等管理環節開展了較多研究。Ivanov(2018)認為風險的存在是由于對未來存在著某種確定類型的不確定性[3],不確定性水平與風險程度高度正向一致。Wagner等(2008)提出了識別供應風險來源的分析框架[4],Abdel Basset等(2019) 建立了度量不確定性和供應鏈風險的評估模型 [5]。在分析方法選擇上,Hamdi等(2018)運用網絡分析法(ANP)等多準則決策和多目標優化方法進行比較[6],Paksoy等(2019)采用內部審計和CA因果分析兩種層次分析法(AHP)評估風險[7]。對供應鏈風險控制和緩解策略有較多文獻關注,Tsiakis等(2001)認為供應鏈風險預防與控制應該始于供應鏈設計階段[8],控制風險的影響因素、采取風險轉移和分散、建立風險池[9]。預防風險的策略有冗余策略、靈活性策略[10]、延遲策略,以及物理備份、多元采購和標準化流程[11],建立靈活的供應基礎[12]和戰略庫存[13],不依賴特定供應商的產品設計[14]等緩釋方法與措施[15]。在技術應用上,利用大數據探索不確定性的決定性屬性與風險控制[16],強調供應鏈風險信息處理能力和環境不確定性在緩解策略選擇過程中扮演不同的調節作用[17]。同時,考慮公司的規模和發展階段,Hariharan等(2018)提出了中小企業防控供應鏈風險的關鍵因素與緩解策略[18]。
(二)供應鏈脆弱性與緩釋策略相關研究
供應鏈脆弱性內涵的相關闡述強調了供應鏈內外風險嚴重干擾的暴露[19]、因擾動而出現目標偏離的負面結果[20]。供應鏈脆弱性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之一是供應風險,如供應鏈中斷風險。供應鏈風險與供應鏈脆弱性的關系密不可分[21],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2],但是并不完全等同,當不利事件對供應鏈造成嚴重破壞時,風險才成為脆弱性[22]。在供應鏈脆弱性的影響因素分析中,認為脆弱性源于供應鏈風險的暴露[23],來自于供應鏈的復雜性、產品生命周期縮短、全球化的市場供需的不確定性[24],還由于供應網絡的全球化、供應商數量不斷減少[25]、供應鏈管理的精益化[26]等方面。通過建立供應鏈脆弱性評價理論框架[27]和評價模型[20],基于網絡的可視化和聚類分析方法對供應鏈脆弱性進行評估[28]。關于供應鏈脆弱性風險的消減方法,有文獻探討供應鏈脆弱性削減機制[29],有學者主張供應鏈成員應通過提升供應鏈恢復力[30]、構建彈性供應鏈[31]、實施彈性供應商選擇以及最優訂單分配策略 [32],以應對供應鏈脆弱性風險。
上述文獻研究表明,過去較多學者和管理實踐者對供應鏈風險問題關注和研究的范疇和側重點各不相同。現有文獻關注較多的是供應鏈的能力風險、協作風險與績效風險,對認識供應鏈風險本質與成因、識別、評價以及應對策略選擇的規律,提高企業供應鏈風險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貢獻。供應鏈風險管理的側重點一直被聚焦在微觀層面的企業供應鏈管理的運營職能上,大多是從企業內部運作與外部環境影響的角度探討與應對供應鏈風險問題,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從更高的層次更寬的視野來認識供應鏈風險問題,供應鏈與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緊密相依,供應鏈不只是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問題,我國供應鏈的安全穩定、自主可控關系到國家現代產業鏈體系安全和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也關系到我國“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本文基于構建我國自主可控的現代供應鏈體系的視角,探討新時期我國供應鏈脆弱性的本源與新型風險防范、自主可控能力建設的策略與路徑。
三、供應鏈脆弱性風險分析
供應鏈風險與供應鏈的脆弱性密切相關,在某些特定環境下相伴而生、互為因果。由于供應鏈脆弱性在不同的發展情形下面臨不同的發展環境具有不同的特征,要正確認識和理解我國供應鏈面臨的新型風險,需要在分析供應鏈脆弱性一般特征與成因的基礎上,結合當前的世界發展環境變局認識當前我國供應鏈脆弱性的本質特征及其新型風險。
(一)供應鏈脆弱性一般特征與成因
1.供應鏈脆弱性與風險關系
供應鏈脆弱性是使供應鏈產生非合目的傾向的性質,供應鏈適應外部變化、抵抗干擾和恢復能力薄弱,容易受到內部或外部的嚴重干擾從而引致供應鏈異常,使供應鏈目標受阻、造成破壞性或損失等情形。由于導致供應鏈偏離正常的、期望的或計劃的進度或活動的擾動因素存在,影響供應鏈穩定運行,導致違背正常的結果或者期望的結果暴露,因為負面結果的出現而影響公司實現目標的情形[21]。供應鏈的脆弱性與風險密不可分,應在一個統一框架下開展討論。從風險角度看,一方面,供應鏈脆弱性體現在內部風險和外部風險可能對供應鏈造成破壞的性質[22]。供應鏈由于內在的結構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存在而對外在的不確定性和擾動會做出敏感的不適反應,如供應鏈出現受阻、中斷、運營崩潰等不良后果引起損失。另一方面,供應鏈的風險并不等同于供應鏈的脆弱性,當不利事件的擾動對供應鏈可能造成嚴重破壞時的脆弱性才表明供應鏈的風險[33]。
2.供應鏈脆弱性的一般成因
供應鏈脆弱性源于供應鏈內部因素和外部擾動,使得供應鏈易于產生脆弱性,容易對各類風險因素的影響變得敏感[34]。供應鏈內部因素影響的程度和外部擾動發生的嚴重程度決定了供應鏈脆弱性的強度。在供應鏈發展進程中,當前面臨的脆弱性新型風險來源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供應鏈系統內部視角,脆弱性源于供應鏈系統的內生變量。譬如,供應鏈網絡結構的復雜性,新技術的應用、產品多樣化和生命周期縮短、個性化需求和客戶偏好多變、市場變化的頻率和振幅加大,市場的國際化以及生產規模的擴大等原因使得現在的供應鏈系統結構比過去更加復雜[35],增加了復雜性結構脆弱性。再如,供應鏈節點企業自身的缺陷,供應鏈管理過于強調供應鏈運營的精益化,追求供應鏈瘦身,精簡供應商和分銷商數量,從而使得供應、制造與分銷集中化,供應商和分銷商的集中度提高,供應鏈節點企業依賴程度增加,導致供應鏈系統結構更加僵化,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削弱。同時,由于全球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愈加激烈,供應鏈管理中對供應鏈運作效率和響應速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導致越來越重視供應鏈運營的敏捷性、實時性和低成本的運行模式,基于時間競爭和成本競爭獲取供應鏈競爭優勢。影響供應鏈的穩定性,有可能損害供應鏈績效。
第二,從第三方供應鏈服務嵌入供應鏈系統的視角,脆弱性源于供應鏈系統的嵌入性延伸。為應對全球分工背景下的供應鏈全球化,多數大中型企業專注于核心業務以提升其核心競爭能力,選擇將供應鏈服務外包,第三方物流和資金流、信息流等供應鏈服務節點介入,制造外包層次提高,對供應鏈服務需求依賴程度提高。其結果形成了供應鏈服務企業的客戶以大型企業或行業龍頭為主、業務占比較大且較為單一的客戶結構,多為定制化服務,營業收入集中度相對較高。這種供應鏈服務的嵌入性特點決定了企業客戶黏性強、忠誠度高,形成長期合作的依賴性和穩定性,但若面臨外部環境沖擊致使一方的經營情況和資信狀況發生重大不利變化,或發生突變擾動,將會立即將不利變化和擾動傳導給供應鏈系統,可能形成供應鏈的脆弱性暴露的動因。
第三,從供應鏈面臨的環境視角,脆弱性源于供應鏈的外部擾動因素,包括影響供應鏈穩定的人為災害和自然災害構成脆弱性的來源,這些環境擾動因素難以甚至不可預測。尤其是不可預測的外部擾動因素,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隨著供應鏈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全球采購、集中生產分銷等供應鏈發展新趨勢的增強,以及國家開放程度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供應鏈管理所面對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自然環境越來越復雜多變。不確定性及易變性已成為供應鏈面臨的新常態。供應鏈對環境易感性與環境擾動的有害性顯著相關,外部環境擾動的嚴重程度易于傳導到供應鏈的關鍵環節,致使供應鏈關鍵環節突變而失調,這種影響因素在當前顯得尤為突出。供應鏈的脆弱性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環境具有不同的特征,在當前面臨新的國際環境影響下表現出新的特征,構成供應鏈的新型風險因素。
(二)當前國際環境下供應鏈脆弱性來源
在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發展情境下,我國企業及其供應鏈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主要問題是供應鏈脆弱性問題,其本質特征是在全球供應鏈中主導權不足、自主可控能力不強,因此面臨的突出風險是同供應鏈脆弱性密切相關的新型風險,即波及供應鏈的安全穩定風險。逆全球化思潮迭起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使得全球供應鏈終端產品需求的不確定性和劇烈波動性,向供應鏈上游傳導且逐級放大,過去建立的敏捷供應鏈運作失靈,供應鏈協作與協同失去秩序和穩定性。盡管對供應鏈上不同環節的節點企業影響程度不一,但通過供應鏈的傳導,對供應鏈系統的影響產生疊加效應[36]。對我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分工中的地位產生負面影響、使我國制造業供應鏈生態系統產生破壞性的擾動、引致全球供應鏈遭受扭曲和重構秩序的困擾。
1.我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分工中的地位受到負面影響
從國際角度來看,由于全球生產分工活動不斷深入,我國企業從參與價值鏈分工逐步轉變為引導價值鏈分工活動。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及各類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勢必會以更高的頻率和強度出現,擾動既定的供應鏈分工體系,對中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分工地位產生副作用。全球疫情的防控進程與效果參差不齊,充分暴露了當前經濟全球化中的產品內分工體系的脆弱性[37],2021年聯合國發布的報告顯示[38],全球新冠疫情或將導致全球失去10年發展成果。這些因素都將對產品內分工格局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產生深遠影響,跨國公司將有可能考慮對其全球供應鏈進一步多元化,引發歐美部分處于供應鏈核心地位的跨國公司回流而引起在中國的供應商數量減少、份額下降甚至中斷。
2.我國制造業供應鏈生態系統面臨破壞性的擾動
當前需要重視全球疫情對我國制造業穩定的供應鏈生態系統造成破壞[39]而影響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從長遠來看,更需要預防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疊加貿易戰和科技戰以及經濟制裁與技術封鎖等沖擊全球供應鏈分工格局,甚至對制造業供應鏈生態產生破壞性的擾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通過直接影響市場需求、擾動市場秩序,市場劇烈波動通過供應鏈網絡迅速向上游擴散,并逐級放大波動幅度,產生長鞭效應,導致供應鏈系統紊亂。第二,通過直接影響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他中間品的各級供應保障和成本、勞動力供給和成本以及資金保障和融資成本等,擾亂產業分工體系,引發供應鏈遲緩、不暢或者中斷,沖擊制造體系及其供應鏈體系的穩定。第三,通過間接影響生產性服務業的中間投入,這種影響雖是間接的但是長遠的。由于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嵌入供應鏈各環節,產業鏈長層次多且復雜,某一環節一旦出現問題,如違約、失信,延遲、中斷,拖欠、壞賬,損失、破產,等,將通過轉移機制傳導到供應鏈下游相關企業,風險傳遞環環緊扣引起連鎖反應并放大風險,引起供應鏈整體風險。生產性服務企業長期建立起來的技術經濟聯系,一旦受到沖擊或破壞,恢復起來需要高昂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3.重要行業供應鏈遭受扭曲和重構秩序的困擾
在關鍵核心技術與高新技術產品市場的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一方面,以美、英、德、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以振興制造業為目標的再工業化加快進程;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國家為了保持對關鍵核心技術、高新技術產品市場的控制與霸主地位,通過發動貿易戰、科技戰等手段來遏制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疫情爆發以來更加不擇手段對中國科技企業實施打壓與制裁,引致供應鏈遭受扭曲的困擾。尤其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以及科技服務業為代表的全球供應鏈面臨重構主導能力的激烈競爭,觸發新一輪全球供應鏈重構秩序。對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分工的中國制造來說,當受到關鍵核心技術牽制時,供應鏈面臨遭遇“卡脖子”的風險,也會波及到供應鏈核心企業的供應商選擇。由于產業分工高度專業化、產業鏈高度全球化,產業鏈上中下游分布在不同國家、不同區域受到的影響程度不同,對全球企業經營、經濟活動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牽制和障礙,從長期來看,這意味著供應鏈網絡結構可替代性的組合成為可能的選擇。如何在面臨全球供應鏈重構秩序的激烈競爭中獲取主導地位、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成為當務之急。
四、供應鏈自主可控策略與路徑
有效防范與管控供應鏈面臨的脆弱性風險的重要途徑在于加強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建設。自主可控能力體現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能力、掌握關鍵核心技術能力和可持續生存能力、營運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等方面。探索我國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建設的策略與路徑,防范供應鏈脆弱性新型風險,應著重建立自主可控供應鏈戰略,打造雙循環供應鏈模式,發揮供應鏈柔性與敏捷性優勢,增強供應鏈韌性與魯棒性,推進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創新供應鏈管理模式,優化供應鏈創新發展生態,從而提升我國供應鏈的自主可控能力。
(一)建立自主可控供應鏈戰略
建立自主可控供應鏈戰略主導我國供應鏈網絡建設十分必要和緊迫。我國企業尤其是重要行業領域的核心企業應深入反思制訂供應鏈的戰略規劃,重構供應鏈危機應對體系。順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全球產業分工深度調整態勢,立足中國經濟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正視在全球供應鏈中部分核心環節和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現實,分行業做好供應鏈戰略設計和精準施策,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安全可靠的供應鏈。
第一,依靠供應鏈優勢鍛造長板增強自主可控能力。我國供應鏈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其必要性。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對全球經濟和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力逐步提升。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供應鏈網絡的中心,中間品進出口占到相當高的比重[40]。根據WITS數據庫顯示,全球近200個經濟體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占比平均達到21.7%,經濟比重和經濟增長率超過世界平均經濟增長速度,表明中國經濟在國際循環中占據重要地位并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我國在市場規模、產業體系以及配套能力等方面形成了比較優勢,在通訊、新能源、重大裝備等諸多領域具有競爭優勢,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鍛長板將優勢轉化為自主可控能力。
第二,提升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補齊短板是當務之急。我國供應鏈在全球供應鏈中部分核心環節和關鍵技術面臨的困擾決定了其緊迫性。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自由貿易的碎片化趨勢愈加顯現,供應鏈還存在諸多“斷點”“堵點”,直接沖擊我國的供應鏈安全穩定。高科技領域高度依賴進口導致的“卡脖子”短板現象已經顯現[41],從這個意義上最大的風險和短板就是一些重要領域還缺乏關鍵核心技術,部分核心環節和關鍵技術受制于人,通過補短板提升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是當務之急。
(二)向雙循環供應鏈模式轉型
在新發展格局下,如何實現從傳統模式向國內國際雙循環供應鏈模式轉型是亟待探索的現實問題。要從供應鏈安全和制定供應鏈規則的角度引導國內國際資源的全球配置,利用國際和國內兩種資源,拓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變革與引導產品內分工體系,將供應鏈從傳統依附型轉變為自主型,增強供應鏈的主導性和完整性,建立雙循環供應鏈網絡。
第一,以消費變革為核心,以新消費推動國內大循環加快升級[42]。國內市場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立足于國內供應鏈大循環體系,激發擴大終端產品的國內大市場需求,發揮中國國內的市場規模優勢。面向滿足國內需求的終端產品,以終端產品為共同經營主線,以核心企業為主導,建立國內需求導向的供應體系、生產體系和流通體系。針對供應鏈存在的堵點,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解決供應鏈結構性問題,著力打通國內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形成產品內分工的內循環供應鏈體系,實現從生產到消費的國內大循環。
第二,以關鍵核心技術產品為主線,發力科技創新,以培育發展新技術、新產品和新興產業為突破,科學謀劃和參與國際經濟循環,主動參與國際循環供應鏈網絡。以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企業為主導,形成關鍵核心能力的自備替代準備,“卡脖子”技術的研發準備。立足于國內供應體系、生產體系和流通體系,優選國際供應商組成、優化國際供應商的區域分布,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供應鏈網絡。
第三,建設國際國內雙源供應商與采購渠道,形成以國內渠道為主國際渠道為輔的多元供應商策略,重視供應商合理化選擇,針對國際獨家供應商或供應商高度集中的情形,適度平衡對供應商的依賴度,優化集中主力供應與備份供應共存的模式。著力促進國內經濟區域之間產業分工協作,疏通經濟區域之間的供應鏈梗阻與斷點,激活產業鏈上中下游的行業龍頭企業,發揮供應鏈核心企業網絡構建的主導作用。
(三)鍛造供應鏈韌性與鏈魯棒性
從應對新冠疫情和國際經濟環境變換的實踐表明,統籌兼顧供應鏈成本與效率、應變與穩健越來越重要。科爾尼(2020)認為一個健全的現代供應鏈應該具備強固(Reliable)、韌度(Resilient)、抗風險(Risk-proof)和敏捷性(Responsive)“4R”特性。強調了供應鏈韌性、魯棒性、敏捷性與抗風險的統一。因此,企業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統籌均衡供應鏈的柔性和敏捷性、增強供應鏈韌性與魯棒性。在發揮柔性與敏捷性優勢的同時,增強供應鏈的韌性與魯棒性,保障供應鏈的穩定和安全。
第一,改善供應鏈的柔性和供應鏈敏捷性能力以使其優勢充分發揮。改善供應鏈柔性重點聚焦適應顧客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提升面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分析預判、創新變革和應對能力,實現產品多樣化適時調整轉換。改善供應鏈敏捷性重點聚焦適應面向全球化的市場從基于成本競爭轉向基于時間競爭,在敏捷制造技術的支持下,實現一體化的供應鏈協同運作。以應對產品生命周期縮短、更新換代加快,快速響應準時供貨。當前,改善供應鏈的柔性和供應鏈敏捷性尤其需要客服過度追求準時性、精益化、低成本帶來的缺乏韌性和穩定性,從而形成脆弱性的弊端,建立供應鏈安全穩定風險防控的底線思維。
第二,鍛造供應鏈魯棒性與韌性能力以消減供應鏈脆弱性,應對供應鏈安全穩定風險。供應鏈具備魯棒性是在異常和危機情況下生存的關鍵能力。所謂供應鏈魯棒性即供應鏈的穩健性,反映供應鏈的穩固程度,與供應鏈的韌性密切相關。當面臨各種內部或外部風險因素擾動時,表現出抗沖擊的韌性,具備動態調節、迅速恢復穩定的供應鏈渠道及其網絡結構并穩健運作的能力。譬如通過強化重要供應商/客戶關系的穩定性,探索實質性可執行的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機制,創新有效庫存成本分攤和利益補償機制,增強在預警時期應對波動的庫存緩沖韌性以保持供應鏈的穩定性。
第三,提升供應鏈復原能力對增強魯棒性有著顯著的支持作用,可消減供應鏈脆弱性[43]。針對供應鏈脆弱性的來源因素,建立具有復原能力的供應鏈風險反饋控制系統。根據不確定性可能的變化范圍,控制引致風險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擾動底線邊界(閾值)。通過建立控制對象模型、控制指標體系、信息感知系統,運用知識庫及大數據計算,智能反饋機制、智能決策機制,通過人-機-網絡一體化系統界面實現運作。在面對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以及不確定性條件下,具備漸進緩沖功能以保持韌性,增強動態調節能力和自我恢復穩定性能力。
(四)推進供應鏈數字化升級
全面深化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升級是提升供應鏈的現代化水平的核心驅動力。也是增強供應鏈應變能力以消減供應鏈脆弱性的重要途徑。通過供應鏈數據驅動—功能屬性激活—協同能力提升—敏捷性觸發—魯棒性增強的動態過程,使供應鏈企業之間、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鏈接更加緊密,使企業各業務單元之間的銜接更加協調,有助于提升企業供應鏈敏捷性[44]和穩健性,使信息流、商流、資金流和物流更加潤滑順暢。
基于大數據平臺,充分利用數據資產有效提升供應鏈管理決策水平和運作效率。通過數字化技術改進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的協作,改善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借助數字化技術,推動供應鏈業務流程變革,暢通供應鏈業務流程,增強供應鏈信息互動性和預見性,提高預測與預警機制效能,消減各種擾動因素通過供應鏈傳導并逐級放大引致的脆弱性風險。
(五)優化供應鏈創新發展生態環境
以供應鏈創新轉型為主線,推動供應鏈運作可視化、智慧化、協同化創新實踐的生態環境。第一,供應鏈運作可視化。利用先進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應用于供應鏈信息流、資金流、物流在各價值活動的業務環節,實現跟蹤、定位、引導、虛擬-增強現實、可視化,提高透明度。譬如抗疫實踐表明,信息可視化建設程度越高的企業受到疫情的短期沖擊越小[45],有利于克服商流、信息流障礙,避免由于疫情隔離造成商務活動延遲或中斷。第二,供應鏈決策智慧化。供應鏈管理正在朝著智慧供應鏈的趨勢發展。供應鏈與互聯網、物聯網實現深度融合,以基于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應用為重要特征,構建高效、智能和人性化的智慧供應鏈生態。第三,供應鏈運作協同化。供應鏈的參與方多元化,處于不同行業的供應鏈節點企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都是價值創造者和傳遞者,基于價值鏈整合有機地組織在一起、共同建立供應鏈跨行業協同運作生態圈。建立資源共享、價值共享、互動協同機制,實現核心能力、協作能力、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的協同,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供應鏈脆弱性風險。
五、結論與展望
過去較多文獻側重關注認識供應鏈風險的成因、識別、評價以及管控策略的選擇,主要聚焦在微觀層面的企業供應鏈管理的運營職能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我國供應鏈安全穩定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聚焦供應鏈脆弱性新型風險及自主可控能力建設的策略與路徑進行研究,得到如下結論:第一,供應鏈的脆弱性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環境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發展情境下,我國供應鏈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主要問題是供應鏈脆弱性問題,其本質特征是在全球供應鏈中主導權不足、自主可控能力不強,因此面臨的突出風險是同供應鏈脆弱性密切相關的新型風險,波及供應鏈的安全穩定。第二,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的擾動形成傳導效應與疊加效應,對我國企業參與引導全球供應鏈分工產生負作用、尤其對我國現代制造業的供應鏈生態系統面臨破壞性的擾動,引致全球供應鏈遭受扭曲和重構秩序的困擾。第三,我國供應鏈的安全穩定和自主可控能力建設關系到國家現代產業鏈體系的安全和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有效防范與管控供應鏈面臨脆弱性風險的重要途徑在于加強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建設。應著重建立自主可控供應鏈戰略,打造雙循環供應鏈模式,發揮供應鏈柔性與敏捷性優勢,增強供應鏈韌性與魯棒性,推進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優化供應鏈創新發展生態,從而提升我國供應鏈的自主可控能力。
本文克服了以往文獻研究的局限性,以理論闡述與經驗事實為基礎建立了概念框架,拓展和豐富了相關研究結論,為當前供應鏈脆弱性新型風險防范提供了理論和經驗證據。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為優化和穩定供應鏈、增強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提供理論支持和學術意見。本文也存在不足之處,受篇幅所限以定性分析為主,未來的研究需要考慮不同產業情景下,結合我國重點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制造業等,針對特定供應鏈面臨的突出問題進行定量分析與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1]何黎明. 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與現代化[J]. 供應鏈管理, 2021(1): 7-13.
[2]宋華, 楊曉葉. 供應鏈風險管理文獻綜述[J]. 供應鏈管理, 2020(3): 33-45.
[3]IVANOV D.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resilience in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M].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2018.
[4]WAGNER S M, BODE C.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along several dimension of risk[J].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2008, 29(1): 307-325.
[5]ABDEL BASSET M, GUNASEKA RAN M, MOHAMED M, et al. A framework for risk assessment,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economic tool for quantifying risks in supply chain [J].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019, 90(1): 489-502.
[6]HAMDI F, GHORBEL A, MASMOUDI F, et al. Optimization of a supply portfolio in the context of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2018, 29: 763-788.
[7]PAKSOY T, ALIK A, YILDIZBAI A, et al. Risk management in lean & green supply chain: a novel fuzzy linguistic risk assessment approach[M]//Lean and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pringer, 2019: 75-100.
[8]TSIAKIS P, SHAH N, PANTELIDES C C. Design of multi-echelon supply chain networks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J].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2001, 40(16): 3585-3604.
[9]DIABAT A, GOVINDAN K, PANICKER V V.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and its mitigation in a food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2, 50(11): 3039-3050.
[10]CHANG W, ELLINGER A E, BLACKHURST J. 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supply chain risk mitigation[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15, 26(3): 642-656.
[11]FAN Y, STEVENSON M. A review of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defini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2018, 48(3): 205-230.
[12]TANJUNG W N, HIMAWAN S, HIDAYAT S. Fuzzy house of risk to manage supply chain risk[C]//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Bandung: IEOM Society International, 2018.
[13]LUCKER F, SEIFERT R W, BICER I. Roles of inventory and reserve capacity in mitigating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ris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9, 57(4): 1238-1249.
[14]王靜, 陳希. 考慮供應鏈中斷風險的制造商風險應對方案研究[J]. 工業工程與管理, 2019, 24(3): 27-34.
[15]TANG C S. Perspectives in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6, 103(2): 451-488.
[16]WU K J, LIAO C J, TSENG M L, et al. Toward sustainability: using big data to explore the decisive attributes of supply chain risks and uncertainti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142(2): 663-676.
[17]李隨成, 崔賀珵, 石霞. 供應風險緩解策略選擇研究[J]. 軟科學, 2020(5): 50-56.
[18]HARIHARAN G, SURESH P, NAGARAJAN S. Supply chain risk mitigation strategies and its performance of S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018, 119(5): 741-749.
[19]CHRISTOPHER M.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cost and improving service[M]. London: Financial Times/Pitman, 1998.
[20]PECK H. Reconciling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y, risk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06, 9(2): 127-142.
[21]SVENSSON 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vulnerability in firms inbound and outbound logistics flo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2, 32(2): 110-134.
[22]寧鐘. 供應鏈脆弱性的影響因素及其管理原則[J]. 中國流通經濟, 2004(4): 13-16.
[23]JUTTNER U.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understanding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from a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5, 16(1): 120-141.
[24]CHRISTOPHER M, LEE H. Mitigating supply chain risk through improved confid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4, 34(5): 388-396.
[25]劉希龍, 季建華. 基于多源供應的彈性供應網絡研究[J]. 工業工程與管理, 2007, 12(3): 8 -12.
[26]劉彥平. 供應鏈脆弱性和風險管理策略研究[J]. 現代管理科學, 2009(11): 104-106.
[27]SVENSSON 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vulnerability in supply cha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0(9): 731-749.
[28]BLACKHURST J, RUNGTUSANATHAM M J, SCHEIBE K, et al.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 network based visualization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approach [J].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2019, 24(1): 21-30.
[29]劉家國, 周粵湘, 盧斌, 等. 基于突發事件風險的供應鏈脆弱性削減機制[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 2015(3): 556-566.
[30]SERHIY Y PONOMAROV, MARY C HOLCOMB.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supply chain resilience[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9, 20(1): 124-143.
[31]CHRISTOPHER M, PECK H. Building the resilient supply cha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04, 15(2): 1-13.
[32]HOSSEINIS MORSHEDLOU N, IVANOV D, et al. Resilient supplier selection and optimal order allocation under disruption ris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9, 213(7): 124-137.
[33]王玲, 褚哲源. 供應鏈脆弱性的研究綜述[J]. 軟科學, 2011(9): 136-139.
[34]劉家國, 施高偉, 盧斌, 等. 供應鏈彈性三因素模型研究[J]. 中國管理科學, 2012(11): 528-535.
[35]BOGATAJ MARIJA, BOGATAJ DAVID. Measuring the supply chain risk and vulnerability in frequency spa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7, 108(1-2): 291-301.
[36]馮耕中, 孫煬煬. 供應鏈視角下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7): 42-49.
[37]劉志彪.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特點、風險及政策建議[J]. 東南學術, 2020(3): 42-47.
[38]新華網.新冠疫情或將導致全球失去10年發展成果[EB/OL].(2021-03-2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26/c_1127259178.htm.
[39]王高鳳, 鄭瓊潔. 產業鏈視角下新冠疫情對我國制造業的影響研究[J]. 產業經濟評論, 2020(7): 44-58.
[40]徐奇淵,楊悅珉, 祝修業. 應對全球供應鏈“灰犀牛”沖擊[J]. 財經, 2020(5):19-21.
[41]張學良, 楊朝遠. 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N]. 光明日報, 2020-07-07(16).
[42]本刊編輯部.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統籌推進現代流通體系建設觀點綜述[J]. 中國流通經濟, 2020(11): 3-17.
[43]王海軍, 譚潔, 王天雨. 供應鏈復原能力與供應鏈競爭力關系研究: 基于動態能力的視角[J]. 管理評論, 2018(11): 223-233.
[44]孫新波, 錢雨, 張明超, 等. 大數據驅動企業供應鏈敏捷性的實現機理研究[J]. 管理世界, 2019(9): 133-151.
[45]蔡臨寧, 葉楊慶, 熊雪珍. 新冠肺炎疫情對供應鏈影響的實證研究[J]. 供應鏈管理, 2020(4): 24-32.
Research on Vulnerability Mitigation and Autonomous Control Strategy
of Supply Chain in China
Shen Xiaoping
(Economics School,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vulnerability risk of the Chinas supply chain has become prominent. The supply chain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in its autonomous contro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ausing the current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y risk,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conduction effect and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divis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 the destructive disturbance faced by Chinas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ecosystem and the trouble caus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distortion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strategies and paths to mitigate the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ies and strengthen its autonomous controllability, such as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supply chain strategy, create a dual circulation supply chain mode,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flexibility and agility, enhanc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robustness,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innovate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 and optimize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cology.
Key words: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y; risk mitigation;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strategies and paths
(責任編輯: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