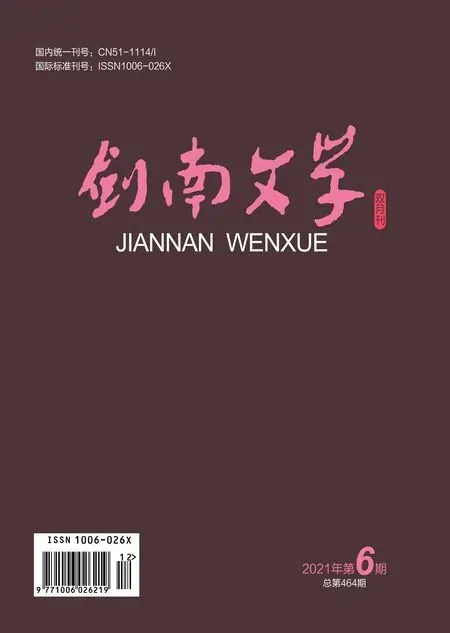豉油雞
□安昌河
1
就靠這一個菜當家,他們年收入就上百萬!王環視了一眼這家飯店,雨也跟著他的眼神打量了一眼四周。店鋪不大,鋪陳簡單,青磚地面,粗瓷大碗。飯點還沒到,店堂里人已坐滿。
菜上來了,一只整雞,熱氣騰騰,香氣四溢。
你爸爸吃的時候它還不叫豉油雞,叫蒸鯤雞。那會兒我們破了什么大案,或者送走人,會特別叮囑老肉給我們做。你爸當時吃的時候,是個什么情況呢……說到這里,王端起了酒杯,借機觀察雨的神情,他有點兒吃不準雨這個時候找他的真實意圖。雨說他想知道他父親的最后時光,還特別想知道他父親最后一餐都吃了什么。
王放下酒杯,說,當時我去問你爸爸,最后一餐想吃點什么。他想了半天,想不出來。我說,那就吃個蒸鯤雞吧。他說好。我就去伙食團,跟老肉說,你多蒸一只雞。我把蒸鯤雞送到你爸爸跟前,他吃了一點就不肯再吃了。
王講這段往事的時候,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雨的臉,見雨紅了眼圈,心頭那懸著的東西也慢慢落了地。
飯店的老板肉從外頭回來,見了王,肉做出驚喜的樣子,說好久沒見到王了,說他老丈母去世了,老婆留下辦理后事,他先回來打理生意。
王向肉介紹雨,說這是老朋友的兒子,請他品嘗愛城特色,推薦了水蜂子、藿香魚……他最后選了豉油雞。
真是太榮幸了!肉將王自帶的茶坪老燒換成了他珍藏的茅臺,還特別鄭重地跟雨講,沒有王,就沒有這道豉油雞。當年我爸爸坐班房出來,不知道干什么,王說還是老本行嘛。于是我爸爸就開起了館子,主打豉油雞!
那會兒還不叫豉油雞。王糾正說,那會兒叫蒸鯤雞。王比畫說,“鯤”是形容這雞之大,當然也有完整的意思。館子才開起那會兒,門可羅雀,他爸爸打起了退堂鼓。我說你做的豆豉油不錯,看能不能把豆豉油和蒸鯤雞整合一下,豉油雞就這樣出爐了!
寒暄一陣,肉忙別的事去了。
王倒了一杯酒,要雨嘗一嘗,哪怕一口。雨就抿了一口。咋樣?王問他。雨說,挺好的啊。王拿指頭磕磕酒瓶,真的假的?雨一笑。王也一笑,輕嘆一聲,說,這就是他和老肉之間的差別。老肉可是個實誠人啊,當年受了那么大委屈,到死都沒有講出來。這個肉,他總覺得比他爸爸聰明,其實他做的豉油雞很空洞,就像沒有靈魂。
空洞?靈魂?雨覺得這兩個詞語頗耐人尋味。
豉油雞的做法重點在雞,更在油。黑豆豉剁碎,拿菜油煉,豆豉煉干,油濾出。雞用滾水淋,皮緊肉縮了用牙簽將肉厚實的地方戳一戳,趁熱涂上豉油,放冰箱冷藏,每三小時涂一次,一個對時后上鍋蒸。上氣一小時,涂最后一次油,燜三小時,大功告成。肉就是這么做的,做得也很認真。但是缺少點題,沒有升華,就像一篇文章最終沒有表現出意義。
你能做?雨問。
我知道靈魂所在。王將茅臺推到一邊,拿過自己的茶坪老燒斟滿一杯,小啜一口,說,什么時候他給我喝真茅臺了,我就告訴他豉油雞的靈魂在哪里。在哪里呢?在最后那道涂油上!那可不單純是豉油,而是番茄醬和蜂蜜混合豉油熬制的濃油。這樣做出的雞毫無油膩感,味道更加鮮美可口,富有層次,就像一篇千轉百回的漂亮文章!
你可真是個美食家啊!雨說。
治大國若烹小鮮,做菜也給了我很多破案的靈感!王放下筷子,看看雨,送走你爸后沒兩年我就退休了,但是每年都有像你這樣的家屬來找我。因為我們之間建立了一種奇妙的關系,所以我從來不拒絕,也不擔心會遭到報復。一切早都結束了,大家對此都很清楚。見面,不過是因為心頭還有些東西浮在上面,沉不下去。那么你呢,還有什么嗎?王看著雨,目光明亮,有著一眼到底的銳利。
我想知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土鎮是否發生過命案?
王兩眼緊緊盯著雨,什么意思?
那天露水很大,天不亮我就趴在五道河三灣堰塘埂子上的草堆里,手握一根兩米多的長火。我渾身潮濕,癢得難受,我一動也不敢動。我要殺的人出現了。我瞄準了他,扣動了扳機。轟一聲槍響,他栽倒在地上。時至今日,槍聲好像還在我耳邊回蕩,硝煙還是那么刺鼻。
王的目光一直在雨的臉上,錐子一樣想要鉆進他的內心。雨卻像開玩笑,神情輕松,仿佛這并不是一件真實發生過的事。我這不是第一次跟人打聽,都說不光土鎮,整個愛城,在那個時間段根本就沒死過人。可是我卻怎么也輕松不起來,因為隨著時間推移,就像所謂的“真相浮出水面”,那些事情越發歷歷在目,清晰無比。我似乎真的是殺過人啊!雨的神情慢慢凝重起來,會不會我殺了人,有人把尸體藏了起來?
二○○○年四月,那會兒我還在刑警隊長的位置上呢。王嘆口氣,說,那可是個清靜祥和的春天啊。
2
一九九九年臘月,雨媽帶著雨從廣州回到秦村。雨媽挎著裝滿香燭紙錢的提籃,要雨跟她一起去祭墳。雨的語氣冰冷,說我不去。雨媽沒敢催逼,害怕又像上回那樣弄出事來。
上回,雨媽一定要雨跟自己去見雨爸最后一面,說你就滿足他最后的愿望吧。雨說他怎么還有臉提這樣的愿望?雨媽哭訴道,他是你爸爸呀!雨說我沒有爸爸!雨媽說沒有爸爸你是哪里來的?雨折身就摸出把刀來,一刀剁掉左手食指,剔骨還父,還要不要命?要的話我馬上還給他!那天雨爸誰也沒見著,他在被押往刑場的路上,索性閉上了眼睛。
拜完雨爸的墳頭,雨媽就帶著雨去了五道河外公家。走到半道上,雨媽突然淚如雨下,抽噎得蹲在地上走不了道。
沒等雨爸頭七過完,雨媽就帶著雨去了廣州。雨的姨父在廣州開服裝廠,給他聯系了復讀的事。校長建議雨將戶口遷移過來,方便來年的高考。于是,這差不多一年時間,雨媽就一直往返于廣州和土鎮,給雨辦戶口遷移,辦轉學的手續。姨娘總是語重心長地給雨說,這天底下你誰都可以辜負,就不能對不起你媽!
見到外公,外公把雨拉到身邊,輕輕撫摸著雨那續上的食指,給他講,要時常揉揉,頭三年是恢復功能的最好時機。雨的指頭恢復得很好,這虧得雨媽從外公那里耳濡目染了不少醫學常識。醫生都在夸她,說處置得當,給他們爭取了時間,創造了條件。
外公是有名的草藥先生,擅長婦兒科,每年過年都有不少經他救治痊愈的人前來拜年。外公家簡直就是個樂園,不光舞獅隊喜歡前來討彩頭,小伙子大姑娘也愛前來看熱鬧,吃糖果,見識那些先一步來到這個家里的洋玩意,比如大彩電、DVD、卡拉OK……
這些洋玩意是姨父帶回來的。外公不太見得慣雨爸,但視姨父為己出。每年過年,姨父都會早早歸來,帶著時新玩意兒和煙酒糖,將外公的這個大院子變成整個村莊的中心。今年盡管姨父沒有回來,但時新的玩意兒還是讓姨娘帶了回來,日本產的跳舞毯。只是都不知道該怎么接線,想嘗試又不敢輕舉妄動,怕搞壞了。這時候有個好聽的聲音說,你們家不是有個高材生么?
雨正躺在床上,羞恥,悲傷,苦痛,憤怒……他很想破壞點什么發泄發泄,卻又無處下手。
姨娘一到家就拉著雨媽到一邊,沒幾句話雨媽就抹起了眼淚。雨看在眼里,心頭愧疚,覺得是自己惹她慪氣。兩姊妹交完心,姨娘摸出手機,爬上樓去給姨父打電話。雨悄悄跟在她身后,聽得她說,那個人保證要娶她,她也覺得人家好,就因為人家給她做飯了,變著花樣做……是啊,我覺得她瘋了!
外公過來跟雨講話,語重心長。
你還小,就像一棵小苗,一點火星。你媽媽就是因為擔心你會把自己這棵小苗毀了,把自己這點火星吹滅了,她才事事擋在前頭,事事隱瞞著你。你還小,還承擔不起捍衛她的責任。你的小就像外公的衰老。外公現在是一盞就快要枯滅的油燈,只能守住這個家,讓你們的心里有個念想,身子有個歸宿。那么你呢?你要好好學習,要把自己的性命和自由看得比泰山還重。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負!
就在此時,雨聽見樓下的院子里有個女孩子的聲音在喚他:雨,你咋個像個小姐一樣躲在繡樓里呢?還聽見姨娘在慫恿說,接到喊,他肯定有辦法。又傳來一陣姑娘小伙們的笑聲和起哄。
去跟他們耍吧!外公說,春節嘛,本來就是屬于你們年輕人的。
雨成功地連接好了跳舞毯的線纜,做了演示。在炫目的畫面和攝人心魄的音樂節拍中,他像英雄一樣受到大家的追捧。那天晚上,雨也被喚他的那個女孩子深深吸引,她叫梅。雨就像一只電力充沛的熒光燈,不僅自己渾身雪亮,也叫梅晶瑩剔透。
3
梅讀土鎮中學,成績一般,恐怕考不進大學。雨媽擔心她會成了雨的枷絆,外公覺得無所謂,只要相互喜歡,只要是用對的方法喜歡。外公是這個家庭中第一個承認他們關系的人,梅很感激,她跟雨講,你在廣州放心,我每個禮拜都要回來,有空就過來看外公。
到了學校,雨每天都會給梅寫信。雨媽起初很擔心這會影響到雨的學習,卻沒想到他的成績越來越好。眼見一所好大學就在前頭等著了,卻突然出了事。
那天雨放學,剛走到來接他的雨媽跟前,就被一群人圍在中間暴打。領頭的是校長的女人,他們撕碎了雨媽的衣服,罵雨媽是小三,是爛貨。接著,姨父掉進了一個圈套里,資金鏈斷了,被高利貸債主攆得東躲西藏。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一個更可怕的消息傳來:外公跌了跤,已經講不出話來。
雨說,咋是梅爸打電話來呢?咋不是梅打電話來呢?
姨娘很生氣,說這都什么光景,你心里只有那個梅嗎?
安葬了外公,姨父繼續躲債,雨媽必須陪姨娘回廣州收拾爛攤子。雨堅決不回,他留在五道河,住在外公那個大宅子里,他誰都不想見,他的世界只剩下了梅。
雨只在葬禮那天見了梅一面。梅的表現讓雨感到意外,因為她的臉上并沒有什么悲傷,自始至終都表現得像個局外人。他走到她身邊,剛喚了聲梅,眼淚就糊住了眼睛。梅很淡然,你回來了哇。雨說,我給你打了好多電話,你都沒接。梅說,老師管得緊。
這時候有人吆喝雨:搞啥呢,出殯了!
送殯隊伍浩浩蕩蕩,都在感嘆,說人做到這個份上真是了不起了,好多非親非故的都三叩九拜地當起了孝子賢孫。但是梅沒有出現在隊伍里,中午吃喪伙飯的時候她也不見。大家一邊喝酒,一邊訴說著與亡者的交情,感嘆生死無常。
大開靈,八音樂器從午后就開始敲響了,八個道師合力將外公的亡魂送往極樂世界。送亡路十分遙遠,要從午后持續到次日黎明。八個道師一起唱誦經文,恭請沿途的神祇,向他們通報亡者生前諸事,焚香祈愿,請五方五帝滿天神佛加持,以保證順利通關……
雨在這天晚上的表現很不好,該下跪的時候他站在那里愣神,不該跪的時候他跪在那里不曉得起身。在燒紙的時候,他還點燃了道師的法袍,嚇得年邁的道師哇哇亂叫,法器丟了老遠。
第二天,雨去了梅家,梅媽說梅昨天下午就回學校去了。雨轉身要走,梅媽問,你媽媽是不是跟那個校長有那個事?這個人呦,送點錢就是了嘛,咋還把自己送去了呢。又一聲嘆息后,她問,你是不是被開除了?
雨說沒有,只是今年不高考了。
梅媽憂心忡忡地說,也不曉得今年梅考不考得上喲。
雨說,我可以輔導梅的。
梅媽瞄了雨一眼,這個眼神叫雨心頭一凜。梅媽說,我正要講這個事情呢,梅正全心全意地迎接大考,你如果想為她好,就不要去分她的心,離她遠遠的吧!梅媽語氣冰涼生硬,叫雨都不敢看她。
梅就像是從雨的世界消失了。沒有了梅的世界,就沒有了顏色,沒有了聲音。雨不甘心世界就這樣坍塌了,他決定明日就去土鎮,無論如何也要找到梅!但是傍晚他就意外地看見了梅。梅正從小賣部出來,她的身后跟著一個男的。這個男的年歲跟雨差不多,但穿得比他時髦,羽絨服、牛仔褲、馬靴,典型的操哥裝束。
操哥撕開一塊巧克力,往梅嘴里喂。梅咬了一口,輕輕一晃肩,卸開操哥搭上肩的手。
梅看見了雨,目光毫無表情地飄過,就像不認識他,在操哥的說笑聲中,搖搖擺擺地從雨跟前走過。
雨完全記不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中的,也記不得這一夜是怎么度過的。他喝了很多酒,外公那張大床上全是他的嘔吐物,惡臭難聞。
雨洗了個涼水澡,換了身干凈衣裳,他要去找梅,梅卻自己來了。她站在外公家門口那棵大核桃樹下,手里扯著核桃葉,伸到鼻子底下聞那特別的香氣。
梅一眼瞥見他,說,我們分手吧。
好的。雨說。
那我走了。梅轉身就走了,走過田埂,身影倒映在水田里,幾只鳥兒從她頭頂一縱一縱地飛過,鳴叫很歡快。她走過一片麥田,半個身子淹沒在一片綠里。
梅前腳剛走,梅媽就來了,一見雨就兩眼淚花。
那娃姓雷,是年初從愛城轉學過來的,纏上了梅。梅媽說,梅還小,學業為重,將來考不上大學就只有回家搓泥巴。雷說沒關系,他家有后門也有錢。梅媽說梅年前認識了個娃兒,那個娃兒很喜歡梅的。雷拍桌子亮巴掌,說如果老子得不到梅,那么誰都得不到……我們現在是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你是個好娃,梅媽上前一步,拍拍雨的肩膀,你成績好,將來一定很有出息,要找啥樣的人都有,梅其實也配搭不上你,何況現在還有那么個家伙擋在那里。你莫去找梅了,聽嬢嬢的勸,快回廣州找你媽!
4
多年前,外公出錢,給雨爸買了輛小四輪,專門往工地拉砂石。砂石來自愛河。土鎮下游的灣灘,淘金棚到處都是,遍河壩都是窟窿眼,挖出的砂石,先洗金,再賣砂。賣砂的錢保人工,洗出的金就等于賺了。
灣灘落在一個叫李獨娃的手里,他有二十來個兄弟,專門吃詐錢,淘金的要給,拉砂的也要給。雨爸要跟李獨娃講理,李獨娃的手下摸出刀子,說你先跟它講。
雨爸找到獨眼龍,說,獨眼龍,給我整兩根火!獨眼龍說你不是有一根么?雨爸說長火不好當面講道理,我要短火。
李獨娃一伙人正在歌舞廳里唱卡拉OK,每個人都摟著個小姐。雨爸慢條斯理地走過去,把燈挨著全部摁亮,有人問他搞啥子,他說,我找李獨娃。李獨娃說,哪個狗日的沒大沒小?雨爸摸出短火,照著李獨娃大腿就是一火,然后再摸出一根,抵在李獨娃的腦殼上,喊了他一聲,李獨娃。李獨娃趕緊應聲,說,哎,咋個嘛。
雨爸就這樣成了愛河里淘金洗沙的老大,雨媽也不再種地,過上了雨爸當年追求時許諾的日子。只是從這以后,不管是去哪里,哪怕是在外公家吃團年飯,雨爸的褲腰上都別著兩根短火。有一回他喝多了,跟一個親戚扯酒筋,竟然掏出一根拍在桌上,問人家選哪樣,氣得外公一把抓過來丟進了冬水田。第二天雨爸酒醒了,他摸出一疊錢,問,有誰肯幫忙打撈起來?有外公鎮在那里,誰也不敢。雨爸也不好下水去撈,他已經擱不下面子了,就又去找獨眼龍,再做一根。
雨見過獨眼龍給雨爸特制的短火,木柄的,雙管雙發。記得有人問雨爸,你就不嫌這玩意兒沉?要不要大黑星嘛?雨爸說,那是軍火,我這是鎮堂子的。
有一回雨爸在愛城,正好撞上搞“零點行動”。雨爸打開后備箱,掀開皮箱,里頭全是錢。雨爸說,看見沒有,我如果不采取措施,被人打搶了咋辦?
沒過幾天,雨爸又去獨眼龍那里弄了兩根。但凡是雨爸辦的酒席,獨眼龍都會坐上席,雨爸說他是自己的武器專家。
現在,雨站在獨眼龍跟前,手里提著雨爸平常掛在門旮旯的那根長火。
幫我裝個火機。雨說。
火機通常有兩種,一種叫“牛扒背”,也叫“啄啄火”,很簡單,就是在藥膛上鉆個眼兒,叫“藥眼”,用的時候先往槍管里填藥裝砂,再往“藥眼”上倒少許黑藥,拿出“引火泡”,舌頭輕輕舔一下,粘在“藥眼”上,叫上扳機,瞄準,勾動扳機,扳機擊打在“引火泡”上就完成了射擊。另一種叫“罐罐火”,也叫“壇壇火”,點火裝置是個鐵帽。因為密封性好,不怕雨,也不容易受潮,安全性能較高,因此相比“啄啄火”要高檔一些。但是制作“罐罐火”技術要求高,必須動車工。
獨眼龍是不屑做“牛扒背”的。他有一套起眼車絲的工具,雖然速度慢,但慢工出細活。
雨爸在土鎮叱咤風云的時候,獨眼龍跟在屁股上也算個人物。雨爸死了,他也就回了秦村,幫人看管山林。
獨眼龍從雨手里接過那根長火,問,原來那個罐罐呢?
原來那個罐罐是被雨爸敲掉的。他在外頭找了女人,一番吵鬧后,他竟然沖雨媽動起了手。雨摸出了那根長火,瞄準雨爸。雨爸說,你連藥都沒裝,比起好看啊?趁著雨一愣神,雨爸一把抓住槍桿抬向空中。槍響了,把房頂沖了個窟窿。
雨掏出錢來,問,要多少錢?獨眼龍沒接錢,順手將長火往墻根上一靠,說,去買兩斤肉,再買兩瓶酒、兩包煙。
等雨買了酒肉回來,看見長火還靠在墻根上,獨眼龍連工具都沒有拿出來,他倒是蒸了一鍋米飯。肉炒好了,端上桌子,獨眼龍喊他吃,雨也沒客氣,反正是自己掏的錢。獨眼龍喊他喝酒,他就喝,遞給他煙,他也抽。
獨眼龍說,你爸爸是個混蛋,徹頭徹腦的混蛋!
雨不吱聲,心里卻是極其認同的。雨爸表面上答應了雨媽,要跟那個女人斷了關系,卻又在背后給那個女人的丈夫下鬧藥。雨媽一直不肯接受這個事實,因為像他那樣耍刀耍槍的人,咬銅吃鐵的性子,要一個人死,咋個會懦弱到用鬧藥呢?這一定是那個女人的主意,是她親手下的鬧藥也講不清。只要雨爸講出實情,罪過再大,他也頂多算幫兇,判個死緩,不會立即挨炮。但是他卻一口咬定鬧藥是自己買的,是自己誘使那個男人吃下的,他跟那個男人說,你連喝了這三杯酒,我就永遠離開你的女人!
吃飽喝足,獨眼龍推開飯碗,打起了飽嗝,嗝聲響亮。你說那個娃,姓雷?
雨啄了一下腦殼。
獨眼龍沉吟片刻,說,我覺得她們娘兒母女在耍你,你腦殼莫要發熱,開弓沒有回頭箭喲!
雨說,你到底幫不幫這個忙嘛?
獨眼龍嘆口氣,說,你要是整出什么大事,我也會跟著遭。
雨一聽這話,起身就要走。
這小龜兒子喲!獨眼龍從椅子上直起了身子,笑罵道,你咋比你那個老龜兒子還要脾氣臭呢?我又沒說不幫你的嘛!
獨眼龍說,我既然答應幫你,就會幫你把事情辦漂亮,辦到我們兩個都脫得了手,懂哇?
雨說,雷喜歡釣魚,上禮拜六和禮拜天大早就去了三灣堰塘,一個人。堰塘埂上有個土包,土包上有個草堆,正好埋伏。
獨眼龍想了想,問,你曉不曉得,如果距離近,容易被發現,如果距離遠,鐵砂子打出去又是一把傘,咋整?
多裝點藥,鐵砂里頭再灌鋼珠!
你說多裝點就可以多裝點?你曉不曉得鐵砂和鋼珠混多了要炸膛?獨眼龍嘆口氣,說,你個小龜兒子啊,光曉得殺人,卻是啥都不懂!既然是暗殺,就要人不知鬼不覺!鐵砂沒法遠距離射殺,也不可能一槍斃命……媽喲,算老子上輩子欠你兩爺子的。這樣,大后天就是禮拜六了,我把罐罐給你安好,藥給你裝好,就擱在我這個屋里,然后我就出門去個人多的地方,萬一以后調查起來,也有人證明我不在案發現場。你呢,直接進屋拿槍。切記,遠點打!打了就原路返回,把槍給我丟床底下,我回來就銷毀。你呢,片刻都不能逗留,趕緊回廣州躲起來。行不行?
5
回到酒店,雨把思路捋了捋,瞇了一覺,洗了把臉,又來到豉油雞店。店里空空蕩蕩,幾個伙計懶散地收拾著衛生。雨問肉在不在,伙計打了肉的電話。
肉進店門的時候,雨正湊在墻壁上看那些光顧過這里的名人明星的合影。梅在合影里,她保養得很好,白皙,微胖,一臉自信的笑容。
肉說,我老婆。雨說你福氣好啊。
沒幾句話,就扯到了王。雨說他曾經是個記者,當年采訪過王,王現在看起來似乎很落魄。
你怎么看出來的?肉問。
他的樣子就像掉光了葉子的樹,往事正在磨損他的骨頭。
你的眼睛很毒!肉感慨道,生活已經拿走了他所有值得驕傲和快樂的東西。
雨愿聞其詳。
肉說,王是孤兒,生活沒著落了,投到肉爺爺門下學廚。肉爺爺說你這么靈性懂事,學廚可惜了,拿錢供他繼續念書。王也算爭氣,考上了警校,當上了警察。但王卻從來不提這段經歷。王唯一的報恩,就是肉爸爸生意落敗后,他把他招進了公安局食堂。但他爸爸也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我爸爸是以貪污的罪名入的獄。可是貪污的錢呢?說是揮霍了,揮霍到哪里去了呢?我問多了他就冒火。臨終的時候,我說你要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里么?你是不是替王頂的缸?!他直搖頭,也直流淚。起初那幾年,我一直耿耿于懷,老是想搞清楚,把自己折磨得都快瘋掉了。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我搞明白了又怎么樣呢?再說我又怎么可能搞得明白呢?我爸爸不告訴我真相,不就是害怕真相把我毀了么?
真相是美杜莎,凡是看見的人都已經變成了石頭,這個世界所謂的真相,不過是盾牌上的倒影。雨說。
肉頻頻點頭,感嘆說講的好。肉講了他的家庭、事業和發展。他現在每年各項收入加起來不低于兩百萬,而且還在以百分之三十的比例逐年增加。他養了兩個女兒,老婆肚子里還揣了一個,是個男孩。他老婆很愛他,他也很愛他老婆,孩子們都非常健康。他在土鎮、愛城等地有十多處房產。每年,他都會以他爸爸的名義拿出三十萬資助貧困學生和救助無依無靠的老人……
等我兒子上大學的時候,我準備為他的大學捐建一座圖書館,以我爸爸的名字命名!
真好!雨感慨道,天道酬勤!
是善惡有報,天道輪回!你不知道他早已聲名狼藉、眾叛親離了嗎?肉問。
雨說我還真不清楚。
王無疑是愛河流域警察中最會破案的,但也是警察中最會搞破鞋的。他總是喜歡跟那些案犯的家屬搞在一起,什么殺人犯的妻子啊,什么搶劫犯的女兒啊,完全不顧影響。
王這么做,純粹是出于對他老婆的報復。也不知道他采用的是什么技術,他竟然懷疑自己的妻子在嫁給他之前就經手了十幾個男人,兒子出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起名字,而是用刑偵技術檢驗是不是他親生的。他的兒子不姓王,姓雷,隨他母親。
聽到這里,雨的心頭咯噔一聲,手一顫,送到嘴邊的茶水濺到了臉上。
王破案無數,人送美名“神探”,可他有個案子卻始終無法破獲。二○○○年五月一日,他的老婆駕車沖進了河里。按邏輯推理,他老婆應該是溺水身亡,但是根據尸檢,肺部卻沒有多少積液,而且致命傷是在頭部。是因為慣性撞擊了腦袋?法醫卻說不敢肯定,撞擊不會產生那么大的力,水會起到緩沖作用,而且車頭幾乎沒有受損……所以,有關他妻子的死,有太多傳言,有說是黑社會報復,有說就是王自己導演的殺妻案。
雷拿出了證據,說他聽到王給一個女人打電話,向那個女人保證說他會很快處理掉麻煩,然后就和她結婚。雷認為王要處理掉的那個麻煩就是他的媽媽。至于那個電話打給了誰,只消查一下通話記錄,就完全可以揭露出他們的奸情和陰謀。
雷到處舉報,舉報王在外頭搞破鞋,收受賄賂,虐待他和他母親,以及在他母親遇害前后各種反常。王自然要受到調查。調查結果他是清白的。雷不接受這個結果,跟王動了槍。王被打斷了腿,雷進了班房。
6
兩個小時后,雷才回來,開著輛貨車。下車就接過他女人遞過來的茶缸,咕咚咕咚地猛灌一氣。那茶缸像枚大炮筒,一半茶葉一半水。女人心痛,說你喝慢點,小心炸胃。
雷在女人的照顧下洗了把臉,換了身干凈衣裳,這才正面站到雨跟前。雷說,怎么,你是來補槍的么?說完自己忍不住咧嘴呵呵笑起來,笑過了,問雨是怎么找到自己的。雨說了肉。雷問雨吃過他們家的豉油雞沒有。雨說吃過了。雷說每個月他都會帶著老婆孩子去吃,肉總是拿茅臺酒款待他們。
雨打量著雷,雷皮膚黝黑,體格健壯,看起來是那么質樸豪爽。這么多年來,我的耳邊總是那聲槍響,眼前總是你栽倒在地的樣子。這么多年來,只要一閑下來,槍聲準會響起,我就像只無處可逃的兔子。每當我準備自首的時候,又心有不甘,因為那天早晨發生的一切并不像是真的,可是火藥味是那樣刺鼻,硝煙始終彌漫在眼前。
現在好了。雷說,你瞧,我好端端地活著。他擼起袖子,又干脆脫光了衣服,敞開脊梁和胸膛叫雨看,你瞧,這些都是刀疤,沒有槍傷。不過,你的確開了槍,的確有人倒下了,但那不是我。
雨驚詫道,那明明是你呀,橙色的羽絨服,牛仔褲……
在平常的教育中,人們總愛說這樣一句話,要想成為人上人,必得先吃苦中苦。只要你進入武校,幾乎所有的老師傅都會這樣教導,要想打人,先得學會挨打。雷從記事起,就挨王的打。他先是感到恐懼,慢慢地就覺得其實也就是那么回事,挨打嘛,不外乎皮肉骨頭疼嘛。
可揍人的是王,有令罪犯們聞之色變的好拳腳。雷還只是個小孩子,王在揍他的時候就沒有吝嗇過力氣和技巧。雷承受的不止是拳打腳踢,還有王那道不明講不清的憤怒和仇恨。他的小小身體就像容器,將王施予他的毫無遺漏地全部裝了進去。可是,這個容器只有那么大,而王總是不停地施予他拳頭、耳光和辱罵,眼見這個容器就要被撐爆了,雷不得不將那些東西拿出來,轉贈給身邊的人。
雷的成長過程就是不停地挨王的揍和不停地揍別人。雷在挨揍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揍人經驗,所以只要打架,毫無懸念,雷幾乎都是勝者。面對家長們的滿腔憤怒和學生們的頭破血流,校長唯一能給予的正義,就是堅決將雷開除。
雷其實早就不想念書了,但他媽媽一直堅持要他留在學校。媽媽說,你根本不知道校門外的社會有多險惡,到處都是炸藥包,而你,這樣一個渾身揣滿火柴的娃娃,一旦進入社會,不出半年,你就會將自己炸得尸骨無存。學校里的人,再怎么也要善良一些,純真一點,你和他們在一起,要安全得多。
進入土鎮中學,雷的表現和過去相比有太多的改變。他喜歡上了個女娃兒,梅。
雷在梅的家中受到了從沒有過的尊重和溫情。梅的父母專門將家中那間最寬綽亮堂的房間收拾出來給他住。這間房屋真不錯,打開后門就是漂亮的后院。在這個后院里,有梅爸栽種的果樹和各種花草,還有個小魚塘,雷釣回來的幾尾魚兒游得很歡。
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雷在鳥鳴花香中醒來,伸展開雙臂和腰身,一夜好夢,讓他精神抖擻。昨夜他夢見自己釣了好多魚,這是個好預兆,今天肯定大獲豐收,如果魚塘裝不下,那就好好吃一頓。
他雙腳剛落地,就愣住了。因為在他的床邊站著個陌生人,雙手抱懷,用一只獨眼瞄著自己。
哦,醒啦。他說。
他是怎么進來的?又是幾時進來的?他這是要來干什么?盡管雷不是個膽小的人,仍然覺得有些害怕。
都叫我獨眼龍,我從秦村來。你想不想知道我這只眼睛咋回事?那是個傍晚,我攆了一天山林,一無所獲。就在準備下山的時候,突然聽到前頭傳來一陣響動,經驗告訴我,這個野物個頭不小,它正踩著枯枝爛葉往這邊來。我大氣不敢出,小心把槍叫上火門,瞄準響動處。響動越來越大,是只麂子,它看見我了,也看見了黑洞洞的槍口,它的眼神充滿了絕望,放棄了逃跑,靜靜地站在那里,等著槍響。我勾動扳機,轟一聲,我眼前一黑,糟了,炸膛了。還好,老天爺憐憫我,給我留了只眼睛。
你現在應該曉得我是干啥的了吧?我會造槍,長的短的,單發的連發的。我更會耍槍,不管是野豬還是麂子,只要是被我看見了,它就成了肉。因為有肉,我的床上從來不缺女人。吃我的肉最多的是個知青。不光她吃,她還帶回家給她年邁的父母吃,還拿去送人情,求乞人家把她調回城里。在我的肉的滋養下,她不再黃皮寡瘦,她還變得越來越豐滿,越來越美麗。她是大著肚皮回城的,并不是因為肉吃多了長胖了,而是肚皮里揣了個東西,這個東西是我在這個世上唯一的種。
講到這里,獨眼龍突然問雷,娃兒,你就沒聽出點什么嗎?
我不懂你在說啥子。雷說。
獨眼龍瞟了一眼屋外,說,時間不早了,我沒工夫跟你繞圈子了。那個知青,她姓雷,她就是你的媽,而你,就是她從這里帶走的我的種。
你放狗屁!雷感到氣憤。
我不是想到你就要死了,又咋個會專門來跟你講這些話呢?獨眼龍說,有人要殺掉你!你是必須挨他一槍的,必須死在他眼前的!他是個死心眼。你即便躲得了他今天這一槍,也躲不過他明天或者后天的第二槍、第三槍……
為啥呀?雷叫喚道。
因為你奪去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這個東西有個名字呢,叫梅!
雷被雷劈了一般,呆在那里。眼見獨眼龍抓過他的牛仔褲穿上,又穿上羽絨服,扯上帽子套在頭上。魚竿在哪里呢?獨眼龍問。
臨出門的時候,獨眼龍走到雷跟前,摸摸他的臉,說,等一等,你會聽到一聲槍響的。這是我唯一能為你做的,當然,我也是為自己。我在,就不會讓你去挨槍,我在,就不會讓自己絕種!
過了一陣,雷果然聽到了一聲槍響。
隨后雷收到了一個包裹,是那個獨眼龍親自送到他手上的。獨眼龍面色蒼白,步履艱難。他嘶嘶地倒吸著涼氣,跟雷說,這事兒就這么擱平了,誰都不要講!
那個包裹里,是雷的牛仔褲和羽絨服,血跡斑斑。在羽絨服的前胸上,是一片密集的孔洞。
7
雷說,他成家后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獨眼龍從秦村接到了愛城,帶他去看病,買新衣服,讓孩子叫他爺爺。獨眼龍和他們在一起生活了兩年,就再不肯了,固執地離開他們,去了一家企業當看門人。
就在幾年前,他突然找了個老伴。他悄悄告訴我,說他這個老伴在很多年前伙同她的姘頭辦過一件歹毒事,用鬧藥將自己的丈夫弄死了。也不知道她給姘頭施了什么迷魂藥,姘頭竟然一個人扛下了所有的罪。姘頭被炮打腦殼,她卻只在班房里揀了幾年豬鬃。我說你既然曉得她是那樣的底細,為啥還要和她結婚?他說,他就要老死了,臨死之前,想要送我一件禮物。
我覺得,你可能從未看見過獨眼龍的裸體。雨說。
是沒有。雷說,為什么要看呢?
雨笑笑,揮揮手,走了。
雨又去了肉的飯店,專程去買豉油雞,發現梅在店里,就沒進去,遠遠地看了一陣。梅腆著肚皮,指揮伙計往墻上換新的合影。雨叫了個車,讓司機進店幫忙打包了兩只豉油雞,特別叮囑跟店家多要點豉油,然后去了機場,傍晚就回到了家中。
雨媽接她的孫女去了,雨妻還在公司忙碌。雨分別給她們打了電話,又叫姨娘和姨父晚上過來吃飯,他親自下廚。
有一陣子沒見到丈夫了,雨妻很高興,丟了手上的事,馬上往家趕,說要給他打幫手。雨特別叮囑妻子,記得在樓下超市買一罐蜂蜜和一罐番茄醬。
兩口子正忙碌著,姨娘和姨父先到了,接著雨媽和女兒回了家。學校布置了個手工,女兒希望和奶奶一起完成。雨媽當然樂意,但是女兒老是嫌她手腳太慢。雨媽佯裝不高興,女兒趕緊哄她,說她是天底下最聰明的奶奶,最能干的奶奶。雨媽被逗得呵呵笑。
雨妻要告訴雨兩件重要的事,雨以為是一直談判的協議有進展了,雨妻卻突然羞澀起來,說她又有了。這一個你計劃怎么處理?她看著他,問,要嗎?雨說,為什么不要呢?以后來多少咱們就要多少!雨妻很高興,湊過來深深地親了他一口,正好被進廚房的姨娘看見了,喲喲喲,姨娘咋呼道,我還說來幫忙呢,算了,辣眼睛。客廳的姨父吆喝道,少放點辣椒,我腸胃最近不好。大家都笑。
還有一件呢?雨問。
雨妻壓低了聲音說,媽媽戀愛了。雨一愣。雨妻說,對方是個教授,那叫一個文質彬彬呀。雨妻打開手機,找出照片叫雨看。雨看了一眼,高高瘦瘦,很儒雅的樣子。他邀請媽媽和他一起去歐洲玩,他的女兒女婿都在歐洲,機票都訂好了,大后天出發。
飯菜上了桌子,雨媽和女兒的手工還沒做好。雨說吃了飯再做,女兒不答應。雨站在一旁看著她們。雨發現媽媽頭發全白了。是什么時候全白了的呢?他竟然沒有印象。手工終于完成,女兒拿出來展示,大家都鼓掌,夸獎。女兒說要送個禮物特別感謝奶奶的幫助。她環著雨媽的脖子,啃一般地親吻她。雨媽笑得淚光閃爍。
姨父問雨這么些天跑哪里去了。雨說回了趟老家。雨媽、姨娘和姨父,都愣了一下,然后飛快地交流了一下眼神。
雨看著雨媽,說,你還記得梅么?
記得記得,那是個漂亮姑娘啊。雨媽說,就是她的那個媽不太討人愛,喜歡嚼舌頭。
她再也不會了。雨說,她過世了。
阿彌陀佛。雨媽念了好一陣佛。
雨妻從廚房出來,問雨,你咋把做好的那個醬丟垃圾桶里了呢?
做失敗了。雨說。
我嘗過,挺好吃的呀,香呢!雨妻說。
哦,有臟東西進去了,壞了。見雨妻還要問,雨上前解下她身上的圍裙,挪開椅子,扶她坐下。雨妻看著雨的臉,就好像他的臉上沾了什么東西。雨笑笑,挨著她坐下,看著她,滿眼深情,又抓過她的手,輕輕捏捏。雨妻心頭的那點疑惑瞬間就融化了。
雨提起筷子,夾起一塊雞腿,擱在雨媽的碗里,又挨個給雨妻、姨父、姨娘和女兒夾了菜。
梅和她老公開的店,專賣豉油雞,來,都嘗嘗!雨說。
都說好吃。
雨問姨父和姨娘,以前吃過嗎?
姨父和姨娘都說沒有。
雨看著雨媽,沒等雨問,雨媽就說了——
我以前吃過的,吃過幾回。但沒這好吃。
雨媽提起筷子,夾了一塊擱進雨的碗里,來,你也吃呀!
在機場送別的時候,雷打了電話來,說獨眼龍死了。
他給自己和那個女人買了很多意外傷亡保險,受益人寫的是我。雷遲疑了下,說,我看到了他的裸體,渾身上下光光潔潔,不見一點疤痕……你在聽嗎?
雨說,我聽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