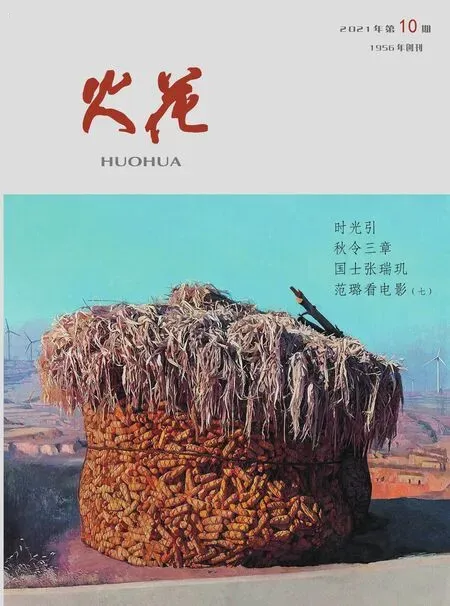趙家洼的消失與重生(四)
魯順民 陳克海
第四章換水土
一、救急與幫窮
工作隊駐村,人下來,政策也跟著下來。
他們本來就是來落實脫貧政策的。
工作隊駐村之初,就有人問陳福慶,這回下來帶多少項目,帶多少錢?問了陳福慶一個愣怔。但細想一想,扶貧,不就是帶項目帶錢下來嗎?
過去扶貧,修一段路,以交通內外,筑一段壩,以防雨季里“山水”(注:洪水)下來沖垮村舍,大一些的工程呢,今年新修村校以繼弦歌,明年再建筑舞臺以豐富文化生活,還有給村民安裝自來水、沼氣池。規模再大一些,竟或聯系企業資助,給村里建大棚,興養殖業,帶動村民增收。項目著眼基礎設施,工作多重產業提升。
過去扶貧,左不過如此。效果當然是有的,村民得益,村容改變,農村的產業結構也因扶貧在某種程度上發生著改變。可是,大多數項目下來,操的是好心,卻落不下個好。常常聽到農民講,下來項目撥下錢,“不知道最后好活了誰”。也確實,扶貧資金用不好,用不到位,常常引發新的鄉村矛盾;再則,任何項目落實到村,建工程,搞項目,搞承包,非能人莫為,與貧困戶關系不大;而且,獲得項目支持的常常是大村好村,甚至是富村,真正的窮村、小村卻難有項目落地。兩種現象,被學者稱為經濟活動中的“精英俘獲”。“精英俘獲”之下,矛盾在所難免。
農業在岢嵐縣的縣域經濟中占有很大比重,廣種薄收,薄收得益于廣種。岢嵐縣還是一個農業大縣,所以縣里對農業生產向來不敢掉以輕心,春播、抗旱、秋收,全縣的機關干部幾乎是傾巢出動下鄉督促。千名干部下鄉,岢嵐縣每年都做得聲勢浩大。
陳福慶在擔任陽坪鄉人大主席的時候,也包村,也包戶,每每下鄉慰問,機關從有限的辦公經費中擠出資金,前往村落慰問農戶,一壺油不少,兩袋面不多,逢年過節,還要加一兩箱牛奶,人人有份,戶戶不落,一旦出現偏差,好心就辦下壞事,新的矛盾馬上出現。
所以,從省到縣到鄉,大家都認識到,過去的扶貧方式,是一種“漫灌式”“撒胡椒面式”扶貧,而“精準扶貧”則是“滴灌式”扶貧,精準到村,精準到戶,精準到人,精準到項目,精準到幫扶效果。
陳福慶他們工作隊一行下來,搞的就是這個“滴灌”,搞的就是這個“精準”。
帶著政策下來,怎么精,如何準,需要給在村的、不在村的村民解釋半天。本來,解釋講解政策法規,是工作隊諸多任務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可是,精也好,準也好,任你說他個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見不到實效,都沒有什么說服力。
政策的輪廓一天一天顯現出來。就建檔立卡貧困戶而言,精準識別一直處于動態調整中,半年一調,一年一調。2014年,全村54戶115口人,常住人口僅6戶13人,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7戶45人,貧困發生率39%。經過兩次評議公示,到2017年有貧困戶17戶31人,其他則脫貧摘帽。
動態調整,有一整套程序與手續,不像過去“撒胡椒面”,有錢全村有份,有政策大家沾光,現在識別的是真貧困戶。在村的,不在村的,再沒有人用“有多少錢”“帶沒帶錢下來”問工作隊的人了。
因為程序擺在那里,這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
貧困戶建檔立卡,有九個步驟:先農戶申請,后入戶調查,再民主評議,然后由鄉村兩級審核,初步確定貧困對象之后,公示公告。公告結束,才確定幫扶結對對象,幫助貧困村戶制訂脫貧計劃,最后填好手冊,錄入數據,把貧困戶信息與幫扶措施、幫扶效果信息全部上傳到縣網、省網,數據隨時要更新。
這一套程序與工作細節之繁瑣之復雜,不到扶貧點上看,誰都不清楚。劉福有看到,陳福慶他們這三人工作隊,閑的時候跟你山南海北扯,忙起來點燈熬油半夜三更還不睡,連一句話都顧不上跟你拉。
村民住得散,留村的不用說,三個自然村,背操著手一天能跑三個來回,但還有住陽坪鄉政府所在地的,有投親靠友的,在縣城里也是東巷一家,西街兩戶,跑起來很麻煩。工作隊進出村落,單位倒是有交通補助,可是縣鄉公共汽車一天才兩趟,根本跟不上工作隊的工作節奏。公共汽車來了,他們手頭有事走不開,鄉里、縣里有緊急會,等車又偏偏等不來,罷罷罷,只能自己解決了。
剛開始大家都騎電動車,但岢嵐縣一過中秋節,百草回頭,霜雪相連,寒風梳骨,電動車走十幾里進入村莊,腿腳關節落病倒是其次,干線公路上每天有運煤大車源源不斷從興縣那一頭趕過來,加上冬天路面容易結冰,騎電動車真是特別危險。
冬天摩托車不能騎,陳福慶買了一輛汽車。汽車載著工作隊進村,大家都溫和地笑起來:啊呀陳書記,開上汽車啦?
這是一款什么汽車?是一輛“奇瑞QQ”,費洋16800元整的二手車。遮風擋雨不費油,還毫無懸念有暖風供應,比之電動車,已然豪華無比。買來一年多,方便工作不說,村里誰家有一個病病痛痛,王大娘要買一袋米,劉大叔要捎一壺醋,曹大叔要買化肥,楊大叔要給羊群吃防疫用藥,這輛“豪華無比”的汽車就派上大用場了。
建檔立卡,建檔同樣是動態的,每落實一項政策,都要及時填上去。每一戶一個檔案,每一份檔案里低保金額、糧食直補、“五位一體”貸款扶助、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地膜補貼、退耕還林等等,般般樣樣,都要及時填上去。檔案里記載不說,每一戶家里還有“明白卡”,內容與檔案相同,誰誰家享受了什么政策,收入幾何,一目了然。
工作不能有半點含糊。鄉里要考核,縣上要檢查,省里還要來檢查,還有國家級驗收,一點點差池都來不得。
山西省脫貧攻堅頂層設計,精準扶貧措施包括兩大塊。像曹六仁、張秀清這樣有勞動能力的窮困戶,采用開發式幫扶,所謂“有志想做,有事可做,有技會做,有錢能做,有人幫做”;另外像劉福有、王三女、李虎仁這樣無勞動能力的老人,實施政策保障兜底,所謂“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病有所醫,居有所安,難有所幫”。
兩大塊,具體實施起來又分為八大工程二十個專項行動。八大工程為:培訓就業扶貧、健康扶貧、社會保障扶貧、金融扶貧、教育扶貧、旅游扶貧、交通扶貧;二十個專項,則覆蓋了扶貧、財政、民政、水利、農業、林業、社保、科技、教育、交通、金融、商務、工商、電力、電信、住建、衛生、國土等27個政府和企業職能部門。山西脫貧攻堅,打的是一套“組合拳”,造得聲勢大,投入力量大,鋪得攤子大,分門別類,因地制宜,覆蓋到全省58個貧困縣。
這些,趙家洼的老鄉們未必知道。
他們也不看你聲勢如何大,攤子如何廣,看的是實實際際的效果如何。
貧困戶的明白卡(注:記載貧困戶享受扶貧政策項目的卡片)就擺在家里顯眼的地方。
比如劉福有,上有高堂老母,全家3口人。因缺勞力致貧。享受各種扶貧政策如次:
光伏扶貧3000元。
退耕還林補助13畝,6500元。
滲水地膜谷子補貼3畝,150元。
農資補貼44畝,3156元。
合作醫療報銷4471.86元。
新農合參合費用補貼3人,540元。
大病保險報銷1人,2663元。
低保3人,8208元。
臨時救助1人,1000元。
養老保險金3人,3420元。
高齡老人生活補貼1人,720元。
愛心煤1戶,200元。
兩節慰問、電費、合作,1615.97元。
共計35244.78元。
王三女,全家3口人,因病因殘致貧,享受各項扶貧政策如次:
光伏扶貧3000元。
退耕還林補助25畝,12500元。
滲水地膜谷子補貼2畝,100元。
農資補貼25畝,1755元。
新農合參合費用補貼3人,540元。
大病救助1人,1500元。
低保1人,3396元。
殘疾2人,17000元。
臨時救助1人,2000元。
養老保險金1人,1140元。
愛心煤1戶,200元。
兩節慰問、電補、合作,2425.92元。
共計45556.92元。
賈高枝,全家2口人,因病、因缺勞力致貧,享受扶貧政策如次:
退耕還林補助13.9畝,6940元。
農資補貼27畝,1953元。
新農合參合費用補貼2人,360元。
低保2人,5472元。
養老保險金2人,2280元。
愛心煤1戶,200元。
兩節慰問、電費,685.92元。
共計17890.92元。
李虎仁,家里1口人:
光伏扶貧3000元。
退耕還林補助10畝,5000元。
滲水地膜谷子補貼2畝,100元。
農資補貼33畝,2437元。
新農合報銷1人,6517.52元。
新農合參合費用補貼1人,180元。
五保1人,3940元。
臨時救助1人,1000元。
養老保險金1人,1140元。
愛心煤1戶,200元。
兩節慰問、電費、合作、幫扶,895.92元。
共計24410.64元。
曹六仁,全家4口人,因學致貧。享受政策保障與生態扶貧扶助如次:
金融扶貧4000元。
光伏扶貧3000元。
生態扶貧2000元。
退耕還林補助23畝,11500元。
滲水地膜谷子補貼3畝,150元。
農資補貼32畝,2378元。
雨露計劃1人,2000元。
新農合門診報銷1人,4479.25元。
新農合醫療補貼4人,720元。
低保1人,2736元。
臨時救助1人,3620元。
愛心煤1戶,200元。
慰問金1人,300元。
電補、其他,925.92元。
共計38009.17元。
張秀清,全家4口人,因學致貧,享受扶貧政策如次:
退耕還林補助22畝,11000元。
農資補貼34畝,2456元。
新農合參合費用補貼4人,720元。
愛心煤1戶,200元。
白有厚幫扶,6000元。
共計20376元。
等等。
幾位貧困戶所享受的扶貧政策,大致上涵蓋了開發式扶貧與政策性兜底兩種扶貧措施。
這里需要解釋的,有一項光伏扶貧項目,這是山西省整合扶貧資金做的光伏發電扶貧項目,利用光伏發電收入盈余給建檔立卡貧困戶分紅。光伏發電項目惠及全省58個貧困縣,總裝機容量達到190萬千瓦,相當于一個大型火電站裝機容量。光伏發電,各縣采用的方式不同,許多縣份把光伏發電板直接裝在貧困戶的窯頂之上,被老百姓稱為“屋頂上的銀行”。
趙家洼貧困戶,貧困類型相對單一,所以,基本上以政策性兜底為主。僅是政策性兜底扶助,村民全年可支配收入遠遠超過人均3200元的現行貧困線標準。有政策扶助,脫貧在即。
政策一項一項落實下來,一項一項落實于每一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名下。村民漸漸明白了,這一次“精準脫貧”可跟過去不一樣。
老楊楊玉才說:這個精,就是少。貧困戶畢竟是少數,全村弄成貧困戶,說出去也不好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老支書馬忠賢做過三十多年村干部,因為兒子馬貴明是鄉鎮干部,領著財政工資,屬于建檔立卡“八不進”之列,退出建檔立卡戶,但老人說:可不是不一樣?老話說死了,救急不救窮。這一回扶貧,是既要救急,還要救窮!
二、6·21 的趙家洼
2017年6月21日,趙家洼村史上一個特殊的日子。應該講,是整部趙家洼村史的一個高潮部分。
這一天,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山西。下午四點多,習近平總書記一行踏進這個不足百年歷史的小村莊。在這里,他待了將近80分鐘。
村里人,包括工作隊的陳福慶,開始并沒有感到這一天會與其它庸常日子有什么不同。平時忙忙碌碌,操心的事多,這一天,要操心的事一點也沒少。
一大早,陳福慶見劉福有到井邊去擔水,跑上去要給他擔,但劉福有怎么也不讓,兩個人相持了一會兒,陳福慶只能放棄。
兩人說起今年這天氣。地里的莊稼“捉了苗”(注:出苗),出苗情況還不錯,該間苗了,正是要一場雨的時候,偏偏老天爺扎住口袋一滴雨都不肯下。早晨,天氣比平時要冷一些,老劉擔一桶水,瞇眼看天,說:“這天氣,看不看,沒雨。”
緊接著曹六仁曹大叔也出門了,要到玉米地里間苗,抬頭看看天,還是個不下雨。舊歷五月,莊稼最需要雨,可就是下不來。曹大叔嘆了口氣就下地去了。
雖說有各種各樣的扶貧政策落實到戶、落實到人,但村里人日常生計還需要靠種地。早春,陳福慶落實春耕備耕情況,全村還有12戶還按老規矩按部就班耕田下種,開始一年勞作。在村6戶耕作面積不等,劉福有15.45畝,張秀清7.57畝,王三女7.94畝,曹六仁12.67畝,楊玉才18.94畝,李虎仁和回村種地的兄弟李云虎3.77畝。不在村的,馬貴明5.65畝,田貴林8畝,張二全(縻)15畝,趙亮香3.5畝,馬忠賢老人也回村種地,但地是女兒的。另外一家在村包別人地種,戶籍不在趙家洼。就這12戶,全村共計種植面積98.49畝。
天旱,旱的不獨是貧困戶,旱的是全村人。
如果再過一個月不下雨,今年的莊稼就要歉收了。劉福有說,如果再不下雨,就只能是個祈雨了。祈雨這個事情,陳福慶沒見過,但聽說過。趙家洼素來是“養窮漢”的地方,這一帶過去山林密布,除了天氣寒涼之外,降雨倒不見得少,保德、興縣臨近陜北的地方有祈雨風俗,趙家洼的人都知道,但也就是隨口一說。
可是今年確實是旱。
陳福慶究竟是農家子弟,幾乎是出于本能,每年春天,他會不由自主關心地里的墑情,下一場雨,臥一場雪,眉頭也不由舒展,心情格外好。天旱、霜凍、冰雹,即便坐在辦公室里,他會不由自主望一眼家鄉所在,如坐針氈。土地給人太多的東西,雖然不在土里刨食,但土地上的悲喜是植在血脈里的,由不得人。
久不下雨,陳福慶著急。但眼前兩件事,他得馬上辦好。
一件,扶貧蛋雞的問題。
早在4月份,縣人大給留村的貧困戶每戶發放15只蛋雞,都是縣人大統一從雞場購進的產蛋雞,發放當天就可以下蛋,15只雞每天可以產蛋7到8顆。發扶貧蛋雞的目的,是考慮到村里留守的都是老人,一來,可以自己留一部分,增加營養;二來呢,攢到一定程度,再到集鎮上去賣,怎么也夠平常下油鹽醬醋“嚼裹”(注:支出)。
本來呢,雞的品種還好,都是一水的紅翎母雞,實際上也是本地土雞品種,但發放到貧困戶家里,問題就來了。一是丟蛋,這雞不好好往雞舍落蛋,草地里一顆,土窩里一顆,哪里舒服它往哪里走;二是丟雞,王大娘前天丟了一只,昨天又丟了一只,鄉防疫站人來打雞瘟疫苗,當下又給打死一只,15只雞,只剩下12只,把個王大娘心疼得。劉大叔家的呢,中午吃飯的時候,那只最大的雞還一步一搖過來向劉大叔討食吃,吃罷飯,轉眼就不見了。三呢,就是雞病,剛捉回家,下蛋下得好好的,過了一個月,說不下就不下了,十幾只雞,一天下一兩顆,還“不住氣”(注:不間歇)個喂食,長此以往,如何得了?
總之,蛋雞們來到趙家洼,不安生就是了。
因為這個雞的事情,陳福慶回城里辦事,專門請教過曾一起工作過的畜牧員,人家說雞到了一個生疏環境需要適應一段時間才可以正常下蛋,現在還處于適應期,不要著急。
接下來,是王大娘的情況,實在讓陳福慶放不下心。
王大娘丟雞還是其次,她的情況太特殊了。
新任縣人大領導剛一上任,就帶著縣人大同志來定點幫扶的趙家洼村,自己一口氣定點幫扶王大娘、趙成仁、趙拴仁、曹六仁四位貧困戶,成仁、拴仁兩個是老年單身,缺乏勞動力致貧,曹六仁三個孩子上學因學致貧。
王大娘就特殊多了,老而無依,又患有風濕性心臟病、高血壓,藥不離身。2016年由合作醫療報銷2083元,臨時救助200元,鄉政府救助1000元,常用藥硝苯地平緩釋片。治療問題暫時緩解,但還要“務育”(注:養育、扶養)兩個殘障孫輩,種植9畝多土地。
2017年開始,工作隊的一個共識,要徹底幫助王大娘解決問題。
此前,陳福慶已經“承包”了老太太的擔水問題,余下尚有幾項需要解決。
首先是種地。一個68歲的老太太,還種著9畝多地,田力勞作已經勉為其難,耕種鋤耬收獲,過去都得靠她自己。還有種子、化肥、雇人這一系列支出,收種9畝多地,真夠老太太忙亂的。
牛工,縣人大領導大包大攬,說自己出。劉福有喂有兩條耕牛,縣人大領導跟老劉商量,由自己掏腰包,一年1500元租下老劉的牛,為王三女把耕地的問題解決,然后是種植、管理、收獲,那就是幾個工作隊員的事情了。
再就是兩個殘障孫輩。
在討論的時候,發生過一件事,這件事發生之后,大家更覺得應該把兩個孫輩安置好。
王大娘把李虎仁狠狠罵了一通。
6月初,縣人大領導通過民政部門,為兩個孩子聯系好忻州市特殊教育學校。陳福慶去做王大娘的工作,王大娘就是動用一輩子積攢起來的經驗,也絕對想不到,國家還專門有為兩個娃娃辦的這種學校,先是吃驚,再是不舍。兩個孩子其實就是自己養大的,推干就濕,佝勞苦辛,一直養到十歲出頭,沒離開過自己一步。兩個孩子離開自己怎么生活?她想象不來。兩個孩子離開趙家洼,遠天遠地跑到忻州,多長時間才能見一面?想來想去,她猶豫再三。
送兩個孩子的事,在村的幾戶人家都知道了,大家都勸王大娘讓孩子受點教育,掌握一定謀生本領,這是為孩子的將來著想啊。
誰知道,李虎仁說了一句話:“怎么解決?再簡單不過了———要是我有這么兩個娃,就把他們帶到火車站,推上火車,拉他們到哪里就去哪里哇!”
李虎仁的話讓大家都吃了一驚,但大家都知道他其實就是那么個不會說話的人,也不跟他計較,但這話無疑戳到王大娘的心窩子上了,她頓時勃然大怒,氣得扯新蘆帶瓢,風攪雪,雷夾雨,把個李虎仁咒得無地自容,落荒而逃回到大趙家洼的土窯里,唉聲嘆氣怪自己說錯了話。
也是這次沖突,王大娘決定送孩子到忻州去。也是啊!將來自己老了,走不動了,帶兩個娃娃,該怎么生活?
2017年的6月5日,王三女的兩個孩子,曹永麗、曹永興,被送到忻州市特殊教育學校。要說,這事慎重,漫說是王三女一輩子沒出過遠門,即便她行動便利,一個農婦只身帶兩個孩子坐車走一百多公里到陌生的他鄉城市,工作隊實在不放心,定點幫扶的縣人大領導更是不放心。
人大出車,人大出人,走的那一天,是縣人大領導陪同王三女把兩個孩子送到學校去,來回走了一天。
陳福慶太知道王大娘心里的糾結了。正好他在城里有事,幾天沒回工作站,6月8日一回村,第一個看的就是王大娘。王大娘的精神狀態還好,孩子雖然送到學校,吃住“公家”都管起來,還有人照顧,放心是放心,但老太太的表情還顯疲憊,還有些戚然。
王大娘說:咱親眼見,誰誰校長誰誰主任對這件事情很重視,人家關心,咱也放心。可是……可是啊,身邊一下子空了,院子里聽不見孩子們的叫喚聲音,真還有些難活(注:不好受)。
是啊,王三女真是一個苦命人,兩個頂梁柱十年之間走了一對,窮家連個殘障兒媳婦都留不住,現在,兩個孩子又送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另一個地方,身邊的親人,接二連三以不同的方式離開自己,一個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守著破敗孤院,心里怎么好受得了?
從那一天起,每天早晨,陳福慶一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王大娘家的煙囪冒沒冒煙。冒煙,說明王大娘起來了,如果沒有呢,他就著急,要在大門上喊兩聲,等王大娘答應一聲,他才放下心來。
第一書記陳福慶操的不是一道道心,日理十幾機,機機都上心。6月21日這天也一樣,他關心完旱情,看完王大娘,問候了劉大叔,才回工作隊駐地收拾屋子,做飯填肚子。他而后組織工作隊的成員給王大娘玉米地里間苗,再給曹大叔家里清掃了一下院子。
然后,總書記一行踏著鄉間道來到趙家洼。
總書記來趙家洼,入田間,問苦寒,先后探訪了王三女、劉福有、曹六仁三戶貧困戶。
在王三女家,總書記親切地稱呼王三女為“大姐”。
總書記一句話,曖的不僅是王大娘一個人的心。
陳福慶在《民情日志》中如此記述這一天。
下午兩點多,接到通知,要求待在站內,有人說總書記來了。我一驚,怎么沒人說啊。
到了四點,聽見有人喊:快點,總書記到咱們工作站來啦!
我趕緊跑出去,只見總書記正從石階上往上走。總書記一一和我們握手,說,辛苦了!我趕緊應答,不辛苦。大家忙把總書記讓回屋子里。總書記詳細看了屋子里的擺設,最后與我們親切交談,詢問我們工作中有什么困難。縣人大領導趕緊答應:現在黨的政策好,只要我們落實好政策,就一定能幫鄉親們擺脫貧困。
然后又聽總書記講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深感責任重大。
總書記來趙家洼考察的新聞報道輪番播放,遠在他鄉的趙家洼鄉親都給陳福慶打電話,問為什么不早早告訴他們。而在岢嵐縣,總書記視察趙家洼和宋家溝,新聞一遍一遍播放,闔縣的人對每一個細節都熟稔于胸。
陳福慶的《民情日志》如是記述在外趙家洼村黨員的反應:
楊旺才:57歲,1989年11月入黨。現居鄂爾多斯東勝區二女兒家,陽光新城B區。他從央視、微信已經知道總書記來村情況。
馬飛:34歲,2014年12月入黨。現住東勝區,在遇見旅游有限公司打工。他從父親那里已知悉總書記來村情況。當天央視新聞、山西新聞看了好幾遍。
劉永兵:46歲,1997年11月入黨。現居巴盟(臨河區),打工。從央視新聞已看到,那幾天本來打算回村,沒有回來,感覺有點可惜。
趙慧:女,30歲,2010年6月入黨。現居太原許西村,租房居住。介紹習總書記來村慰問情況和本人在外生活情況。她已從微信群得知,感覺挺光榮的。
還有,遠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馬飛,也就是馬貴明的大兒子,算是趙家洼最年輕一茬人里最成功的一位,大學畢業,懷揣夢想遠走他鄉創業打拼。這一日上班回來,突然看到《新聞聯播》中播放總書記考察山西的消息,他頓時呆住了。那個貧窮的小山村,那個無數次出現在夢里的故鄉如此隆重如此浩大出現在面前。
劉爺爺、曹伯伯、王奶奶,一張張熟悉的面孔,跟總書記在那里拉家常,黃土地綿延,禾苗在生長,還有那些收藏自己童年記憶的泥街陋巷。鏡頭閃過,這位來自山西岢嵐縣趙家洼村的小伙子,在鄂爾多斯城市的燈火里,仿佛瞬間回到故鄉,他含著眼淚不錯(注:一直)盯著電視屏幕,生怕漏掉哪怕一幀圖像。
在此之前,馬飛,還有他兩個弟弟,還有在趙家洼出生、在趙家洼一起長大的那一群年輕人,共二十幾位,他們建有一個微信群。但是,平常大家各忙各的,群里消息寥落,冷冷清清。6月21日之后,微信群就像爐膛里扔進一捧柴火,添進煤,加進炭,嘭地點燃了,呼朋引伴,每天都有說不完的話題,仿佛回到少年做夢的年代。
大家都感到溫暖與榮光。
6月21日這一天的經歷,將在趙家洼人的嘴里念叨好長一段時間。陳福慶也一樣,電視里播出過他陪總書記前往貧困戶家里的鏡頭,走在街上,會被許多人認出來。一段時間,他都感到很不好意思。
他的壓力其實不小。
三、老李的瓜與王奶奶的病
跟王大娘發生“沖突”的李虎仁,住在大趙家洼,一個人,74歲。兄弟三人,虎仁、根虎、云虎。老二根虎離開趙家洼遷到北道坡,老大虎仁、老三云虎還在趙家洼。留在村里的兩兄弟至今未婚。老三云虎“活泛”一些,外出打工,在三村五舍的同齡人中頗有號召力,擔任著趙家洼村主任。大哥虎仁的日常生活用度,全由這個三弟弟來照應著。
李虎仁所居的大趙家洼,陸陸續續出遷,只剩下他一個老漢獨自守著村子。李虎仁住的仍然是爺爺手上留下來的土窯洞。
黃土高原上的土窯洞堪稱建筑史上的奇跡。黃土直立性好,掘土而居,門窗合一,采光好,保暖性強,若一一列舉,蔚成大觀。其實窯洞建筑與其它形制的建筑一樣,有甚為講究的,好一些的村落,或土窯,或石箍窯,或靠崖窯,沿山勢排列開來,呂梁山區好多村落都成為十分了得的古民居聚落。也有很勉強的,靠崖畔掏進去,一孔或者兩孔,或者三孔,外面稍事收拾,泥抹墻面,深居溝底,這種窯洞簡陋至極,是窯洞建筑里最不講究的“一炷香”。“一炷香”泥墻泥地,“孤眉單眼”,如一縷輕煙,一派蕭索。春天一場風刮過,在龐大的黃土覆蓋層那里,簡直無法分辨出來,夏天一場雨下過,泥濘遍地,無法下腳,連狗走路都打滑。雨殺霜打,幾十年下來,這種窯洞居所極不安全。
趙家洼第一代移民過來,大都住的就是這種窯洞,隨便開挖,先安下身來再說,溝溝岔岔里,轉一個彎一戶,再轉一個彎,又是一戶。直到“生產隊年代”,大家才三家五家從溝溝岔岔里搬出來,起瓦房,建新舍,成為村巷相連的聚居村落。
但李虎仁一直住的是他爺爺手上留下來的“一炷香”。這“一炷香”,燒了沒有九十年也差不多。李虎仁就出生在這孔窯洞里。村里人一天比一天少,李虎仁本來性格就“綿”(注:隨和,懦弱),內向,這就跟人交流更少了,若不然也不會對著王三女說出那樣唐突冒失的話來。
俗話說,“男兒無妻財無主”,李虎仁一個人一輩子下來,孑然一身,縱是七尺男兒軀,就像沒有主人的財富一樣,既無法生利,也無法自生,渾身的毛病不只一端,他的整個人生處于嚴重的挫敗狀態。把他評成建檔立卡貧困戶之初,村里人就有意見,原因是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懶”人。懶人都可以列為貧困對象加以幫扶,那不是鼓勵懶惰嗎?
議論紛紛。
但大家誰不知道李虎仁的情況,74歲一條老光棍五保戶,你不扶他扶誰?你若不去扶他,他可怎么辦?議論一陣,也就不再說什么,剩下的事情則全部交給工作隊了,相當于把一個人托付給了陳福慶他們。
李虎仁一個人住在大趙家洼,幾乎每天都要來位于小趙家洼的工作站坐一坐,陳福慶,或者村主任弟弟李云虎,則每隔一兩天過去給李虎仁把水缸擔滿,再給他收拾一下院子。
李虎仁被陳福慶喚作“老李”。老李一輩子無兒無女,跟人交流也少,孤單寂寞,忽然有人叫他“老李”,之前從沒有人這樣稱呼過他,頓時感覺自己好有尊嚴。當然,剛開始多少有些不適應,以后也就慢慢習慣了。
而且叫他“老李”的這些縣人大干部,平常照顧他生活,逢年過節還送米送面送油過來。李虎仁心里的感激自不必說,處的時間長了,一天不見陳福慶就覺得生活缺下了內容,不知道該怎么辦。兩年多時間下來,這個平常在大家眼里有些懶的五保戶話也漸漸多起來,跟人交言接語,也關心村里的事,變化不小。
2017年春天,陳福慶逐戶落實村民的耕種面積,李虎仁退耕還林之后,還種著6畝多地。陳福慶問他準備種些什么,李虎仁訕訕地笑起來,直是個搓手。原來,老李李虎仁是要種幾畝西瓜。種幾畝西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老李才說:我是專門給咱工作隊種的,你們給我送米送面送油,還送牛奶,我還不能種點西瓜來酬謝一下?
老李要種西瓜,陳福慶吃驚不小。因為他太知道老李了,每年種地,東刨一爪西耬一耙,種瓜那是個技術活,老李怎么能種得出?但老李做這樣的決定顯然不是心血來潮,不知道思謀幾個黑夜才下的決定。
這個懶人總算是“動”起來了,陳福慶打心眼里高興,正像曹六仁寫的順口溜那樣,“扶貧先扶志,有志無難事”。老李這是有了生活的心勁兒了,不說酬謝工作隊吧,能種瓜,還能換幾個現錢,這是好事情。
陳福慶說:好哇,老李,好好種,等你開園下瓜。
懶人老李要種瓜,讓扶貧隊員寬慰不少,而王奶奶的病,讓他們的心又緊了起來。
此王奶奶,就是劉福有大叔的老娘王花仁,趙家洼村年齡最大的老人。在劉福有那里,老娘就是自家的頂梁柱,現在已經失能臥床,縣人大通過殘聯給配了輪椅,天氣好的時候,由兒媳婦楊娥子推出村口曬曬太陽。
70歲的兒媳婦推著91歲的婆婆間天出來曬太陽,貧瘠寒素的山溝溝里,樹木、草坡、禾苗,還有房頂上的炊煙都會現出十分柔情的。
王奶奶突然發起高燒。她本來就有肺氣腫,這一發高燒,還不一定要引出其它病來。陳福慶趕忙給鄉衛生院李鳴飛院長打電話,李院長開車從鄉里10多分鐘就趕了過來。病來得兇險,一時無法確診,李院長建議快把王奶奶送縣醫院做進一步檢查。當下,陳福慶和人大的周繼平兩個人陪著,李院長再開車把王奶奶送到縣醫院,住進病房,忙前忙后,直到下午三點上班,王奶奶被送到CT室,到了晚上結果才出來,老太太是肺部感染,需要住院治療。
王奶奶病倒,王三女王大娘接著出了狀況。她說一直“沒精神”,病病殃殃的,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賴病”?
也是,家里十年之間前后走了兩個頂梁柱,老太太對自己很沒信心,成天念念叨叨。
陳福慶著急,包戶幫扶的縣人大領導更著急,把老太太送到忻州檢查一次,開了一些藥,也沒有診斷出個子丑寅卯來。過了些時間,縣人大領導讓陳福慶干脆帶老太太的病歷到太原的山西省腫瘤醫院讓看一下,搞清楚老太太的病。
太原診病,當天來回,病檢結果得等幾天。工作隊在村里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很要緊,每一件事都得認真對待。過了幾天,陳福慶需要到太原去取化驗報告,又是一天的忙。
陳福慶的《民情日志》記述當天情形。
8日早8點,小張磊(單位司機)下來,我簡單整理一下,便坐車上了高速。路過奇村服務區,渴得不行,買了一瓶水。快到太原怕走錯路,小張磊打開了手機導航。
10:20左右到達省腫瘤醫院。拿著王大娘的身份證和交款收據,直接去三樓病檢科取了化驗單,化驗單上并沒有不好的詞語,我心里也輕松了一下。到一樓去掛號再讓醫生看一下,門診醫生說現在不能掛號了,下午3點再來吧。
和小張磊到外邊吃了午飯,在車里休息了一會兒。快3點,到一樓大廳排隊掛了號,來到二樓等叫號。坐了一會兒,醫生叫號,我拿出化驗單讓醫生看。醫生說,沒有大問題。我又問,需要怎么治療呢?醫生說,吃點藥吧。我說在忻州開了近600元的藥,都是消炎藥。醫生說,那按照醫生的安排,把藥按時吃了。又給開了一種叫巴洛沙星膠囊的藥,按說明吃上。
從醫院出來,我將情況向縣人大領導做了匯報,并把化驗單照了相,發給縣人大領導。
6:50左右回到趙家洼村。正巧碰上小王記者在村子里采訪。小王記者詢問了王大娘的化驗情況,并仔細看了化驗單。
本想第一時間把這個情況告訴王大娘,小王記者說,等明早吧,給大娘一個驚喜。這下她就可以徹底放心了。
王大娘的病暫時可以讓人放心了,心焦的事又來了。
天旱了一個五月,又旱了一個六月,再持續到七月。7月17日中午,陳福慶到縣委組織部辦事回來,好幾天沒見老李,怕他有什么差池,和村主任李云虎到大趙家洼看望老李。結果這個老李呢,是怕上山栽樹的人來來往往踩了他的地,這幾天就守在家里看門。更主要的,他還是惦記自己的二畝西瓜。他特意領陳福慶和自家兄弟看他的西瓜地,一個勁說,看看看看,再過兩個月就可以開園啦!長得怎么樣?
旱情持續,西瓜長得很不喜人,但老李卻信心滿懷。
看完老李,陳福慶、李云虎兩人往回走,走到半道,一陣爽風吹過,接著就來了一陣雨,雨打在臉上,心里好爽快。可是這雨來得急,去得也急。這場意想不到的雨,把全村人都召喚出來。兩人進村,已經見王大娘、曹大叔、劉大叔都出來了,地邊聚下一群人。
陳福慶抹一把臉上的雨水,問大家:怎么下了一下下就停了?
是著急,問話也沒頭沒腦,仿佛這雨操縱在眾人手里似的。
王大娘說:只下了一個地皮濕,根本救不了命。她指著自己的幾畦菜地說:看看,菜也快曬干了。
這種雨不起作用,老百姓叫它作“掃院雨”,剛剛達到打掃院落不蕩塵的地步。
可不是,王大娘地里的黃瓜長到二尺多高,花菜、白菜剛剛間苗,都是無精打采。陳福慶也二話沒說,叫上正在村里的人和駐村的周繼平,從劉大叔家拉來平車,又到宋木溝村借來儲水塑料大罐,到井邊取水。一桶一桶接滿,再一車一車拉到地邊,幾趟下來,總共拉了幾大罐水,黃瓜、花菜、白菜挨個兒澆一遍。
開始是雨水淋,再是汗水淌,陳福慶和周建平兩個人的身上都濕了。王大娘說:唉,不當人子,我們老給你們添麻煩,你說說,我們這些人也沒做過啥貢獻,國家又是搞扶貧,又是給政策,還派你們下來,咋能叫人過意得去?
陳福慶不善言辭,不講大道理,但王大娘的話讓他感到很沉重。
王大娘、劉大叔、曹大叔,包括老李,其實心里都懷一顆感恩的心,他們純樸、善良,從來不把感謝的話放在嘴邊,他們會今天給工作隊端一碗涼饸烙,明天送一籠莜面過來,老李還專門給工作隊種上二畝西瓜,東西不值錢,但那都盛著滿滿的情、滿滿的意。
他們怎么沒做過啥貢獻?想當年,趙家洼人從保德縣、寧武縣、河曲縣,從四面八方趕過來,雖說是為了吃一口飽飯,但他們不知道,抗戰時期移民墾荒,實則是當年中共邊區政府“大生產”運動的一部分,為邊區建設乃至全國抗戰做出過大貢獻;“生產隊”年代,大小趙家洼、駱駝場從“立社”開始就交公糧,一直交到1982年;改革開放之后的“三提五統”各種費稅則交到2003年。趙家洼和全中國的農村一樣,為國家建設貢獻過食糧,貢獻過勞力,還貢獻過土地,怎么能說不創造價值?趙家洼的農民和全中國的農民一樣,是國家的柱石。
從這個意義上講,惠及岢嵐全縣鄉村乃至全國貧困地區的扶貧工作,還帶著一重政治倫理意義。
而今,一項聲勢浩大的扶貧工程即將落地,趙家洼村在2017年9月之后將從民政部門的地理名錄中“銷戶”,最后徹底消失。
老李的瓜究竟沒有長成,也是因為天旱,更是手藝不行,到西瓜開園的季節,他種的瓜比一個人的拳頭大不了多少。
陳福慶故意逗他:老李,你種的瓜呢?
老李的臉騰一下就紅起來。
四、“得搬!”
總書記一行考察山西,脫貧攻堅是重點,而到趙家洼視察,易地移民搬遷又是重點。
6月21日,在趙家洼扶貧工作站,縣人大領導在回答總書記問話時,非常肯定地回答:得搬!不搬不行!
陳福慶在匯報材料里這樣總結趙家洼村,叫做“六多,三難,三不通”:坡多、災害多、外流人員多、老人多、病殘多、單身漢多,上學難、就醫難、娶媳婦難,網絡不通、動力電不通、電話不通。
一村如此,全縣共有115個村莊莫不如此。
一方水土養不好一方人。
一方水土實在是難養好一方人。
“得搬!不搬不行”,這話發自肺腑。
脫貧攻堅,八大工程二十個專項,其實圍繞一個目標,叫作“兩不愁,三保障”。兩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保障義務教育,保障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兩不愁”不發愁,“三保障”有問題。
“兩不愁,三保障”僅僅是國家脫貧攻堅總目標的一個描述性表達,轉化為量化指標,分得就細了。
具體到山西省,具體到岢嵐縣,這個標準分為三個層次的考核,即“戶脫貧、村退出、縣摘帽”,每一層次的考量相互聯系,相互發揚。
戶脫貧,具體指標為“一超五有”。
一超,有基本穩定的就業渠道和收入來源,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且吃穿不愁。
五有,有養老保障,符合條件的家庭成員享受低保、五保、養老等政策保障;有安全飲用水;有義務教育保障,家庭無因貧輟學的學生;有基本醫療保障,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重大疾病有救助;有住房安全保障,且戶容戶貌達到“五凈一規范”(注:院內凈、臥室凈、廚房凈、廁所凈、個人衛生凈和院內物品擺放規范)。
村退出,則叫作“十三有”。
有集體經濟收入且集體經營性收入破零,財政轉移支付使用符合規定;有帶動農民增收的產業;有通村硬化路,具備條件的通客運班車;有安全飲用水;有動力電;有住房安全保障;有通信網絡;有醫療保障;符合條件的貧困戶人口有低保養老保障;60周歲以上貧困人口有養老保障;有達標的村級衛生室,合格的鄉村醫生;有義務教育保障;農村實現有電視電話網絡、有日用百貨銷售、有文化活動場所、有村規民約“四有”。
戶脫貧、村退出達標指標分得如此之細,至于整個縣脫貧摘帽,要求更嚴,總共有14項指標。項項量化,項項嚴格,不暇細舉。條條款款,皆是真金白銀的國家投入。
縣人大定點幫扶趙家洼,縣人大領導是第一責任人。就趙家洼村的具體情況,做到“一超”問題不大,“五有”卻有難度,首先住房安全就是大問題。
村退出“十三有”,每一“有”背后都是大量的國家投入,等于重建一個新村。
比方,路得重修。簡易公路只修到小趙家洼,進大趙家洼、駱駝場還是土路。過去修的村村通簡易公路,按當時的標準,1公里預算僅為1萬元,長期不養不護,坑坑洼洼。從干線公路到小趙家洼有5公里,小趙家洼到最后的駱駝場,又是5公里,還不算跨嵐漪河的涵拱橋,十多公里按現行通村公路預算標準每公里40萬元計,投資達400萬元之巨。
再比如,“十三有”,有動力電。十多年前農網改造,趙家洼村已經完成照明電改造,如果再通動力電,變壓器擴容,線路重架,又是一筆大投入。
再比如,“十三有”,有安全飲用水。大小趙家洼人畜飲水,主要靠上世紀七十年代打下的老井提供,水源為山間地表滲水。打深井取水,趙家洼地區沒有地下礦藏,地下水層破壞倒不大,但即便打一口50米的水井,投入也同樣不菲。
“十三有”指標,樣樣無法達到。
公共汽車無法通達,學校無法建立,集體經濟歸零,村衛生室沒有,網絡信號飄移不定,是個“要甚沒甚”。反過來講,即便“要甚有甚”也是不可能,村里只剩下6戶人家13口人,一應公共設施全部建設下來,不用細算,沒有一兩千萬元的大投入休想建成。而岢嵐縣屬于國定貧困縣,農業大縣,一縣的財政收入剛剛“破億”,一下子拿出這么多資金投入到一個村落顯然不現實。況且,岢嵐縣像趙家洼這樣的村子還有115個,即便村村實現“十三有”脫貧退出,闔縣馬上就進入另外一種極端貧困。
趙家洼全村17戶未脫貧戶,總共31口人,就有18位老弱病殘,只有9人還有勞動力。留守村莊的6戶13口人,只有楊玉才、曹六仁和張秀清還有勞動力。其他幾戶,王大娘、劉大叔和劉大叔老娘的身體,李虎仁的住房安全就夠工作隊操心的。
趙家洼村,不足百年歷史。過去基礎設施差,比之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而今更差。
得搬!
不搬不行!
縣人大領導深有感觸,一開始扶貧,也跟過去一樣,落實低保、大病救助各項扶貧政策,然后給貧困戶送米送油送面,早就感覺這么個扶法不能長久,小修小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扶貧工作,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經濟維度的單純業務性工作,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貧困戶有了錢,但生活品質上不來還不行。
只能換水土,換地方,謀劃另外一種生活。
比如王三女,縣人大領導定點幫扶戶,縣人大領導出牛工錢,這幫王大娘解決了很大問題。但老太太總覺得不種地不像個農民———事實上,在趙家洼,你不種地還真不行。但工作隊的幫扶也是有限度的,天天忙前忙后,最后千說萬說,王三女同意把9畝多地連青苗出售,最后賣了不到7000元,除去各種支出,9畝地純收入也就2500元。王三女算了算賬,一年下來也就是這么多收入,沒有長余。
換水土,還得換產業,讓農民進入新業態,一年下來怎么也比這個強。
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趙家洼之后,趙家洼村和岢嵐縣115個村莊被列入整村搬遷計劃。
村子要搬,本著“自覺自愿”原則,愿意到縣上集中安置點,還是愿意回陽坪鄉中心鎮,隨大家意愿。
總書記考察形成的興奮還沒有多長時間,搬遷的消息一出,村莊很快就被另一種情緒籠罩了。這種情緒從7月開始,一直持續到9月。這中間,下過一場透雨。時間是8月22日。
持續干旱烤得人心焦,下起雨,則淋得人心焦。駐村干部來了兩年,每一年雨季,是他們最操心的時候,劉大叔的房、王大爺的房,還有王三女的房,都陳舊破敗,還有大趙家洼李虎仁那孔“一炷香”窯洞,都擔心出什么問題。
駐村干部擔心,縣城里的人大機關也都操趙家洼這邊的心。不說住房安全不安全,僅是每年房頂漏雨就讓人心煩。在雨季到來之前,縣人大必須備好另外一種物資,從縣農資供應站買幾卷厚實一些的塑料布分發到各家,然后再一塊一塊裁剪鋪在房頂上。雨下了一天,又下了一天,縣人大領導一天幾個電話打給陳福慶,隨時了解情況。
陳福慶的《民情歸志》這樣記錄這個雨天。
小雨轉中雨,在村里檢查房子漏雨情況。
昨夜3點多,雨漸弱漸強地下著。不知道鄉親們的雨布風刮走了沒有,房子漏雨嗎?村子里就數老劉的房子危險。雨還在一直下著,看天氣預報,明天沒有雨,多云。只要挨過今天,一睛,就好說了。來到王大娘家,門還是里邊掛著,里屋的門開著。等會兒再進去吧。去劉大叔家,剛好田大叔也在。看到屋子里沒有臉盆接雨,我很高興。讓老劉仔細觀察房子,有情況隨時叫我。路過曹大叔家,我高聲問了一句,屋漏雨嗎?不漏,曹大叔說。回到王大娘家,在住人這邊房子里轉了一圈,仔細觀察了一會兒,沒有漏雨的痕跡。大娘說放雜物的那邊靠煙窗的地方漏雨。我過去把雜物挪開,接了一個臉盆。等雨停了再處理吧。現在上去怕壓壞了房子。來到張秀清家,問漏雨嗎?也不漏。
—會兒縣人大領導來村,詢問鄉親們下雨屋子的情況,我做了回答。電視臺小李要去老劉家采訪,我陪著。送了小李回到工作站,飯已經快做好了。繼平說中午還有客人來,于是和縣人大領導一起早早吃了午飯,又去村里轉了一遍。還是老樣子,老劉已經放牛去了。
雨還在一直下著,綿綿小雨漸弱漸強地下著,讓人平添了一絲愁堵,也不知愁什么。
在工作站待不住,我來到趙家洼村的會場前,正巧碰上曹大叔也出來,不一會兒,王大娘也來了,吳大嬸也出來了,秀清也出來了。
大家議論今天的天氣,大家仰頭看云到底是往東還是往西,終于看清楚,云在往東行。道是:云往東,一場空。明天沒雨。
看來大家都希望雨盡快停下來,其實誰都看得到,云在亂飛。
大家出來看雨,絮絮地說著話。
雨絲被初秋的風刮過來,強一陣弱一陣。誰都明白,大家幾雙眼睛看雨絲落入田地里,看那雨霧橫山間,聽雨滴落在莊禾葉面上淅淅瀝瀝聲音的日子,今天怕是到頭了。
趙家洼村整體搬遷的日子定在9月22號,再過一個月,這村子真就消失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