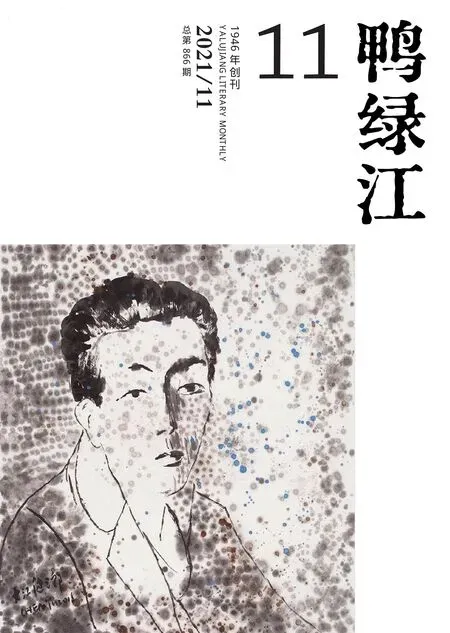出事(短篇)
牛健哲
前些天,出事了。事情與我沒(méi)什么牽連,但我沒(méi)法當(dāng)它沒(méi)發(fā)生過(guò),更沒(méi)法浮皮潦草地講它。
前幾天的我也不單純,也被心事填塞被雜念縈繞,但知道這件事時(shí)我顯然處于一種毫無(wú)防備的狀態(tài),任其沖襲而入,揮蕩了既存的大多心緒。當(dāng)然這話像是說(shuō)過(guò)頭了,事情在我起初聽(tīng)說(shuō)時(shí)確實(shí)顯得簡(jiǎn)單囫圇,后來(lái)才刀刻一般顯露出鮮艷的茬口。就像尋常看客看見(jiàn)幾只鴿子歪飛斜撞,卻見(jiàn)不到那些濕膩的眼瞼舌喙和羽毛脫落處翻露的毛囊,也聞不到它們翅膀下和肛周的氣味,然而總有人悉曉它們的五臟六腑,有機(jī)會(huì)目睹它們病變的顱腦,甚至嘗一嘗它們烤過(guò)的味道,親身體驗(yàn)?zāi)承┚N毒株的跨物種感染。
事情的講述權(quán)因人而異。我雖然沒(méi)有目擊這件事,但對(duì)其情節(jié)不會(huì)講偏說(shuō)錯(cuò)。種種人間丑劣中我最鄙夷信口雌黃,說(shuō)從不同角度會(huì)看到不同真相是相當(dāng)無(wú)賴的,只有老實(shí)話該說(shuō)。我對(duì)事發(fā)地帶熟悉,而且四個(gè)當(dāng)事人之中認(rèn)得兩三個(gè),如果我這樣聲張出來(lái)相信在任何街口都會(huì)引得聽(tīng)客圍攏。
首先你得大體上了解北環(huán)之外的師范大學(xué)。電視新聞提到引翠路時(shí)便顯得有一點(diǎn)古怪,因?yàn)槟抢锲饺罩粫?huì)被叫作師范大學(xué)西側(cè),在市臺(tái)編輯記者里占據(jù)超大比例的師大畢業(yè)生更是會(huì)脫口說(shuō)出“師大小西門兒”,我笑過(guò)他們這種故作狎昵,好像讀過(guò)的不是職高中專就足夠沾沾自喜了似的。
師大是所中下游本科院校,當(dāng)初收到它的錄取通知書時(shí),感覺(jué)像是親了一位歪嘴表姐。雖然如此,我畢竟在其中讀了七年書,別人說(shuō)它不好我其實(shí)是不愛(ài)聽(tīng)的。這學(xué)校委屈過(guò)我,畢業(yè)時(shí)我還是掉了眼淚,騎車馱走行李時(shí)還在操場(chǎng)和熱水房之間的樹(shù)林邊停下來(lái),做出女生式的回望。畢業(yè)后的半年之內(nèi),我回校看望一個(gè)留校同學(xué)有七八次之多,每次還必然用他的飯卡去食堂打飯溫故。
但說(shuō)到戀校,人與人畢竟也大不相同。我對(duì)師大有感情,可第二年這感情淡薄下來(lái),我揮散了身心之間的學(xué)生氣,后來(lái)只在一個(gè)初識(shí)的女孩要看我母校的秋葉時(shí)才回到校園故作感慨。在校部樓門前的宣傳欄前,我凝神望著一位老教授的訃告許久。我佯裝追憶故人,但沒(méi)有費(fèi)心編造一份師生緣的細(xì)節(jié),只是沉著臉嗟嘆才情虛無(wú)芳華易逝,所用劑量剛好夠讓那女孩當(dāng)晚多陪陪我。我是這樣的。然而有人離校后卻守著這所學(xué)校十幾年不惜代價(jià),當(dāng)事人田唯為此被議論多時(shí)。我早和旁人說(shuō)過(guò),師大早晚會(huì)害苦田唯,說(shuō)這話時(shí)我指的是一種隱形的、慢性的傷害,可見(jiàn)我對(duì)真實(shí)生活的想象有多局促,也活該我會(huì)為這件猝然發(fā)生的新聞事件打戰(zhàn)。但是誰(shuí)都沒(méi)猜錯(cuò)的是,師大對(duì)田唯命運(yùn)的影響果然托形于一個(gè)男同學(xué)。
季節(jié)算是深春,恍惚間我卻幾次以為身在秋天,有點(diǎn)像昏睡乍醒時(shí)辨不清窗外是清晨還是黃昏。
我認(rèn)識(shí)的另一個(gè)當(dāng)事人叫韓仕辰,不是上面所說(shuō)的那個(gè)男同學(xué),甚至可能沒(méi)念過(guò)幾年書。他是近年來(lái)唯一一個(gè)兩度到我住處做客的男性。我工作的報(bào)社東遷,為了早上能晚點(diǎn)起床上班,我租住在城市東區(qū)的老舊小區(qū)里,老舊到坑洼遍布,夜里路燈只是閃光燈似的偶爾閃閃。而他兩次都是從西邊執(zhí)意趕來(lái),而且都是在陰雨天。我有點(diǎn)懷疑他是故意這樣來(lái)讓自己顯得狼狽而熱忱的。第一次來(lái)他遲到了十幾分鐘,說(shuō)自己在這片昏暗的舊樓群里白白兜了半小時(shí)圈子,踩了好多水坑,濕透了鞋。我則說(shuō)自己早就餓了,但可以聽(tīng)他講完再做飯吃,其實(shí)我是在下班前就犯了胃病無(wú)心進(jìn)餐。這樣我們?yōu)檫@次交涉各自取得了一些微妙的心理優(yōu)勢(shì)。韓仕辰是來(lái)向我推銷保險(xiǎn)的。他是我一個(gè)大齡女友的遠(yuǎn)親,自然也沒(méi)放過(guò)她,早拉她做了客戶。
但正式開(kāi)始推銷那份人身意外險(xiǎn)時(shí),韓仕辰卻讓我另眼相看,他說(shuō)話張弛有度,居然喚起了我這種沒(méi)誠(chéng)意又有戒心的人對(duì)生死殘障的多愁善感,胃里難免更疼。講人一生遭遇不測(cè)的風(fēng)險(xiǎn)時(shí),他并不生搬硬背,也不拿一些不知有無(wú)的例子嚇唬人,而是帶些法醫(yī)的派頭,讓人隱約聞到了災(zāi)禍現(xiàn)場(chǎng)的氣味兒。更顯匠心的是,他介紹了西方的一項(xiàng)研究,研究結(jié)論是人對(duì)自己應(yīng)對(duì)災(zāi)禍后果能力的預(yù)計(jì)能夠影響災(zāi)禍發(fā)生的概率,這似乎提示了一條隱秘的因果通路。我沒(méi)法反駁那些援引有據(jù)的數(shù)字。大概半小時(shí)后,他水到渠成地拿出了合同,我下意識(shí)地握好了他遞過(guò)來(lái)的筆,像商場(chǎng)里一個(gè)本來(lái)不想買鞋的顧客,如今聽(tīng)話地把腳塞進(jìn)鞋里試腳感,踩踏的步子還是直奔收款臺(tái)邁去的。
“兄弟,這是一個(gè)活著就得有所依靠有所寄托的時(shí)代,否則我也未必做這行。”他嘆息,呼出少許同樣是空腹已久才有的口氣。
到這地步,我記不清當(dāng)時(shí)是如何扭轉(zhuǎn)局面的,總之是強(qiáng)把自己拉回本心,拒絕難免生硬。但他看明白我的態(tài)度后,只說(shuō)我以前不了解保險(xiǎn),的確應(yīng)該再考慮一下。走到門口時(shí),他跟我約了下次給我繼續(xù)講解的時(shí)間,這個(gè)我實(shí)在沒(méi)能冷臉回絕。雖然女友告訴我只要見(jiàn)見(jiàn)他就行,但送走他時(shí)我就開(kāi)始憂愁下一次見(jiàn)面的事了。這算是他的本事。不過(guò)半個(gè)月后他的下一次出現(xiàn)讓我頓感輕松甚至小有失望——他換了東家,轉(zhuǎn)而向我推銷另一種更貴的所謂萬(wàn)能險(xiǎn)。他大體不變的腔調(diào)里也流露出尷尬,我故意跑題扯些家長(zhǎng)里短生態(tài)時(shí)政他也很配合。交談間他曾唐突地說(shuō)亟須業(yè)績(jī),想要我憑媒體人的“接觸面”介紹些潛在客戶給他,這話引來(lái)一次悠長(zhǎng)的冷場(chǎng)。后來(lái)我只是問(wèn)他要不要一起吃碗面他就識(shí)趣地告辭了。當(dāng)時(shí)我便覺(jué)得自己弄懂了他這個(gè)人,他真正愛(ài)的,還是上次談的人身意外險(xiǎn)。
這個(gè)新東家是一家新興的保險(xiǎn)公司——太乙保險(xiǎn)。因?yàn)橄氲侥倪傅膸煾福覍?duì)這個(gè)名字產(chǎn)生了一點(diǎn)印象。韓仕辰自稱一到太乙就做了小頭頭,再升升級(jí)就能換換崗位。不知道他后來(lái)對(duì)公司貢獻(xiàn)幾何,總之出事后太乙在本地算是名氣躥升。
其實(shí)出事那天我還去過(guò)引翠路。當(dāng)天傍晚我乘出租車從北郊回城,天氣不太好,處于連日升溫后的一個(gè)小寒流里,還有點(diǎn)陰沉多風(fēng)。看不見(jiàn)太陽(yáng),個(gè)別灰白建筑的反光倒顯得挺刺眼。車載廣播里說(shuō)日間刮的是四到五級(jí)的東北風(fēng),陰天揚(yáng)塵容易引發(fā)呼吸道疾病,但次日起就將繼續(xù)晴好。的確在車?yán)镆材苈劦酵饷娴娘L(fēng)塵味兒,行駛到師范大學(xué)附近也沒(méi)感覺(jué)清爽一些。車行路線是從師大北面的路上西行左轉(zhuǎn),過(guò)一座北運(yùn)河橋,繞到西面。北運(yùn)河失治多年,水流一時(shí)倉(cāng)促一時(shí)遲滯。在我眼里,它是一條被低估了什么的河。剛?cè)胄r(shí),有一陣子我在河邊晨跑,領(lǐng)略過(guò)河水的腥冷之氣。記得那一階段我的心情就不大好,可與如今的怠惰不同,那時(shí)我一天比一天起得早,跑起步來(lái)貌似一個(gè)志存高遠(yuǎn)的青年。晨跑的終結(jié)是一天凌晨,我隱約看到河里漂著一個(gè)腦殼,水面之下有沒(méi)有連著脖頸和臂膀很難看出,但見(jiàn)得到腦殼上的一只耳朵。我告訴自己那是某種動(dòng)物的,但你知道,耳朵像人的動(dòng)物并不多。
畢業(yè)后剛剛工作時(shí)我還和幾個(gè)同事相處得來(lái),一次他們要找個(gè)安靜的地方打牌,我推薦了北運(yùn)河。有時(shí)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河畔雜草蠻生,那天水位很高,風(fēng)把兩張撲克牌吹進(jìn)河里,浮在水面上并沒(méi)漂遠(yuǎn)。為了繼續(xù)打牌我們猜拳決定誰(shuí)去河邊撈牌,結(jié)果我輸了。我走到河邊就呆呆地站在那兒,不肯彎腰伸手,牌終于慢慢地看不見(jiàn)了,身后的牌友都起哄嚷嚷起來(lái)。后來(lái)我多次夢(mèng)見(jiàn)自己在河邊撈撲克牌,牌無(wú)休無(wú)盡地漂來(lái),我對(duì)間或漂過(guò)的帶耳朵的腦殼和它連綴著的醬狀物并不去正視。
“嘿,這路變好走了,靜悄悄的。”出租車司機(jī)得意地說(shuō)。這時(shí)他已經(jīng)把車拐到師大西側(cè)也就是引翠路上了。
“這條路一向這樣。”我微笑,老華僑回鄉(xiāng)似的,要表露一下對(duì)一切還都熟悉。
司機(jī)卻斜了我一眼說(shuō):“誰(shuí)說(shuō)的,我哪次走這條路都堵車。”
“是嗎,你舉個(gè)例子,哪天堵車?”我覺(jué)得他這就是我說(shuō)過(guò)的那種信口雌黃,他最好別說(shuō)他也在師大讀了七年書宿舍還靠近小西門。引翠路路東大多是做學(xué)生生意的店鋪,路西矮墻外則是一片棄置多年的荒地,學(xué)生只光顧路東的店鋪,幾乎沒(méi)人橫穿路面。地界偏,車和行人又不多,路沒(méi)道理不通暢。那些店雖然有買有賣,但總熱鬧不起來(lái),人最多時(shí)所制造的也只是窸窸窣窣的微響,好像這里的空氣都不大波動(dòng)因而傳聲困難似的。這倒是很像這所大學(xué)的校內(nèi)氛圍,缺少青春激昂和輕狂爽朗。
“還舉什么例子,今天上午我還在這兒堵著呢。”
信口雌黃!我發(fā)出嗤之以鼻的聲音。為了教訓(xùn)他一下,我給留校同學(xué)打了電話,讓他回答上午小西門外有沒(méi)有堵車。我打電話時(shí)眼睛是看著司機(jī)的,也開(kāi)了免提。電話里同學(xué)說(shuō)他上午沒(méi)出小西門,師大終于開(kāi)始分家了,上午學(xué)校興師動(dòng)眾把文科五個(gè)院系向新校區(qū)搬遷,西側(cè)兩門集中出車運(yùn)輸,幾乎沒(méi)法步行出入。我掛斷電話,瞇著眼空凝前方。
“那還有哪天這兒堵車?”我說(shuō),“你再舉個(gè)例子!”
司機(jī)只譏笑兩聲,就駛離了引翠路。我也沒(méi)留心望望田唯在路邊開(kāi)的小店,那里就是后來(lái)新聞里說(shuō)的事情發(fā)生的第一現(xiàn)場(chǎng)。北運(yùn)河橋以南的引翠路只有一千多米,田唯的店附近店面又相對(duì)稀疏,但仍然很不顯眼不易指認(rèn)。記得再早一次路過(guò)也就在此前幾天,那時(shí)我倒掃到一眼,有幾家店貼著“出兌”字樣,包括田唯的。
回到住處后我自然是還不知道那件事已經(jīng)發(fā)生了,閑得查看了日歷,這天是谷雨的前兩天,也就是說(shuō)降雨即將增多,空氣本來(lái)就要逐漸濕潤(rùn)了。當(dāng)天宜嫁娶宜祭祀宜沐浴,忌入宅忌移徙忌安床。我暗罵師大校領(lǐng)導(dǎo)愚蠢,擇日不利,更不該選擇讓文科去人跡罕至的新校區(qū),文科里有師大僅有的還算有點(diǎn)名堂的兩個(gè)專業(yè)。電視里說(shuō)一周之后就是本省公務(wù)員考試的日子,建議廣大考生提前確認(rèn)考場(chǎng)位置,以免出現(xiàn)往年有些考生因?yàn)樽咤e(cuò)路線沒(méi)來(lái)得及進(jìn)場(chǎng)考試的狀況。現(xiàn)在你可以大體描繪事發(fā)的環(huán)境,并在時(shí)間坐標(biāo)上準(zhǔn)確地找到這一點(diǎn),也就是這個(gè)陰沉日子的正午,據(jù)我后來(lái)多方了解,應(yīng)該是在十二點(diǎn)十分到十二點(diǎn)半之間的短短二十分鐘時(shí)間。論急促,這在世間眾多事件的“發(fā)生”中當(dāng)然并不出眾,你講給別人時(shí)不要過(guò)于夸張。發(fā)生一說(shuō)本就暗示了瞬時(shí)性和爆破意味,不同于生長(zhǎng)和腐朽這樣的經(jīng)典延續(xù)性動(dòng)作,發(fā)生通常是不容阻滯的,像射精一樣無(wú)法挽留。延綿未絕的只是所發(fā)生事情的后效。總之第二天晚上,這件事才被報(bào)道出來(lái)。
田唯在引翠路開(kāi)理發(fā)店,之前她開(kāi)了一陣子花卉店,再回溯久遠(yuǎn)一些,她在校時(shí)是個(gè)相當(dāng)有知名度的中文系才女,和同班男生唐云齊名。兩人都被老師們器重,而且出雙入對(duì),佳話四起。兩個(gè)人支撐的讀書協(xié)會(huì)也是最長(zhǎng)命的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活動(dòng)他們倆輪流主持,搞講座把文史學(xué)科有資歷的教授請(qǐng)了個(gè)遍。可是考研時(shí),轉(zhuǎn)折出現(xiàn)了,田唯連續(xù)五年報(bào)考,五次落榜,前兩次是英語(yǔ)不及格,之后成績(jī)?nèi)€潰退。而在這五年時(shí)間里,唐云讀完了文藝學(xué)的碩士加博士,作為當(dāng)紅的人才留校任教了。我對(duì)這樁事當(dāng)然有所耳聞。我們辦公室的一個(gè)女編輯清楚后續(xù)的事。
離校后田唯在學(xué)校附近的民居租房住下,仍然時(shí)常來(lái)校和唐云同進(jìn)同出,出現(xiàn)在圖書館或者系里,專注地辯論一個(gè)個(gè)古代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問(wèn)題,有時(shí)也會(huì)紅著臉爭(zhēng)起來(lái)。前兩次考研,唐云是陪著田唯進(jìn)考場(chǎng)的。兩人的緋聞自然更被熱傳,但傳舌的人們后來(lái)漸漸覺(jué)得沒(méi)趣了,因?yàn)閮扇硕紙?jiān)持以單身自居,在一起時(shí)也的確只聊學(xué)問(wèn),好像真的只是學(xué)術(shù)知音。
為這些事我本來(lái)是沒(méi)興趣費(fèi)神的,但社里那女編輯搞文化文藝版,和唐云有往來(lái),跟我講了太多他倆之間的事。女編輯外聯(lián)時(shí)熱情活絡(luò),在辦公室卻冷顏冷色,又像我一樣中午不喜歡出去消閑,與我對(duì)坐著甚顯尷尬。后來(lái)我發(fā)現(xiàn)她很喜歡聊文化人私生活,說(shuō)到興奮時(shí)是很久都不需要?jiǎng)e人應(yīng)和的,說(shuō)完后也能把那種和顏悅色延續(xù)許久。估計(jì)師大中文系是她能接近的不多的幾個(gè)文化圈子之一,學(xué)院小生唐云是她版面的供稿常客,雖然有的文章顯然是田唯代筆的。反正一旦態(tài)勢(shì)需要,我就不客氣地把唐田組合的話題拋出來(lái),由女編輯接應(yīng)發(fā)揮,自己似聽(tīng)非聽(tīng)地得以養(yǎng)神。
有一次,女編輯去學(xué)校找唐云,見(jiàn)到田唯在唐云的座位上替他寫教案,冷淡地說(shuō)唐云病了。女編輯要去看望唐云,田唯卻說(shuō)他是做了個(gè)小手術(shù)在臥床康復(fù),不方便見(jiàn)客,報(bào)紙約他寫的文章她寫完會(huì)交稿。女編輯見(jiàn)到了田唯在教案上寫下的清秀又有力道的字。講到這兒她又嘆息起來(lái),田唯后來(lái)怎么會(huì)去做理發(fā)生意?
聽(tīng)說(shuō)了她的店之后,我去理過(guò)一次發(fā),她不大說(shuō)話,開(kāi)始推鬢角時(shí)我才問(wèn)她記不記得我,說(shuō)在校時(shí)我進(jìn)過(guò)她搞的讀書協(xié)會(huì)。她哦哦了兩聲,仍沒(méi)有熱絡(luò)起來(lái),我也沒(méi)法聊來(lái)前特地又翻看了的幾本名著。那次我的左鬢被剃得接近光禿,耳后的一個(gè)癤子也被剮破了。后來(lái)我又聽(tīng)說(shuō),雖然唐云也在那里理發(fā),但每次只讓田唯剪一點(diǎn)點(diǎn),遵循著一種少量多次的風(fēng)險(xiǎn)控制原則。
我本不想俗氣地把人的改變都聯(lián)系到他們的深心情感,覺(jué)得唐田兩人其實(shí)都別無(wú)所長(zhǎng)孤單無(wú)依,借著談學(xué)論道相互作伴也是寂寞人生常有的某種心態(tài)。可是按照這種理解再去聽(tīng)兩人后來(lái)的消息,就會(huì)滋生出一些不屑。女編輯說(shuō),去年寒假過(guò)后,唐云退了教師宿舍,在田唯住處的對(duì)門租下房子。兩人開(kāi)始極其自然地逗留在對(duì)方那里。唐云搬去不久,兩人請(qǐng)朋友們?nèi)ネ孢^(guò)一次,大家發(fā)現(xiàn)他們各自的家里居然都有對(duì)方的衣物,而且還會(huì)當(dāng)眾做出一些親近的舉動(dòng),比如公然用同一個(gè)杯子喝水。
田唯偏胖,人還算白凈,有點(diǎn)輕微的跛腳,我打聽(tīng)過(guò),據(jù)說(shuō)是她小時(shí)一次腿傷后父母都輕忽了醫(yī)治造成的。對(duì)唐云我印象不深,我只在大三下學(xué)期參加了幾次讀書協(xié)會(huì)的活動(dòng),那時(shí)他已經(jīng)不怎么出現(xiàn)了。在女編輯手機(jī)照片里唐云兩眼浮凸笑態(tài)輕狂,個(gè)子不小但上身短促兩腿細(xì)長(zhǎng),有一頭油黑卻卷曲的頭發(fā),比我頭腦里的模樣更讓我感覺(jué)不適。如果說(shuō)這兩個(gè)人口稱清白,實(shí)際上真存在某種曖昧勾當(dāng)?shù)脑挘沂怯X(jué)得有些惡心的。于是有一天女編輯再次說(shuō)起他們時(shí),我沒(méi)忍住動(dòng)了些怒氣。
“那就是說(shuō)他們至少交換過(guò)體液咯。”
“那怎么算,那碗湯可能唐云確實(shí)只能喝下一半,田唯又不想浪費(fèi)。”女編輯說(shuō)。
“那就是喝人家的口水嘛,明擺著是性欲的表現(xiàn),還有什么可說(shuō)的!”我的嗓門有點(diǎn)高。
“你怎么這么說(shuō)話?”女編輯皺著眉頭瞪我,扭臉不再作聲。
過(guò)了兩天,女編輯竟然讓另一個(gè)同事私下轉(zhuǎn)告我,讓我別以為她很看好我,于公于私都“不是那么回事兒”。詫異過(guò)后我被氣樂(lè)了,我跟她有什么關(guān)系,何來(lái)的看好與否?從此我們?cè)僖矝](méi)聊過(guò),直到出事的第二天晚上,看過(guò)電視新聞之后,我決定給她打個(gè)電話,與此同時(shí),她把電話打了過(guò)來(lái),我們不計(jì)前嫌地聊了四十分鐘。
師范大學(xué)協(xié)調(diào)了本地的媒體,報(bào)紙不采寫這件事,電視新聞里也沒(méi)透露唐云的教師身份,只說(shuō)是兩男兩女,兩個(gè)女的是外地來(lái)打工的堂姐妹。就這樣,曾經(jīng)的師大名人田唯只被說(shuō)成是外來(lái)務(wù)工的打工女。她堂妹的事是女編輯間接探明的。這個(gè)堂妹比田唯小十來(lái)歲,曾經(jīng)被寄養(yǎng)在田唯家多年,差點(diǎn)過(guò)繼。最近堂妹來(lái)投奔堂姐,住進(jìn)田唯的住處,說(shuō)要邊打工邊參加師大的自學(xué)考試。求職未成的階段,這堂妹曾經(jīng)幫唐云打字,打出了一部書稿,后來(lái)去了一家小醫(yī)院做接待服務(wù)。
照常理兩男兩女這種人物構(gòu)成是相對(duì)穩(wěn)定的,促發(fā)超常事件的概率并不高。師大好像也有傳言說(shuō)現(xiàn)場(chǎng)可以算是有五個(gè)人,但靠虛加人數(shù)來(lái)編排事情的誘因不是君子所為。
一個(gè)多月前,堂妹搬出了田唯的住處,不知落腳何處。有人說(shuō)她是被田唯趕出去的。而這一階段,唐云介入了學(xué)校的工會(huì)工作,開(kāi)始操心一些教工福利的事。據(jù)說(shuō)順利的話,唐云日后會(huì)做系副主任。他仍然去田唯的理發(fā)店剪頭發(fā),只是開(kāi)始有了固定的日期節(jié)律。事發(fā)那天正是他該去的日子。
得知情況的當(dāng)晚我就沒(méi)睡好。一段時(shí)間以來(lái),為了跟蹤一個(gè)家具廠工人在車間致殘的新聞,我常往城北的那家家具廠跑,路過(guò)北運(yùn)河和師范大學(xué)的次數(shù)是多了一些。也許是因此,我又被一種學(xué)生氣的敏感侵襲了。家具廠的老板是我們報(bào)社副總編的朋友,很強(qiáng)硬的一個(gè)人,堅(jiān)持說(shuō)那個(gè)傷殘工人是在下班后因?yàn)樗饺嗽蚍祷剀囬g出事的,橫豎不肯負(fù)責(zé)。如果不是受到一個(gè)勞動(dòng)者權(quán)益組織施加的壓力,他也許根本不會(huì)開(kāi)口找我們副總編幫忙。也就是說(shuō),我去本來(lái)是該幫商家解圍的,但見(jiàn)過(guò)工人那殘存的半個(gè)下頜和露出臉側(cè)的舌頭之后我突然就不敢輕率地寫稿子了,因而因?yàn)椴蓪懖缓蠌S方老板的意思,還見(jiàn)了人家的冷臉。老板身邊有兩三個(gè)身板硬實(shí)的糙漢吸煙吐霧,有一個(gè)似乎是有意地對(duì)著我打了個(gè)噴嚏,讓我情緒不佳。在床上,我回想那個(gè)工人洞開(kāi)的側(cè)臉,思緒卻總是漂移到田唯的堂妹那里去。我想她一定是個(gè)不丑的女孩,有一副貌似伶俐的模樣和一股果味口香糖的味道,穿著像似護(hù)士裝的粉色套裝就會(huì)沾沾自喜,不覺(jué)得自己該認(rèn)真地反思什么,也沒(méi)想過(guò)自己僅有的東西會(huì)在頃刻間被剝離踐踏……
過(guò)了些日子,我以為這件事已經(jīng)得到了足夠的甚至過(guò)度的品咂。到了五月,天氣大幅度地暖熱起來(lái),我想剪短頭發(fā),想到了田唯那間必然不復(fù)存在的理發(fā)店。左鬢被剃禿時(shí)我和那個(gè)大我?guī)讱q的女友交往密切,她見(jiàn)了我的怪模樣和耳后的血痂就要弄清楚那是哪里的手藝,執(zhí)意要替我去算賬。她平常對(duì)我頗多調(diào)笑,像對(duì)待晚輩后生似的,那是她第一次因?yàn)槲叶J(rèn)真,我倒兇了她幾句。后來(lái)我們只是偶爾聯(lián)系,她結(jié)婚了,嫁的人挺老但挺好。我想借著這件事再找她聊幾句,沒(méi)想到通電話時(shí)她丈夫就在身邊,更沒(méi)想到她仍然粗聲大氣地和我聊以前。我還沒(méi)開(kāi)口提理發(fā)的事,她就說(shuō)起她的遠(yuǎn)親韓仕辰了,我這才知道當(dāng)事人里的男性之一竟然就是險(xiǎn)些做了我保險(xiǎn)顧問(wèn)的他。
電話那邊察覺(jué)不到我的神色,她丈夫幾次叫她,她都懶得理睬,繼續(xù)說(shuō)韓仕辰的事和她親戚圈里的反響。
“對(duì)了,據(jù)說(shuō)那天是那個(gè)女孩拉著他去的,出事兒之前他陪她染頭發(fā),等了一個(gè)多小時(shí)。也有人說(shuō)他本來(lái)就是要去跟師大工會(huì)的人談業(yè)務(wù)的,想談下一個(gè)團(tuán)體大單,唉……”她說(shuō)。
“那個(gè)女孩?哪個(gè)女孩?”
“就是那個(gè)年輕女孩——新聞里沒(méi)說(shuō),是韓仕辰的同事。”
我沒(méi)興趣告訴她事件里那個(gè)理發(fā)師就是她曾要討伐的人,而那女孩是理發(fā)師的堂妹了,只問(wèn):“那個(gè)女孩不是在一家醫(yī)院工作嗎?”
“什么啊,其實(shí)是……哎呀我說(shuō)不清楚,老頭子你來(lái)!”她居然要讓她丈夫和我直接對(duì)話,“我家老頭子和韓仕辰混得最熟。”
結(jié)果她家的老頭子比她羞澀,講給她幾句就走開(kāi)了。她只聽(tīng)了個(gè)大概,告訴我那女孩的工作單位不是醫(yī)院,是一家體檢中心,名字叫霞光太乙健康體檢中心,是太乙保險(xiǎn)跟別人合辦的,聘了二院和婦嬰醫(yī)院的一些退休醫(yī)生。韓仕辰與體檢中心過(guò)從不淺,盤算著用一些手法搞業(yè)績(jī),然后升職接管其他險(xiǎn)種的推廣。電話里她盡力描繪這兩個(gè)人物,又試圖說(shuō)清楚女孩和韓仕辰曾是怎么互相幫忙、那天又是怎么纏在一處的,我還是沒(méi)太聽(tīng)懂,然而這幾分鐘之內(nèi),腦皮層的眾多神經(jīng)突觸悄然完成了迅速勾結(jié),編織出新的網(wǎng)絡(luò),我對(duì)整樁事的理解被更新了三分之二。
“反正這小姑娘膽子挺大,那天也使了心勁兒,是帶著自己那份體檢報(bào)告和超聲圖去的。”
我腦袋里回閃著那則新聞和辦公室女編輯的神情,還有某些傳聞,感官似乎變得超常地敏銳,比如那種現(xiàn)場(chǎng)其實(shí)有五個(gè)人的說(shuō)法,這時(shí)猛然生出狂誕的回音……這感覺(jué)讓我莫名地汗毛刷動(dòng),恍若開(kāi)悟,稍后同時(shí)念及事情的幾條脈絡(luò)時(shí)我又好像重新糊涂了,然而這糊涂絕不等同于此前的糊涂,好比見(jiàn)到死蝌蚪忽地蹬出兩條后腿,便不會(huì)再當(dāng)它是蔫丑的死魚(yú),只會(huì)暗自忍受新的不適感。我的嘴巴久久地半張著。
思路可以整理,但我還是決定不做任何主觀猜測(cè)。摹想臆測(cè)無(wú)非是想擴(kuò)大事件的信息量,而這件事對(duì)我這個(gè)層面的知情者來(lái)說(shuō),本身已經(jīng)足夠刺眼足夠銳利了。我要說(shuō)的唯一帶一些主觀色彩的,就是事情發(fā)生之后我們應(yīng)該如何自處。總結(jié)出事后生活的指南才是略有裨益的。這種總結(jié)必然不會(huì)有條理而又整齊地完成。現(xiàn)在我只能說(shuō)我要盡快找到一種滑脫的方法,甩開(kāi)家具廠報(bào)道的事,從此也不會(huì)輕易再去師范大學(xué)附近,不會(huì)對(duì)北運(yùn)河和引翠路過(guò)于留心,不會(huì)與出租車司機(jī)爭(zhēng)辯什么。要記著自己居住在老舊破敗的城東,身處破敗才會(huì)讓人顯得年輕些,凌亂地回憶當(dāng)年并不會(huì)。我再也不會(huì)那么厭惡那些比我更加執(zhí)拗甚至昏恣成性的人,卻也不會(huì)理會(huì)他們,無(wú)論他們叫人膩煩還是令人惱火,命運(yùn)對(duì)他們自有相稱的安排。去找一個(gè)自以為會(huì)與之熱絡(luò)起來(lái)的人理發(fā)是挺蠢的,如果有人剃壞了你的鬢角弄破了你的癤子,你應(yīng)該當(dāng)即放聲叫出來(lái)。
別太關(guān)心某些相識(shí)者,別在電視新聞里看本城的案件。要學(xué)會(huì)看電視,睡覺(jué)前不要看第二次、第三次重播的片子,你會(huì)被此前未曾發(fā)現(xiàn)的細(xì)節(jié)攪亂心緒,可能出現(xiàn)病理意義上的興奮。可以播放那些把心思都用來(lái)拉投資的綜藝節(jié)目,把音量調(diào)到舒服,放任自己每晚開(kāi)著電視睡著。
應(yīng)有盡有了。關(guān)于事情的紋路,估計(jì)沒(méi)有誰(shuí)能悉曉更多。最后,附帶贈(zèng)送給你們兩件小事。一件是一個(gè)外地的同行告訴我的,有一次他們市搞的一個(gè)文化論壇邀請(qǐng)了唐云,但因?yàn)檫€請(qǐng)了外省的幾位知名學(xué)者,唐云發(fā)言沒(méi)有得到充裕的時(shí)間,末尾還被截?cái)嗔藥拙洹J潞筇圃圃谫e館房間里號(hào)啕大哭,路過(guò)門口的人都聽(tīng)得見(jiàn),似乎他在頭上蒙了被子,但有些高音還是很尖利。這事我沒(méi)對(duì)女編輯說(shuō)過(guò)。
另一件是我那位大齡女友在電話里講給我的,她那天講韓仕辰講得暢快,把與引翠路上的事有關(guān)的無(wú)關(guān)的都說(shuō)了。說(shuō)的是他們?cè)谝粋€(gè)婚禮上聚了頭,桌上談起保險(xiǎn)的事,韓仕辰起初沒(méi)開(kāi)腔,后來(lái)有人提到了他這個(gè)從業(yè)者,朝他問(wèn)這問(wèn)那,他終于講起了他疏遠(yuǎn)已久的人身意外險(xiǎn)。他放下筷子,比較了幾家公司設(shè)計(jì)的意外險(xiǎn)產(chǎn)品,指出了關(guān)鍵的差別,還有板有眼地援引了保險(xiǎn)合同條款細(xì)則和保監(jiān)會(huì)的規(guī)定,當(dāng)然總的來(lái)說(shuō),他對(duì)這類保險(xiǎn)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該買。這觀點(diǎn)亮出來(lái)后,桌上就有兩個(gè)人開(kāi)始一唱一和地譏諷,后來(lái)開(kāi)始與韓仕辰唇槍舌劍地爭(zhēng)吵起來(lái),說(shuō)推銷保險(xiǎn)的都?jí)虿灰樀摹4簖g女友的老頭子喝多了酒,早就躺倒在一旁,錯(cuò)過(guò)了這場(chǎng)戲。韓仕辰一口酒都沒(méi)喝,因而在爭(zhēng)吵時(shí)也沒(méi)拿出醉漢的氣勢(shì)。散席后,韓仕辰還若無(wú)其事地開(kāi)車送一車人回返,包括大齡女友兩口子,其中一個(gè)參與爭(zhēng)吵的人也被安排進(jìn)來(lái),還帶了一個(gè)孩子。
婚禮在鄰近一個(gè)小城鎮(zhèn)舉行,是晚場(chǎng)的。開(kāi)車回城的路上天已經(jīng)黑了,但公路上路況還不錯(cuò),大家乏累了,沒(méi)怎么說(shuō)話,倒是有打鼾聲。在幾個(gè)人都昏昏欲睡時(shí),車突然發(fā)生了一個(gè)急劇偏轉(zhuǎn),在迎面奔來(lái)的大貨車面前癲狂地晃了一下,大貨車強(qiáng)勁的鳴笛聲驚醒了大家,這時(shí)韓仕辰已經(jīng)利落地?cái)Q轉(zhuǎn)方向盤,回到了正常的車道上筆直行駛。車上剛剛有些人發(fā)出了驚叫,然后看著沉默不語(yǔ)的韓仕辰,都垂下調(diào)門,乖巧地歸于隱斂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