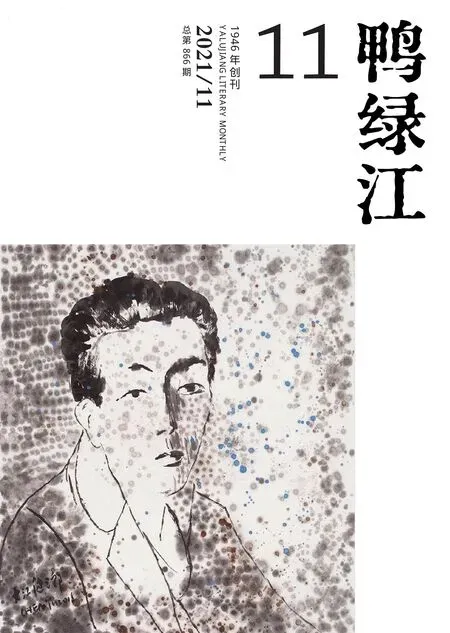編輯林建法
潘凱雄
記憶中初識林建法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事,他那時還在福建省文聯主辦的文學理論批評雜志《當代文藝探索》工作。那是一個文學的時代,也是一個批評的時代,當時全國至少有一半的省(直轄市)都有自己專業的文學理論批評雜志,現在還剩幾家就不一一清點了。《當代文藝探索》還有一位林姓編輯,當時與我對接業務的,正是那位林焱。我肯定是見過他的,可與建法是否見過已記不清了,不過信倒是通過,那也是一個傳統的通信時代。但無論哪種方式,和建法的“初識”,總還得從那個時間算起。
也記不清這種“初識”究竟過了幾年,時間應該不是太長,時任遼寧省文學理論批評雜志《當代作家評論》的主編陳言來京組稿,身邊跟著的“小伙計”之一就是林建法。我與陳言相識是1983年在煙臺舉行的一次文藝理論年會上,由于是“老”相識,所以再見面也就沒了那些初見時的客套與寒暄。盡管陳言的蘇北普通話十分難懂,但還是知道了建法因為愛情而毅然“背井離鄉”調入夫人傅任的家鄉遼寧工作,成為陳言麾下的一員大將。也正是從這時起,我與建法開始了一段長達十余年的“蜜月期”。
盡管這則小文的主題是 “編輯林建法”,但還是想再饒舌幾句,繼續說說陳言。我不否認再說陳言是因為他畢竟是建法的直接領導頂頭上司,上行下效也很正常。但更重要的是,在我眼中,陳言不僅是一個好人,更是一位好主編;不僅是一個好領導,更是一位好文學編輯。在我印象中,這位1945年便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一點也看不出當年軍人的影子,坐在你對面,也不明確地約稿,一口濃重的蘇北鹽城鄉音吐出來的滿是對文學作品與文學現象的看法與評價,盡管他講的話,我最多只能聽懂五分之三,但還是為這位長者的閱讀量之大和思考之勤而折服,面對這樣的編輯,你自然會產生一種信任與信服,有了稿子自然會想到請他賜教。我想這就是所謂高級的文學編輯吧。而在陳言身旁工作的建法,有幸時常耳濡目染這樣的“高級”,應該自會潛移默化地得到許多收益。
當然了,建法還是建法,別看他平時臉上老笑瞇瞇的,但從內里看,他其實是一個挺倔強的男人。有時想想那時的《當代作家評論》也挺好玩的,一家北方的文學理論期刊,卻偏偏為兩個“南蠻”執掌。建法的“福普”倒比陳言的“蘇普”好懂得多,可他偏偏要固執地入鄉隨俗,三句話下來就動輒一個“整”字。他來約稿,不像陳言那樣侃侃而談,坐下來后,就只是笑瞇瞇地不停地重復五個字:“你整一個吧!”此時,無論你找什么理由,在建法那兒就像是耳旁風,甚至干脆充耳不聞,依然是不停地笑瞇瞇地重復著“你整一個吧”,直至你不得不應允下來。這種軟磨硬泡的功夫倒是好文學編輯的另一套路。
當然,建法這種軟磨硬泡的背后,其實也有硬招在支撐。和他交流,他雖不似陳言那般侃侃而談,但你會感到他的確閱讀了大量作品,這種硬功夫,自然會無聲無息地體現到他工作的雜志版面上。特別是在他接班雜志主編后,那一組組評論小輯的推出、一組組文壇爭鳴的組織,如果沒有編輯鮮明的主觀意圖的灌注和浸潤,是很難形成這種格局的。人們常說一個好編輯對一個作者或一部作品是何等重要,這其實還只是一個好編輯好作用的一個部分。對一本雜志一家出版社而言,一個好主編,更可以對一本雜志或一家出版社的大格局、大氣象產生直接的影響,進而再影響到一個行業一個領域,歷史上這樣的案例實在不少。我想,某種意義上,建法也是可以成為這種案例的。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鋪開和走向深化,文學的轟動效應日漸式微,文學期刊的流金歲月已然逝去,文學評論期刊的日子不好過了,有限的事業經費已很難支撐一家刊物的正常運營。本文開篇所說的全國至少有一半的省市以上都有自己專業文學理論批評雜志的盛況,也就是從這時開始逐步萎縮,關張或易轍者不在少數。這時,建法的能耐就不僅僅是“整”點選題“整”點稿子了,而更要“整”點銀兩補貼刊用。于是,我們在《當代作家評論》的扉頁上就看到了一欄“古里古怪”的“理事會”名單,而出任理事者多為工作在不同行業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所理之事其實只有一件,那就是輪流贊助刊物一點費用以維護其運轉。這個“理事會”的名單是流動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建法卻從那時開始,在主編大名外又多了一個新頭銜:“理事會秘書長”。這個秘書長究竟承擔了多少功能我說不清,但我知道,交際絕對是主要功能之一,通過交際實現成功化緣,保證刊物運轉。當然天上從來不會平白無故地掉餡餅,建法換來餡餅的招數有哪些我也說不清,但良好的服務肯定是必需的。在這個過程中,建法的變化是明顯的,他本不善飲,一杯啤酒能完整下肚已是上佳表現,但這個秘書長幾年任下來,其灑量居然也能將一桌甚至幾桌妥妥地支應下來了,臉龐雖然紅撲撲的,行為言語卻絲毫不受影響。可見,如果不是先天的生理反應,人在這方面的能量還真有著巨大的提升空間。
那些年,建法“秘書長”究竟為雜志拉來多少支持,我自然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當代作家評論》在當時依然辦得風生水起,那種大環境的經濟影響在這里似乎也沒激起啥漣漪,可他自己,那時的生活卻十分簡樸,而且簡樸到難以令人置信。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去過他家,普普通通的兩室一廳,面積在當時倒也還說得過去,但整個家中除去最基本的生活設施,最富有的只是書與雜志,在占滿一面墻的書柜之外,剩余的,就那么一垛垛地整齊碼放得老高老高。坐在方凳上聊過一會兒,我很想找把椅子靠著說話,可這才發現,居然一把都沒有,無論啥材質的都沒有,就連他書桌旁放著的也是方凳。顯然,在他家待著只能選擇三種姿態:端坐、直立、“躺平”。我勸建法至少為自己在書桌旁置辦一把椅子,這樣看書編稿累了也可以靠一下,結果他的答復卻是,坐在凳子上看書看稿精神容易集中。唉——這又算哪門子的苦行僧邏輯呢?
就這樣,建法在“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大背景下接手陳言執掌的《當代作家評論》后,雜志依舊被他“整”得“風風火火闖九州”,一個省級的地方性文學批評專業期刊硬是“整”出了全國性大影響。完全可以不夸張地說,那個時候任何一位重要的作家評論家、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一個新鮮的文學現象,都會在這本地方性專業刊物上留下自己專業而學術的痕跡。人們當然有權利不同意其中的某些評價,但雜志的職能從來就不是簡單的裁判長,而是有眼光、有胸懷的園丁精心栽植培育的一方百草園。也正因為此,對今天任何一位研究新時期中國文學史的學者來說,《當代作家評論》都是他必須納入參考和引證的重要文獻。
進入新世紀后,由于我的工作發生變化,編輯雖依舊,但審稿與運營的繁忙和壓力使自己不得不與“評論”漸行漸遠,與建法的交集也日漸稀疏。盡管如此,還是不時能從不同渠道聽到建法又“整”啥了的若干傳說,而且“整”的范圍似乎還越來越大,方式也越來越多。再往后,耳邊傳來的,竟然變成了建法身體出了狀況、正在四處求醫、住進了醫院……他曾經也來北京天壇醫院,我和王必勝去探望,看到他人雖略顯木訥但精神還好,天壇醫院當時的診斷是“帕金森”,這個又有“領袖病”之別稱的神經系統疾病,目前雖無根治之法,但維護得好也不至于索命。說好日后再去探視,可他竟于次日不辭而別回了沈陽。再往后,就只是偶有間接的消息傳來,說他似乎還住在沈陽的醫院里與病魔抗爭。屈指算來,建法竟也已過了古稀之年,那就好生養息吧,別再“整”了,爭取早日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