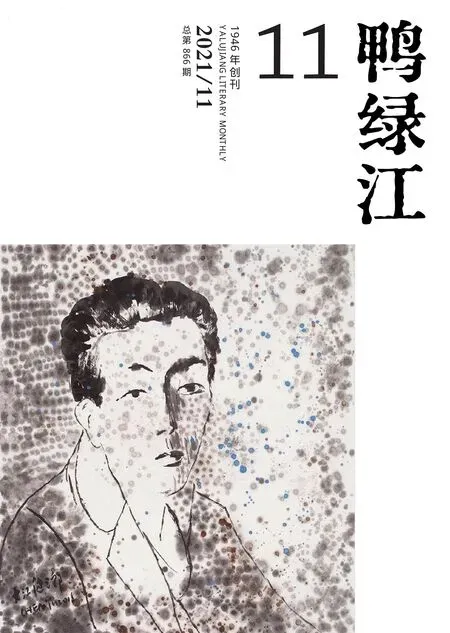論文學創作中的情感活動(節選)
林建法
二、道是無情卻有情
上面,我提出“作家藝術家的感受和情感是偉大創作的生命”,認為“作家藝術家必須在情感最飽滿的時候創作”“沒有生活的強烈感受,沒有強烈的愛和恨,沒有難以抑制的創作沖動和內心要求,不會創作出好的藝術作品”。
有人提出了一些異議,并以名言作論證:
你是否趁你的朋友或愛人剛死的時候就作詩哀悼呢?不,誰趁這種時候去發揮詩才,誰就會倒霉!只有等到激烈的哀痛已過去……
——狄德羅《談演員》
要到你覺得自己像冰一樣冷的時候,才可以坐下來寫。
——契訶夫《論文學》
我以為情感正烈的時候,不宜作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魯迅《現地書》
毋庸置疑,這三位文學大師說的都有道理。不過,我提請諸位注意:他們在這里所講的“哀痛”“情感”,還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情緒”之上,而不是我所說的“情感”——“審美情感”。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情緒和情感是有很大區別的,情緒主要是和無條件反射聯系著,具有顯著的生物性,所以一般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總是把情緒和本能相提并論。而情感主要是和條件反射聯系著的,情感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高級社會性情感,是伴隨著認識活動和意志活動所出現的,一般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深刻性。我所講的審美情感,就是這種感知、理解、想象和情感四種主要因素的和諧的自由結合,是認識內容同心理形式的統一。正是從這個角度,我講情感是偉大創造的原動力,是藝術的生命。其次,所謂“情感正烈”時不宜創作,這話的意思是,寫情感不宜實寫,要經過醞釀,經過提純才好。作家的藝術構思過程,常常是一種情感積蓄和處理的過程。他體驗、理解和整理人物的情感,總是同人物的性格交融在一起進行考慮,這樣,某種情感就只能為某個人物所獨具,彼此是難以取代的。寫情感,尤其應該注意其“詩化”,經過提純和詩化了的情感,同活生生的人物性格交織在一起,因而人物性格也就隨之詩化了。再次,我說情感是偉大創作的生命,這當然不是說凡是情感的自然表露都是作品。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說的:“如果一個人在體驗某種情感的時刻直接用自己的姿態或自己所發出的聲音感受另一個人或另一些人,在自己想打哈欠時引得別人也笑起來或哭起來,或是在自己受苦時使別人也感到痛苦,這不能算是藝術。”(《藝術論》)所以,我以為,作家藝術家要使自己在觀察、體驗生活時所產生的情感在文學藝術中得到表現,就不能只聽憑自然情感的驅遣,還必須對強烈的情感進行一番提煉和整理,“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感受、體驗與評介、解釋,情與理要互相滲透,互相促進,最后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只有這樣,作家藝術家才不會沉湎在自發的情感中不能自拔,從而創造出激動人心的藝術精品。
蘇聯學者尼季伏洛娃根據列夫·托爾斯泰的創作材料,對托爾斯泰的文學構思做了認真的研究,她認為產生托爾斯泰的文學構思的直接原因,主要的、典型的有兩條。一條是他熱心研究人們生活的基本問題并尋找解決的方案,尤其是同他個人生活有關的和屬于道德方面的問題。同時,他的突出之點在于,他打算通過揭示社會現狀的根源來理解社會現狀和理解自己。他對歷史的興趣也是由此而來的。他在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的序言草稿中說,他這部作品的構思的緣由,是搞清十二月黨人運動和當時俄國社會的歷史根源。他1865年3月19日寫道:“我讀拿破侖和亞歷山大的歷史讀得入了迷。現在我感到喜悅,因為我覺得我可能寫出一部大作品,實現我要描寫亞歷山大和拿破侖的心理活動的發展的想法。一切的卑鄙,一切的空談,一切的瘋狂,一切人間的矛盾,一切周圍的事物以及他們本人。”從這段摘記可以清楚看到,托爾斯泰之所以為拿破侖和亞歷山大的歷史所吸引,是因為它涉及他對人的看法。他十分痛恨那些虛偽和滿嘴漂亮辭藻的風氣。這種強烈的愛憎之情是他產生文學構思的原動力。托爾斯泰的構思出現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是他對他所感知的一切現實現象具有異乎尋常的強烈感受性和同情心。他的特點,是他對激動他的人和事具有一種“幻想”,也就是作為他的美學表現的“幻象”。
我們仔細考察《復活》的創作過程是頗有意義的。1887年6月,托爾斯泰從法律活動家科尼那里聽到一件訴訟案:一個普通的姑娘被一個貴族青年欺騙的故事。托爾斯泰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他最初的構思是以這一訴訟案為基礎,寫一本道德教誨的小說。但是,由于當時感性材料還不充分,構思還不成熟,所以沒有立即動筆。但這個故事一直激動著他。1889年12月,托爾斯泰的日記中記載:“科尼的故事的外表形式我腦子里已經清楚了。應該從開庭寫起。這就便于暴露司法機關的偽善以及表現他(小說主人公)的正義的要求。”但是在當時,《復活》的寫作并沒有多大進展。作家曾經不止一次著手來實現自己的構思,可是每次都落了空。1895年11月5日,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散步時我很清楚地理解到,為什么我的小說《復活》沒走上正路?開頭就是虛偽的。這一點,在構思描寫兒童的故事《誰是對的?》的當兒,我理解到,應當從農民的生活開始寫起,他們是主體,是下面人物,而別的東西是影子,是反面的東西。關于《復活》也是如此。應當從她開始。想馬上就動筆……”托爾斯泰又興致勃勃地寫了一段時間,又把它擱下了。關于寫作這部作品的難處,他在日記中說:“科尼的故事不是產生在我自己的心里,因此就顯得棘手。”1897年1月5日,托爾斯泰在重談已經寫好的幾章時,對于其中描寫聶赫留朵夫決定娶喀秋莎的那幾章時,始終是感到極端地不滿。“一切都虛假、杜撰、拙劣,”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著,“很難修改已經寫壞了的東西。要修改就必須:描寫他和她的感悟和生活。對她的——肯定而嚴肅,對他的——否定而嘲笑。看來我未必會完成這本書。一切都已經弄得很糟。”以上材料表明,托爾斯泰為什么會經受那么多創作上的痛苦:開始寫《科尼的故事》時,情節相當狹窄,無法展開,后來寫《復活》時,容量令人驚異地擴展開來,同時,又有了高度集中、目標專一的情節。這部內容廣泛、布局錯綜復雜、包含著當代生活各個方面的巨著的構思,使托爾斯泰最后無比激動。1898年下半年他最后一次重新著手寫作《復活》。他是那么專心致志,以至于一天到晚都想著此事。1898年10月21日,他寫信給巴·阿·布朗熱說:“在寫《復活》的時候,我很慶幸自己能有機會來專心從事于自己的藝術活動,而且還因為這件作品有了更大的價值而感到自慰,可是,實際上我只不過像個醉漢那樣全心沉溺于一件心愛的事,而且工作得那樣津津有味,簡直整個從頭到腳被工作吞噬了進去。”就這樣,經歷了十一年漫長歲月,驚人的杰作《復活》終于問世。列寧給予很高的評價,他指出:“托爾斯泰的批判所以有這樣強烈的感情,這樣的熱情,這樣的說服力,這樣的新鮮、誠懇,并有這樣‘追根究底’要找出群眾災難的真實原因的大無畏精神,是因為他的批判真正表現了千百萬農民的觀點的轉變,這些農民剛剛擺脫農奴制度獲得了自由,就發現這種自由,不過意味著破產、餓死和城市‘底層’的流浪生活等新災難罷了。”(列寧《列·尼·托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復活》的力量的重要來源也就在這里。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藝術家從生活中獲得感受,產生創作沖動,本質就是一種情感上的激動。沒有發自內心的情感上的愉快和激動,就不會有創作。接著在典型化的過程中,正是以情感的發展為動力,推動聯想和想象的風輪的運轉,又是在認識生活邏輯基礎上形成的情感邏輯,決定了作品中人物的命運和作品的完成。最后,在藝術傳達、作品修改的過程中,作家藝術家進行字斟句酌,反復推敲的依據,也還是能否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具有復雜內容的感受和情感。所以,我認為,作為文學因素的情感,不能是瞬間即逝的一時沖動,或脫離思想普遍意義的感性,它必須被現實喚起,被思想提高。作為構成文學因素的思想,也不再是以抽象形態出現的各種觀念,它必須融化在藝術形象里面,充分得到情感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說,文學創作中的情感只能是一種經過思想深化的情感,文學創作中的思想,只能是一種被情感滲透的思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講情感是偉大創作的原動力,是藝術的生命。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過去的一些文學批評中,對于諸如果戈理、契訶夫、魯迅等以諷刺、幽默見長的文學大師,有時會被認為是孤獨冷靜的人,善于嘲諷的人,正是出自對審美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巨大作用的曲解。其實,冷漠和孤僻與文學大師們絕對無緣。如果他們只是這樣的一些人,就不能忠實地反映他們的時代,出色地描繪他們的鄉土,也就不會和未來的生活相通。實際上,果戈理、契訶夫、魯迅,一個個都是非常熱情的人,他們的作品充滿健康樂觀的氣氛,他們文學的功業,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時代。不錯,果戈理、契訶夫、魯迅都是杰出的諷刺作家。那什么是諷刺呢?魯迅認為,諷刺的生命是熱情,是對祖國和人民的愛,是對民族弱點的慈善智慧的鞭策,是對未來幸福生活的熱烈的希望。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是俄羅斯一個時代的生活的橫斷面。在這部作品里,他不只是把那些地主吝嗇鬼和騙子鑄成典型,還把他對祖國的熱烈的希望,也就是作為一個忠實兒子的情感,也寫進去了。一部書里,包含著作家的全部心血,以及他的理智的見解和情感的奔流。正如他在獻給普希金的一篇文章中所說:“一聽到俄羅斯這個字,我們詩人的眼睛就更光亮了,他的眼界也更擴大了,他仿佛莊嚴了許多,比較任何人都要來得偉大。自然,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愛國的熱情。”
魯迅也從來不是那種“冷靜,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的作家,即使在他的十分嚴峻的現實主義小說里,我們仍會感覺到那種有時埋藏得很深的理想和激情的潛流。正如郭沫若所說:“魯迅并不冷,魯迅的冷,應該解釋為不見火焰的白熱。他是壓抑著他的高度的熱情,而不使它表露在表面。他的冷是炙手的冷,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冷……”(《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3)“靜默觀察,爛熟于心”,經過長期磨煉形成的寓熱于冷、熱得發冷的性格,成為魯迅作品的主要風格。強烈的愛憎用不著紛繁的色彩來粉飾,深沉的情感也無須華麗的言辭來渲染。魯迅就是以這樣毫無粉飾的筆墨來直抒情感,著墨不多,而情態畢肖,遠比那些堆砌艷詞麗句的描寫具有更大的表現力,將自己強烈的愛與憎表達得淋漓盡致。比如,對于祥林嫂受到致命打擊時的神態,他這樣寫道:
“你放下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成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地站著。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才走開。
這樣的描寫,是極其簡練而樸實的。這是一個受盡封建禮教迫害的婦女,在最后的生活希望突然受到打擊時完全絕望了的神態。在這一失神的狀態里,凝結著祥林嫂一生的悲苦與辛酸,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猙獰面目,同時也包含著作家的控訴聲,這難道不比“救救孩子”的振臂高呼更能使人心戰栗嗎?而從魯迅另一篇小說《明天》中單四嬸子的太大、太空、太靜的感覺里,我們所感到的階級壓迫,不是遠遠地超出了個別惡霸的猙獰和兇殘,而浸透在廣袤的大氣里,漫無邊際地壓來,早已“四面壓來,叫他們喘氣不得”了嗎?通過這一感覺的描寫,作者就真切地表達了這個苦難者在喪失了人生一切樂趣之后的絕望和悲哀的心情了。《故鄉》中,“我”感到與閏土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時,作者也只寫道:“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也說不出話。”的確,深沉的悲痛之情有時反會使人默默無言。然而,此時無聲勝有聲,道是無情卻有情,這里包含著多么深刻的思想感情啊!魯迅的小說,以清醒嚴峻的現實主義令人注目,正是藝術上達到的爐火純青,高升為不見火焰的白熱的表現。魯迅思想感情中那種既極清醒又分外深沉的個性特征,文學作品中那種火一樣的熱情包裹在冰一樣的冷靜中的美學風格,使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成為一位劃時代的文學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