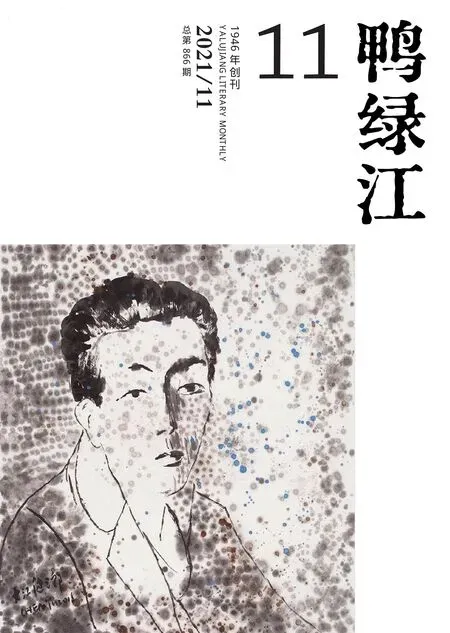猜度陳忠實的秘密及其他(評論)
陳 誠
1
1880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語文愛好者協會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普希金在精力最旺盛的時期與世長辭了,無疑把某種偉大秘密帶入了墳墓,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來猜度這個秘密。”我懷著無比的敬意,將這句話獻給陳忠實先生。《白鹿原》和“白鹿原”的秘密已被帶走,而眾多研究者只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來猜度他的秘密。
2
2019年4月26日,在《小說評論》和西安工業大學文學院合辦的“陳忠實精神遺產學術研討會暨陳忠實先生逝世三周年追思會”上,先生的女兒陳黎力在發言中談道:“懷念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讀他的書、評他的書。”我當時在現場,感動得一塌糊涂。忠實先生去世后,有很多悼念文章,大多真切動人,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好事者有消費先生的嫌疑。眾多悼念文字的背后,其實還有許多無聲的悼念,比如我的前任主編李國平先生、西安工業大學的馮希哲院長,等等。他們都是忠實先生至為親密的同事、朋友、忘年交。他們把記憶和悲傷一同深埋,幾乎不著痕跡,卻又每每在追思會上涕淚縱橫,不能自已。我入職時,忠實先生已經退休,工作中有過為數不多的交集,大多是遠遠仰望的狀態。即使在聚會的飯局中,也僅止于有限的寒暄和交流,說是有限,大概也遠多于他的普通讀者和崇拜者吧。我之前選擇無聲地悼念,更多是出于不忍打擾,同尊敬的逝者保持敬畏和距離。而此番重讀,姑且算作“評他的書”,并以此來懷念。
3
做人和做文章其實是相通的。當我們從事文學批評、研究的時候,首先必須保持一種站立、平等的姿態,不卑不亢,不要躬身膜拜,也不要居高臨下。其次,應該有一種尊重、和解的姿態,充分地理解作家、熟悉作家,根據支配作品的精神來閱讀作品,主動去尋求靈魂的碰撞,尋求靈魂的遇合和搏斗,如同錢理群先生提出的“與魯迅相遇”“他要進入你的內心,你也要進入他的內心,然后糾纏成一團,發生靈魂的沖突和靈魂的共振”。
編輯工作中,最為糾結的時候,就是讀到與《白鹿原》相關的評論文章。我不期待有新的材料發現、新的闡釋路徑(其實大多屬于重復研究范疇),我只是渴望那種能與忠實先生、能和《白鹿原》發生靈魂碰撞的個體閱讀、個體感受。但遺憾的是,除了雷達先生的《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等少數篇什,幾乎沒能讀到我中意的文章。所以,我也嘗試著自己去解讀,就像今天的批評家們不滿意創作現狀,而去親自操刀創作一樣。但我發現自己的解讀是淺薄的,始終不可避免的就是拾人牙慧。或許說不盡的《白鹿原》已然被人說盡了吧?
4
關于《白鹿原》,最值得言說的,我以為不是史詩性,不是魔幻現實主義,不是傳統的重建、現代的反思,不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收煞、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開啟,而是文本中傳達出的歷史意識,以及捕捉時代情緒、與時代共情的能力。
我曾把《田園詩與狂想曲》和《白鹿原》對讀,在有關清末民初的關中地主、宗族勢力、“宗法農民文化”“貧農的性自由”“禮教的性禁錮”等話題上,發現有頗多印證之處,亦有一些觀念相左,或者說事實出入的情況。如果去證實或證偽這些“出入”和“相左”,我以為意義不大。一是社會科學的田野調查分析,一是文學藝術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拆解,本身不在一個領域。且那一時期的歷史,兩人都不是親歷者,而是從各種政府性文件、地方志、田野調查、口述史中探尋得來。美籍印裔學者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曾提出“復線的歷史”的概念,“復線的概念強調歷史敘述結構和語言在傳遞過去的同時,也根據當前的需要來利用散失的歷史,以揭示現在是如何決定過去的”。在他看來,過去并非只是直線式的延伸,而是擴散于時空之中。歷史往往根據現實需要來收集那些與當下有利的散失的過去,而重新整合的歷史話語又對現實形成某種制約,二者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關系。因此,不管是文學藝術的變形呈現,還是社會科學的調查分析,我們所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現實需要來收集和建構的。所以,去深究或者試圖抵達那段真實的歷史,本身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最多能做到的,不過是努力接近而已。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段歷史是否能與現實映照和關聯,是否有助于排解現實的焦慮,是否有助于解決現實的問題。
5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看革命的歷史,要離開革命的那個時代,所謂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就是要強調一定的距離感”。“保持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上的距離就可以擺脫功利的束縛和視野的局限,從更廣闊的、深入、超脫的角度來觀察和評價歷史。”但是,也有歷史學家告誡我們:“太過耽溺于‘后見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則偏向于以結果推斷過程,用來反推回去的支點都是后來產生重大歷史結果的事件,然后照著與事件進程完全相反的時間順序倒推回去,成為一條因果的鎖鏈。”《白鹿原》之所以能成為“20世紀90年代初文學的、也是思想文化的具有標志性的事件”,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還是作品中傳達出的歷史意識。作者不全是從今天的歷史高度、今天的距離感、今天的“后見之明”去反向推導歷史,而是撥開種種歷史的成見和迷霧,表達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歷史語境中的大多數人共同的,或者共通的,面對歷史大變局時,油然而生的“鏊子”的困惑,以及“所有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這是一個生活演變的過程,也是歷史演進的過程”的清醒。
這種歷史感,或者說歷史意識的獲得,不全是作者自己在書齋中冥想、體悟出來的,這與他當時身處的時代氛圍息息相關。《白鹿原》的寫作過程歷時約4年,從1988年4月1日到1992年1月29日。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正是處在思想文化領域“亮”與“灰”更迭的時代語境之下。其間有各種思想交鋒,各種思潮涌動,也有各種偃旗息鼓,各種暗淡混濁,變得模糊,變成雜色。而此時,也正值“中華民族經過反思、探索,開始走向全面振興,尋求科學的發展道路,整個民族正處在一個轉型期,從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前行的時期”。正是作者感受到了這一時代的氣息,捕捉到了這一時代的情緒,與時代同行、共情,并融入自己對于歷史大變革,以及身處歷史轉型期的個體認知與思索,《白鹿原》才成為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大書,才具備了跨越時空的經典性意義和價值。
6
《白鹿原》的歷史意識,以今天的“后見之明”來看,不過是常識之論,但放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卻是得風氣之先。這既是作者獨立思考的結果,也是現實的需要和時代的召喚使然。
20世紀90年代以降綿延至今的家族小說,幾乎都避不開《白鹿原》“影響的焦慮”,動輒百年歷史風云,動輒家族國族命運纏繞,動輒民間匪行敘事愛恨情仇。除少數走出“焦慮”的強者,大多令人耳目一“舊”。讀過前20頁,就大抵知道后面該如何展開,如何收尾,故事的脈絡、人物的命運盡收眼底。殊不知,歷史意識、時代情緒才是這種類型小說之鵠的。制造故事是容易的,甚至經過創意寫作的訓練,把故事講得精彩也是不難的。難在哪里呢?難就難在深知如下常識,卻還是習慣性地故意避而不見,比如是選擇“合唱”還是“獨唱”?是獨立思考還是盲隨大流?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呼吸時代氣息,感受時代情緒,還是借助二手體驗,獨守書齋閉門造車?
歷史意識的獲得,需要一個上下求索的過程。往上,探求幾千年歷史、文化、思想的流變;往下,印證、反思、超越“此在”的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生活。如果做不到,那就最好不要強求“史詩”的宏大抱負,而力有未逮地去抻長歷史。反而應該縮短歷史的長度,把自己熟悉的年代、過去經歷的生活,與正在經歷的生活,進行映照與對讀,從而在文本中獲得歷史的縱深,與時代和讀者共情,尋求心靈的共振。
7
巨細靡遺地記錄時代,可能是一種本領,但并不值得夸耀,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也能做到,甚至記錄得更科學、更細致、更合理;“傳聲筒”般地圖解時代,可能也是一種本領,但同樣不值得稱贊,因為跟一條拙劣的廣告一樣,達不到想要的宣揚效果。找到那個“點”很重要,哪怕只是一個橫切面。
魯迅作品中,我尤為鐘愛的兩篇,一是《在酒樓上》,一是《孤獨者》。這兩篇小說,錢理群、王曉明等諸位先生已經有過精彩解讀。我之鐘愛,可能是隨著閱歷和年齡的增長,有幸與魯迅、呂緯甫、魏連殳“相遇”。從出版到現在近百年的時間,依然能準確觸摸到那一時代的情緒,且能感同身受與當下現實生活的深刻關聯。這種時代情緒,不是通過濃墨重彩地渲染歷史情境得來,而是聚焦于時代中的人,把人物置于核心位置,深入熨帖地體察知識分子的現實困境和精神危機,勾畫出他們吶喊過后的猶疑和彷徨,其中也飽含著作家的自我審問、自我剖析的心靈獨白。他選擇從個人透見時代,而不是在時代中描繪個人,時代的立體感、親切感,自然就撲面而來。
弋舟的“劉曉東系列”(《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盡頭》)亦是我所鐘愛。弋舟大抵也是魯迅的“粉絲”,比如對精神世界近乎偏執的剖析,比如《等深》中的周又堅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比如一些遣詞造句的“別有用心”,都可窺見魯迅的影子。弋舟把親歷的夏日風暴與一代人的精神潰敗聯系起來,在并不久遠的歷史和滾燙無聊的現實之間折返穿梭,獲得了歷史的縱深,時代的情緒也被拿捏得恰到好處。我們了然,那場風暴也許并不是若干年后一代人潰敗的全部理由,所謂理想的幻滅也有可能是被現實生活打敗。周又堅的兒子周翔,面對“不義與羞辱”,不是選擇權宜、茍且,或是退縮,而是亮出他們的短刃,可誰又能預測到周翔的潰敗是在什么時候,但這重要嗎?并不。
陳春成的短篇集子《夜晚的潛水艇》令人印象深刻。博爾赫斯的迷宮,汪曾祺一樣的語言,《紅樓夢》的古韻雅致,無傷大雅的政治諷喻,以及虛實空間的營造、節奏感的掌控,老練到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一位90后作家。《竹峰寺》《紅樓夢彌撒》寫得尤其出彩,但擊中我的卻是《夜晚的潛水艇》一文。主人公充滿奇思妙想,在夜晚把書桌想象成操縱臺,把房間幻化成潛水艇,整夜冒險遨游。但現實生活中,升學、工作從多方制約,面對母親的哭泣,父親的無助神情,“我”只能壓抑幻想,變得“開竅”,可也因此想象力變得稀薄,再也進入不了潛水艇,只能遠遠觀望。一代人成長的代價,以及這一時代的特殊氛圍被詩意地傳達出來。那些似曾相識的成長路徑,共同經歷的長成之痛,那些現實生活中的“輕”與“重”,引起了眾多掙扎于現實的讀者的深切共情。
8
拉拉雜雜,寫下這些跑題的文字,不過是平時得來的一點讀書筆記,或是一些斷想。《白鹿原》是否已經“說盡”,我不得而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特別是新一代的年輕讀者,能走入《白鹿原》,和忠實先生“相遇”。倘若遇見了,就一起喝釅茶,抽雪茄,飲西鳳,吃羊肉泡饃,聽華陰老腔,閑話白嘉軒、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的家長里短。倘若沒能遇見,也沒有關系,畢竟“讀他的書”,也是一種懷念。
注釋:
①[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馮增義譯,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頁。
②錢理群:《與魯迅相遇:北大演講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頁。
③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現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
④[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⑤楊奎松:《走進真實——中國革命的透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1頁。
⑥葛劍雄、周筱赟:《歷史學是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頁。
⑦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頁。
⑧陳曉明:《鄉村自然史與激進現代性——〈白鹿原〉與“90年代”的歷史源起》,《學術月刊》2018年第5期。
⑨李國平:《陳忠實:將自己滾燙的手指按在時代的脈搏上》,中國作家網2019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