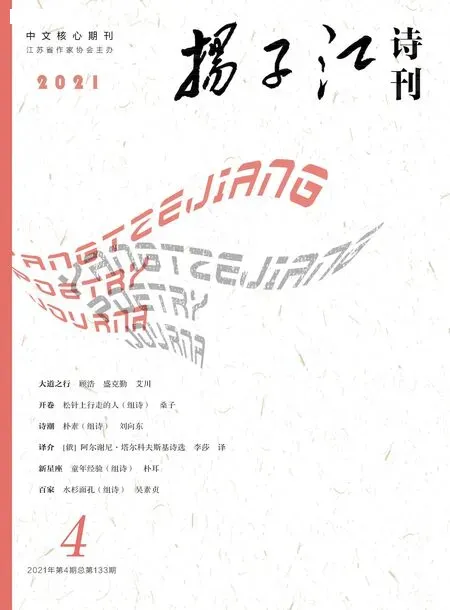自己的贗品(組詩)
潘玉渠
與友人書
在濟南,我們是英雄山下的兩只螞蟻
耗盡無數個黃昏游弋書海
只是為了打撈記憶,或尋覓前程。
日子摩肩接踵,很快
我們便丟失了許多心愛的風景
我們在舜耕路上挖穴
同室而居;趴在泉水抬高的泥土里
寬慰或稀釋彼此
秋季來臨之前,我搭乘風的履帶
前往巴山夜雨的國度,做一個
遠走他鄉的人。而你
在繼續堅守兩個春天之后
也向南撤出一截麥芒的距離
從此,各自構筑新的巢窠
孤軍深入,迎戰時光
天涯相望亦有比鄰之感。或許
直到心肝脾肺胃多米諾骨牌般坍塌
才能將報廢的自己
還給濟南,還給那段
共同的記憶。
午夜火車
回家的路很漫長
在地圖上,卻只是短短的三十多厘米
雖然,粗纖維的江河、村鎮、田畝
統統被忽略不計了,我仍然清楚
雪飄在風里,家
就坐落在一盞遙遠的燈下。
其實車廂內也有燈,淺淺地閃著
低溫的光;也有陌生人
東倒西歪地睡著,散發出
生活的咸澀味
他們同我一樣身似浮萍
每年一次以被動之姿
由一只巨大的手拖曳著
穿過夜的洞穴
穿過一個個別人的故鄉
好在火車每哐當一下
家就會近一些
再近一些。
自己的贗品
最近一次相見,是三年前的正月初二
在你位于洪村二十九巷的出租屋里。
透進西窗的暮光下
你凌亂擺放的家當——
雕刀、拖鞋、水杯和零鈔
蜂擁擠進我的眼睛。
我們圍繞理想與生計,喟嘆
或爭論;圍繞學生時代的往事
給出迥異的定論——
仿佛不經意間
我們對人生的認知
有了巨大的變更,被時光打磨成了
自己的贗品
這讓我想起九年前的那個初夏
我拎著兩個甜瓜看你時
你的居室干凈,有序
你也正在偏西的日頭下
伏身書案,細細勾勒
縱深的理想。
十二月一日
桉樹撐開的清晨
如一頁單薄的故事
努力迎合人的口齒。十二月一日
比十一月的每一天都要短幾寸
但,樓群浮華,車流遲滯
是一樣的。鴿子仍會從草坪的邊緣
侵入沉睡者的閣廳:
調試喉管,矯正夢境,乃至打翻
酒瓶里的癮
比煙絲稍冷的孤寂感
則被漂洗干凈,等待最終的煉制。
在十二月一日,風
并不急于判決那叢枯蔫于窗下的綠菊
指針在墻壁上大肆圈地
讓忙得團團轉的時間
叫出聲來;而生活
在窗簾上映出泥濘的星辰
讓這個冬日的清晨
瞬間渾濁了一些。
對峙
進門后,男人在鞋盒上
刮蹭了下泥水,又順手將購物袋、花束
同雨傘并排立在墻邊
這個習慣性動作,鈍器一樣
敲碎了女人的好心情
兩人為此對峙了整整一夜
仿佛一對反義詞
或許他們認為,對峙
能夠以其中一人的投降
重塑愛情的輪廓和生活的細節
但事實并非如此——
清晨,他們各自吃過早餐
先后走出家門
雨傘、花束和購物袋仍在原地
鞋盒上的泥水,也已凝結成塊
宛如被鎖定的罪證
偶遇
三個月后,我們再次在金陽街相遇
我看到你驟然發福的身體
似乎有過勞的嫌疑:眉宇間的倦色
宛若秋日余暉
西風撩起你的衣領,暴露出
脖子上散射狀排布的溝壑。
你摘下眼鏡,低頭擦拭
伴隨著幾聲嘆息,談起工作的蟲眼兒
和婚姻的魚尾紋
仿佛那些瑣碎的情節
徹底綁架了你的軀體。但你又說:
“生活有著既定的邏輯,
今日辛苦,是為了來日的安逸……”
當你的手機響起——
(老板催你加班的命令)
我們握手而別,各自轉身
就好像今日并未相遇
而我所見到的
只是另一個自己。
羈旅之人
羈旅之人,蟄身于角落,不言語
是最妥帖的。電影中
漂浮在酒水里的影子,以及高濃度的啜泣
是女主角的武器;而她深愛的男人
舉起酒杯,摔得粉碎
留下一地玻璃碴兒,徒然地
折射出吊燈的光芒……
你想阻止他,替女人討回公道
(在黑暗中捏緊拳頭)
但你終究無法修正他們
不對等的愛情。要知道
電影里的角色
大都有著內置的使命
借助一己的肢體與話術,推導
另一個人的悲喜
你又能替代得了誰呢
甚至,他們還有可能走下銀幕
與你在現實中的明處
相逢,或重疊。
在小酒館
當一本書剛翻到扉頁
你突然覺得,不應該寫完的故事
讀一句都是罪過
然后將書合上,到小酒館中
拆解內心,構建曠闊的幻境。
在這里,幾幅速寫的裸體
轉述著陳年往事
聽完陌生人的解析,你再一次
確定自己的判斷:
刨除釀制愛情的功用
你英俊的皮囊,不過是一件
酒杯式的道具
“游戲結束,再來一杯”——
你將自己攤開在玻璃質的喧囂中
大劑量的尖叫、音樂,以及
酒瓶擁擠之聲……
此刻,都是藍色的;只有你
是開闊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