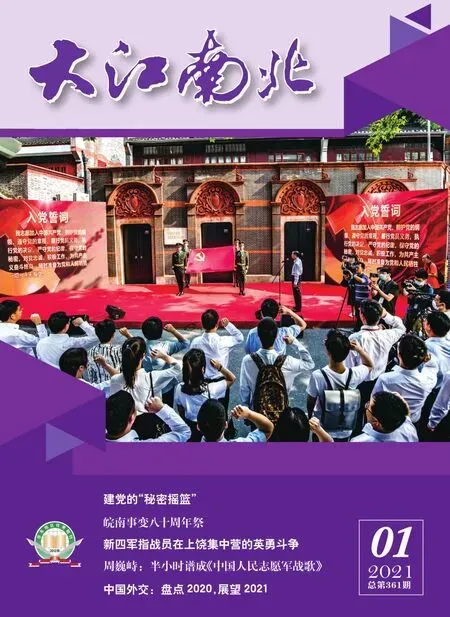我親歷農村改革第一個沖擊波
□ 張 韌
在我們黨的百年歷史上,有著多次里程碑式的重要會議,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翻天覆地般的改變,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其中之一,這次會議所帶來的巨大沖擊波,我是親身經歷的,所以至今記憶清晰,可謂刻骨銘心。
1978年9月底,我離開省城合肥,去蕪湖地委和當涂縣報到,崗位是縣委副書記。過了國慶,縣委安排我去省委黨校學習,為期三月。我在的那個班,多為縣委書記。大家主學哲學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每天聽聽議議,讀讀寫寫,早出操,晚娛樂。
12月的一個清晨,我吸著冬日的涼氣繞著操場跑步,聽到大喇叭里播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心想:這下學習要換新內容了。但,我并沒意識到,從此,我將和全國千千萬萬個縣委書記一樣,面臨著新中國30年來歷任縣委書記們所沒經歷過的工作環境。
黨校當晚就熄不了燈,大家拿著報紙,憑著直覺激動起來,東一攤西一圈地自發討論:“經濟為全黨工作中心,那階級斗爭算第幾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不就要窮的窮、富的富嗎?”
有的在經過一夜“理性”思考后,第二天深沉地問:“今后集中抓經濟工作,究竟廠長大還是書記大?”“黨員能不能先富起來?這算帶頭轉移重點的好同志,還是算他私心太重?”
哈,課堂討論的時間不夠用了!飯桌上、宿舍里、走廊外甚至廁所里一片爭辯聲、宣告聲、疑問聲和開心的哄笑聲。盡管大家一時還消化不透三中全會公報,但全體學員對中央確立“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群情歡騰,完全接受,都認為:人折騰人的日子,算過去了!
第二年麥收后,當涂縣委的難題就開始了。鳳陽小崗村農民秘密搞大包干的風聲悄悄地卻是飛快地傳遍農戶:“聽說人家已經各種各的地,各收各的麥了”,“聽說省里不反對”。
縣委很清楚,安徽有幾個縣已經“放”掉了,省委的態度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允許試行聯產到隊、到組、到戶等各種形式的農村生產體制。問題在于當涂怎么辦?當時縣委一班人總的不想“放”,因為1978年,當涂工農業總產值近三個億,其中縣級工業一個億,全省第一,就是在全國,也小有名氣,正要往新目標沖呢,這集體一散伙,還搞什么?當涂的糧食產量、農業總產值也名列前茅,搞砸了,誰負責?據說江蘇華西是因為集體的底子厚,散不了。可是,這風起云涌的大包干勾住了農民的心,我們的實力又不如華西,能頂得住嗎?再說,我們縣委不想放手大包干,究竟算是馬列主義的“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還是“當涂特殊論”在作怪?我們自己也說不清。
夏天,縣委書記許春波讓我回合肥時找省委書記聊聊,他說:“你是女同志,年輕人,好說一些,問個底吧。”我找到了省委書記顧卓新(注:1977年夏,黨中央為解決安徽省的問題,改組安徽省委,委派萬里為省委第一書記,顧卓新、趙守一為省委書記,從外地來皖任職)。顧是個堅毅爽快的北方人,不假思索地給我交了底:“當涂再看一看也可以。如果你們繼續搞集體生產,省委不會說你們‘左’;如果你們都搞了大包干,也不會說你們放棄集體經濟成果。要看多數老百姓的意向,看實踐效果。”這番話,讓我喜得感到坐著的板凳都快化開了。這一刻,我這個年齡雖不大卻已領受過“文革”以來各種各樣批判的干部,真正體會到了什么叫解放!回到縣里一傳達,大家也一輕松,都說:省委不給我們扣帽子,我們互相之間也別扣,邊干邊研究。
1979年秋,中央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生產體制仍未作規定,強調允許農民因地制宜、自主經營。冬天,每年例行的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會召開了。大會上,縣委的意見不太明朗,傾向維護集體生產形式。討論時,社隊干部吵了個一塌糊涂。有的為縣委不明確而發火發急,有的為集體積累將付諸東流痛心疾首。有的問:“如果包產到戶了,隊里的公用倉庫怎么辦?拖拉機分給誰?”有的說:“你操什么心?只要同意大包干,我就有辦法分!”有的罵:“你小子吃現成飯不知創業難!”有的笑:“你老家伙死腦子一條道走到黑!”嘿,炸鍋了!當然,也有人盤著腿抽悶煙,有人干脆開溜,這會差點開不下去了。
縣委決定一邊組織春耕生產,一邊深入調查研究。1980年開春時,局勢更加明朗。無論圩里還是崗上,許多農民不出工了,他們背靠山墻曬太陽,軟抗。社隊干部說話已不靈,縣化肥廠的化肥也難賣動。農民很清楚,全省許多地方實行了大包干,他們也要走這條路。縣委一看,耽誤生產啦,不行!立即放了個“響炮竹”:各社各隊都可以根據當地農民的意愿決定生產形式,但不能一窩蜂吃光用光分光。
1980年5月,本縣西河公社龍潭大隊窯灣生產隊長水從寬和會計李廣洲,在學習外地經驗的基礎上大膽改革,將全隊化為4個小組,以組為單位,聯產承包,并合理分配了隊里的各類資源,得到本隊農民積極擁護。
像雪崩一樣,不少社隊20年來一貫制的集體出工一夜就取消了;像春筍一樣,許許多多的新形式新辦法一夜就生長出來了。本來最傷神的問題是好地孬地分不均,農民用了個最公平簡單的辦法:抓鬮;本來最擔心的是防汛大堤沒人修,農民自定新政策:有人出人,沒人出錢雇人;本來抓“雙搶”要費勁開誓師大會,層層動員,這年夏收夏種時節,當干部的、做工人的、捧書本的,都早早趕回家“支農”了。
當然,集體經濟的壇壇罐罐也被打碎了一些,有的孤寡老人一時沒人照應,縣財政花幾百萬進口的插秧機只能先靠邊,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不過,那些產品好、管理好、有市場的社隊企業還是被保留下來了,后來發展成上規模的企業。畢竟,農民是識貨的。
1981年7月,當涂全縣平穩地實現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且縣農業總產值繼續上升了。就這樣,這一支混合著懷疑與希望、交織著激奮與歡樂、追求著發展和解放的農村改革第一樂章告一段落。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自那以后,農村的生產體制和生產方式又發生了許多變化,全國的縣委、縣政府面對著不斷冒出來的新情況,著手解決新出現的問題。也許,在今天看來,當時的我們未免可笑,可是,我經歷并見證了新中國農民第一次在黨和政府的放手支持下,各自選擇不同的生產體制和方式。至今想起這一段來,仍然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