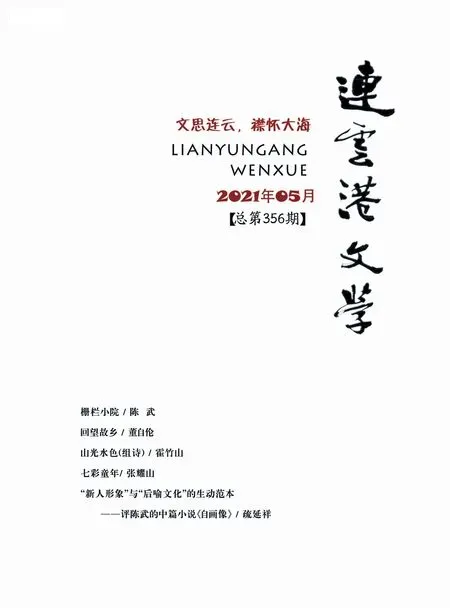“新人形象”與“后喻文化”的生動范本
——評陳武的中篇小說《自畫像》
疏延祥
一、藝術與金錢
1950 年夏天一個酷熱的夜晚,俄裔美籍畫家羅斯科(Mark rothko)向藝術同仁心談論起他貧困潦倒時的情形。他說,如果誰肯每月給他600 美元,他將心甘情愿地將自己以前所畫的和以后要畫的畫全部奉送給他。
藝術往往淪為金錢的奴隸,中西皆然。羅斯科愿意為金錢作畫,齊白石也是。陳武的《自畫像》(《十月》2021 年第1 期,《作品與爭鳴》2021 年第3 期轉載)就寫了一群為了金錢畫畫的藝術工作者。魯先圣是這群人的頭,他在畫家村畢加索路十七號租了一間平房,門楣上寫著:“先圣畫廊”。雇了陳大快和胡俊兩位畫家,一同作畫。他們之間不是同行為了切磋藝術而走到一起,而是為了生存,即金錢這個目標,他們之間是雇主和雇員的關系。魯先圣負責接活,接到活后,三人往往根據需要,緊密協作,完成客戶的需要。所以,從本質上,他們的工作和匠人沒有區別,他們的畫也只能叫匠畫,沒有創造性,沒有自我。小說一開始,魯先圣接到從梵高的故鄉——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樁大單子,要他們畫梵高的《自畫像》《向日葵》《星夜》《豐收》《咖啡館》各一百張。這個開頭暗含一種諷刺性。梵高是為藝術而獻身的圣徒,魯先圣他們是藝術服務于金錢的奴隸。
此后,魯先圣三人的工作就是臨摹這五幅畫作,陳大快敏感到老魯就此要賺一筆,想增加工資,老魯沒有答應,大快不想成為老魯的賺錢工具,就借機跳槽。因為荷蘭方面有時間限制,老魯只好從市場上挑了藝校學生的六十幅《自畫像》等梵高的畫作,以此充數,交給荷蘭的商家。這是明顯的弄虛作假,說是商業欺詐,也不過分。老魯的行為在今天的商業社會比比皆是,人在金錢面前,職業道德常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
老魯為錢作畫,小說中的白色鳥亦如此。她最初也在老魯的畫廊,一旦學到本領,看清了市場運作的規律,就從老魯的畫廊跳出單干,她比老魯更不在乎藝術的本質,赤裸裸地追求金錢。因為熟悉公關,她在藝術市場上玩得風生水起,一幅臨摹米勒的《晚禱》,可以賣到四萬,莫奈的《稻草垛》系列六幅可以賣到十八萬,這都使老魯自愧不如。其實,白色鳥在小說中是作為今天畫家中的成功者來描寫的。這是金錢的成功,而不是藝術的成功。相對于白色鳥,老魯只能是失敗者。因為在胡俊也走后,老魯就面臨著關閉畫廊的危險。好在老魯因為有了一趟荷蘭之行,感受到大師梵高的畫作和生活的關系,認識到藝術之路在原創,在表達自我。為了金錢的臨摹,對藝術才能的提高毫無用處,其藝術道路只能越來越窄。
我覺得,《自畫像》中的老魯有點像最近馮驥才《藝術家們》中“三劍客”的楚云天、洛夫、羅潛命運的復活體。楚云飛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中,一方面能感受到時代的變化,一方面又能堅持自我,所以獲得了成功,成為畫壇領袖。《藝術家們》中感覺最敏銳的洛夫先是追逐先鋒和新潮,后來熱衷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被拍賣市場的資本玩弄得頭昏腦漲,筆力漸漸枯竭,又被一個郝俊俘獲,當他的畫筆再不能掙錢時,壓力山大,最后自殺。羅潛功力最深,然而時乖命蹇,無人賞識,最后只能在老城開一家油畫店,畫“商品畫”謀生。老魯為市場、為金錢而畫,可是因為他遇到了翁格格這個看似單純的女孩,但她堅持初心,堅持藝術是要表達真實,表現自我,終于使得老魯幡然醒悟,開始回到原創的道路。如果比較《藝術家們》和《自畫像》,白色鳥的所作所為,很像《藝術家們》中善于經營藝術品的郝俊,她漂亮精明。長袖善舞、活力四射,把洛夫帶向了市場,帶向了一時的成功。《自畫像》中,陳大快投向白色鳥,接受白色鳥的調教,假以時日,不是沒有成為《藝術家們》中的洛夫的可能。從某種意義上,我以為《自畫像》可以看成是《藝術家們》一定意義上的濃縮版,兩者可以參讀。
二、“新人”形象與“后喻文化”的生動范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小說創作領域,“新人”形象是一個熱門話題,其中以柳青的《創業史》中梁生寶形象最為引人關注。作為一個20 多歲的青年共產黨人,在黨和政府的引導下,梁生寶成了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對合作化運動,他比老黨員、老農民要積極主動得多。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鐵凝的《哦!香雪》寫了一個落后鄉村女青年對城市文明、對文化的向往,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寫了國有企業青年劉思佳對體制改革的熱心,他們都是改革開放初期“新人”形象的代表。
“新人”形象和青年有關,他們是朝氣和活力的象征,沒有保守觀念。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青年還和中國共產黨以及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有關,他們是國家層面時代精神的體現。我認為,陳武的《自畫像》樹立的翁格格是另一種新人形象。翁格格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但她的進取精神、遠大理想和我列舉的上述“新人”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翁格格是一個藝校的畢業生,剛剛走上社會。她和老魯發生交集是因為她要找工作,老魯正好缺一個臨摹梵高畫作,以應付荷蘭方面商業需要的畫師。從藝術技巧上說,翁格格比老魯、陳大快、胡俊、白色鳥等人要稚嫩得多,但是在精神上,她比他們卻富有得多,也正派得多。老魯他們都是臣服于金錢的人,藝術已經淪為他們追求金錢的工具,他們臨摹梵高,那是商業行為,而不是出于對大師的崇拜。因為在藝術市場上混跡,老魯等人已漸漸淪為匠人,不知原創是何物,整天都在畫梵高、莫奈、米勒等人畫作的復制品。翁格格不屑于此,在她看來,原創才是藝術的正途。而對大師的學習,臨摹固然需要,但對大師精神的學習和掌握則是第一位的和最終目的。因此,她力勸老魯到梵高的家鄉去游覽,感受藝術大師那些畫作的現實氛圍,從而為原創獲得靈感。她到荷蘭,帶上《文森特·梵高傳》,平時對梵高總是全稱“文森特·梵高”,決不會像有些人一提梵高,就是“倒霉蛋”“那個割自己耳朵的精神病人”。她對老魯他們畫室的缺點看得非常清楚,一針見血地對老魯說:
“但是畫室一直在畫文森特·梵高的作品,而且是一種低質量的臨摹。卻讓我有點、十分、特別的失望。梵高不是那么好畫的。梵高一生都沉溺在對藝術的追求中,他有著巨大的、無法平息的、怪異的激情,有著獨一無二的執著,非常人能夠理解的固執。‘我是個狂人!’這是梵高向世界發布的決不妥協的宣誓,他的內心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有一團持久噴薄、熊熊燃燒、無法熄滅的火焰。不論是在津德爾特的河灘上捉夜蟲、搜集畫冊、傳播思想,還是挑燈夜讀,孜孜不倦地沉湎于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等大師的世界中,都讓人倍生崇敬。而且,他不僅是畫畫,他任何事情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所以說,不了解梵高,不走進梵高的內心,不了解他所處的世界和當時的環境,畫出來的梵高,連皮毛都不是,就算是高級的模仿,很像,太像,十分像,也不過是像而已,缺少畫意,缺少生命,缺少歷史的沉淀,也沒有傳承,充其量不過是一幅復制品,一幅紀念品,僅此而已。”
翁格格說出了藝術的本質,藝術工作者的努力方向。這番話其實是對老魯等人的當頭棒喝,可惜老魯開始只是有點觸動,在內心里還是不以為然,仍然以市場第一、金錢第一對待梵高等人的畫作,直到碰得頭破血流,成了孤家寡人,畫廊無法繼續辦下去,他才醒悟自己離初心太遠,“原創”二字已經久違。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居然成了比她大20 多歲的人的精神導師,尤其是在需要長時間學習、歷練的藝術領域,可能有人覺得這不真實。但我覺得是合理的,非常符合當今的“后喻文化”精神。“后喻文化”亦稱“青年文化”,指由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他們在世的前輩的過程。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1970 年出版的《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的研究》一書中提出了這種觀點。她認為,在現代通訊、交通和技術革命迅猛發展的情景下,長輩只有虛心向小輩學習,利用他們廣博而新穎的知識,才能建立一個有生命力的未來。米德認為“后喻文化”將成為當代世界獨特的文化傳遞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武的《自畫像》提供了一份“后喻文化”的生動范本。老魯作為翁格格的前輩,只有接受后輩小青年翁格格的思想,才有前途。
三、生活化的敘事
中國當代文學一度不太注意生活化的敘事,但從新寫實開始,日常生活場景的描繪,已被許多作家重視并沿襲到今天,成了小說的常態。詹姆斯·伍德曾談及“生活性”的敘事形態:“當然,細節不僅僅是生活的片段:它們代表了那種神奇的融合,也就是最大數量的文學技巧(作家在挑選細節和想象性創造方面的天賦)產生出最大數量的非文學或真實生活的擬像,在這個過程中,技巧自然就被轉換成(虛構的,也就是說全新的)生活。細節雖不是栩栩如生,卻是不可降解的:它就是事件本身,我稱其為生活性本身。”
細節是藝術的生命,我們讀過《儒林外史》,可能忘記小說中的許多內容,但我們不會忘記胡屠戶從稱范進是“現世寶窮鬼”“沒用的人”“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到“賢婿老爺”“天上的星宿”“文曲星下凡”這些細節。吳敬梓通過這些細節把一個前倨后恭,嫌貧愛富、卑微勢利的市井小人物形象刻畫得活靈活現;我們讀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我們不會忘記小瑪德蘭點心。陳武的《自畫像》的細節不乏生活化,比如開頭老魯站在煎餅攤前劃著手機等煎餅:“煎餅攤上的面粉香、雞蛋香、醬香、火腿香腸和錯碎的芫荽、韭菜香,次第觸動著他的嗅覺和味覺神經。”
這是當今許多城市街頭的富有煙火氣的一幕,如此逼真,我們讀后自然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