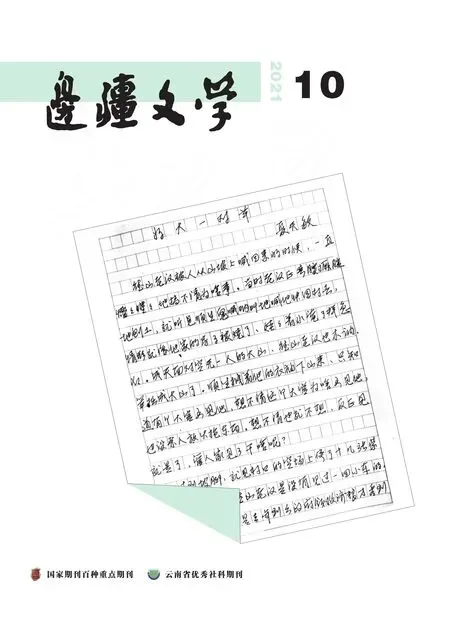九寨之子
羌人六(羌族)
1
二o一七年陽歷十一月九日,中午時分,來不及吃母親盛在桌上的晌午飯,我匆匆收拾好出門的生活用品,帶著由衷的敬意以及一種很久都不曾有過的忐忑不安的心情,獨自驅車從“天下大熊貓第一縣”——平武縣——平通鎮(我的出生地),于車罕人稀的二o五省道上歷時四個鐘頭的長途跋涉和“穿越”,在古老、漫無邊際的暮色尚未拉開序幕,群星閃耀的夜晚還沒有誕生,為這注定要凝結在呼吸、心跳和記憶中的一天畫上句號之前,平安順利地趕攏平武的“鄰居”,美麗的九寨溝縣縣城。跟過去“出遠門”不一樣的是,這次,我到九寨溝既不是為了旅游觀光,也不是為了參加朋友間的文學聚會,這次來九寨溝,是為一個人,當然,也可以說是為了見證或者重現一個英雄的生平與光榮事跡。
準確地說,我是為造訪九寨溝黑河鄉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家人而來。
來之前,我從跟九寨溝縣文明辦何曉蓉副主任簡短的電話聯系中大概得知,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生,年紀輕輕的九寨溝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村民黃孫濤,在二o一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午時分,為營救同村落水伙伴,第一時間挺身而出,用盡全身力氣將溺水者推上河岸,自己卻體力透支,最終被洶涌的河水吞噬,英勇犧牲了。《百年孤獨》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有個讀來讓人心碎不已的短篇小說——《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與之類似,當九寨溝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光榮事跡與其已經不幸罹難的噩耗鉆入耳膜之時,我的心不由得一陣顫栗和痛苦,整個人陡然墜入疼痛和悲傷交織的冰窖一般,久久不能復歸平靜。我需要面對的不只是一個“溺水者”,還有自己百感交集的內心。
或許正是基于英雄青年黃孫濤的這樣一種遭遇,我的心情才會變得如此復雜、忐忑、沉重;同時,也是因為這樣一種機緣——巴金文學院的副院長干海冰先生囑托身為巴金文學院簽約作家之一的我赴九寨溝采訪,寫一篇關于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文字——紀念這位舍己救人的九寨赤子的生平。因此,我才匆匆跨別家門,踏上了對一位青年英雄的尋訪之路,一個人驅車風塵仆仆來到九寨溝,來到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家鄉。
人總是抵達等待他的地方。
途中有過無數種的猜測和“退堂鼓”的敲響,畢竟,要采訪的對象是黃孫濤的家人,是在血液里和精神上都和他有著最最親密關系的親人們。我的心頭沒底。我生怕自己的言辭像導火索一樣再次點燃黃孫濤家人們尚未愈合的“傷口”。我也知道:一個生命的突然隕落,對于一個圓滿的家庭而言意味著什么。然而,最終,我還是來了。想走的路,一定會到。
黃孫濤的英雄事跡所折射出來的光環與樸素精神,讓我為之深深動容,也叫我深深為之遺憾。同時,我迫切地想要深入了解這個美好燦爛的青春年華就像春天的花朵一般剛剛盛開的九寨青年的生平點滴,也極其渴望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來親自見證一個有著美好靈魂的年輕人的所作所為,并把它們化作文字,以示哀悼和深切的紀念。一個人永遠地走了,泥土就成了他的歸宿,莊嚴大地就成了他溫暖的床和被子,年紀輕輕的黃孫濤人雖然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他摯愛的親朋,離開了這個平凡而又美麗的世界,但我相信,也毫無疑問的是,在他的死亡后面,他的樂于助人,英勇事跡,他的臨危不懼和第一時間挺身而出舍己為人的寶貴精神,必然會,也理所應當的鮮活地鐫刻在漫長的歲月之中,和更多人的腦海,永遠不被遺忘。而這些,也是我此次前來九寨尋訪的初衷——挖掘和記錄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生前的細節點滴——用文字記住這位優秀的年輕人,記住他的善良和英勇無畏。
時值初冬,微微的寒意,在九寨溝——中國第一個以保護自然風景為主要目的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在地——寧靜而又美麗的皮膚上奔跑著、游蕩著。九寨的時間仿佛慢了一個節拍,雖然已經立冬了,遠離喧囂的九寨,卻依然保持著她應有的安靜美麗豐盈。車來人往的九寨縣城朝氣蓬勃,周圍,一切的美,仍在默默無聞地繼續著,就像道路的延伸,就像河流的哺育,就像歲月的生長。已經到來的季節不過是一個生疏,或者,還有些遙遠的概念。毫無疑問,九寨溝的美是純粹的,仿佛經過造物主的精心打磨,而這種美,素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單調的。崇山峻嶺間那些繽紛的彼此混淆的紅葉、黃葉,似乎已經說明這一點。對漫山遍野的草木而言,似乎,腳丫子還沒有學會四處撒野的冬天,僅僅是一種幻覺,它們靜靜吮吸著空氣和人們激動而又歆羨的目光,在歲月的柵欄中,在被外界譽為“童話世界”恍如仙境般的九寨,披著一身絢爛多彩的秋裝,肆無忌憚地活著美著,延續著生命的傳奇。從九寨的縣城之內到縣城之外,從河水奔騰的山腳到雄鷹展翅的巍峨山巔,根扎于此的草木,齊心協力裝飾著九寨這塊土地的輪廓,美輪美奐,把它們望得久了,眼就明了,心就靜了,煩惱就輕了,就會感覺自己也成了它們的一部分,恨不能腳板下也生出一些根來,與這片土地,長相廝守。
這一回的九寨行,是我跟九寨溝的第三次“見面”,去年是頭一回,這也是我們今年的第二次“邂逅”。夏天的時候,我與平武作家阿貝爾、江油詩人劉強,各自帶著另一半,一路同行到這兒避暑,參觀了正在打造的“九寨云頂”以及九寨溝過去的一些老寨子,品嘗了美味可口的水果車厘子,跟九寨溝本土的詩人作家們暢聊文學。笑語歡聲,恍如昨日。
這次來九寨溝,我沒帶家眷,也無親友陪同。
這次,我一個人來。
這次,我也只為一個人而來。雖然,明明知道已經見不到他了。
在九寨溝縣城縣委縣政府的門前廣場上,我告訴自己,這就是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家鄉了。黃孫濤小兄弟,我來九寨看你了,我的心在輕聲呢喃著。
來之前,從跟九寨溝縣文明辦何曉蓉副主任的電話聯系中我已經了解到,黃孫濤的出生地不在九寨縣城,而是在九寨溝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一個名字并不十分陌生的地方。九寨溝原文聯主席、作家白林先生告訴我,夏天摘車厘子的地方就在黑河鄉的下游,離得不遠。
因為天色漸晚,我取消了前往黑河鄉的打算,在縣城的賓館里住了一夜。夜里,九寨很冷,但我心頭始終熱乎乎的。
2
十日清晨,我和早早起床的九寨作家白林先生一起吃過早飯,便離弦之箭一般朝著目的地,朝著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出生地——九寨溝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趕去。九寨溝縣委宣傳部劉志鵬部長熱心細致周到,提前給黑河鄉干部打了電話,為我們安排了帶我們去黃孫濤家采訪的工作人員。
開車順著蜿蜒、逼仄的峽谷一路前行,不時會看見一些挖掘機明顯清理過的塌方路面,和散落在路邊的巨石,白林先生告訴我,那是前段時間地震造成的。天空像水洗過一般湛藍著,金黃色的太陽也探出了腦袋,金色的光輝灑落在巍峨的山崗上,大地一片金黃,我一邊開車一邊不由自主暗暗祈禱,希望見到黃孫濤家人的時候,他們現在的心情,他們當下的生活,也當如此般晴朗、明媚才是!
上午九點,我們抵達黃孫濤的出生地,四面群山環繞的九寨溝黑河鄉。佇立在路邊上的幾棵參天大樹與清寂的街道、低矮的屋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迎接我們的黑河鄉紀委書記陳興娟,和據說是黃孫濤親戚的獸防員王志利早已等候多時。將車停靠在院墻刷著紅色標語的鄉政府干凈整潔的大院里,我們一邊寒暄,一邊大步流星朝頭道城村黃孫濤的家中走去。
帶領我們到黃孫濤家采訪的鄉紀委書記陳興娟,跟我介紹起黑河鄉的基本情況,讓我對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家鄉有了一定了解:地處閉塞山區,距縣城約四十多公里,交通不便,經濟落后,人均收入偏低的黑河鄉位于九寨溝縣城東南部,正南接陵江鄉吊壩村和羌活溝林場,西與玉瓦鄉八郎溝村和大錄鄉大錄村的扎子浪接壤,北與甘肅省舟曲縣毗鄰,海拔將近兩千米。許多人祖祖輩輩都扎根生活在這片土地,靠耕耘土地,種藥材、水果等掙錢養家糊口。“退耕還林”以后,黑河鄉的大多數老百姓原來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今,本地人多是選擇出門打工謀生路了。
同樣有著類似農村生活體驗的我幾乎可以確信,為了搭救落水同伴自己卻英勇犧牲的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應該就是在這樣一種物質生活較為窘迫的環境和背景下出生和長大的。與黃孫濤素未謀面,但他那舍己為人、無所畏懼的精神,著實令我感動、感慨,甚至可以說是震撼!
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在黯淡而又孤寂的童年歲月,黃孫濤的心卻并沒有因為貧困而變得冷漠、自私、無情,他的心猶如閃閃發光的金子一般,始終都在照亮和溫暖著他生命周圍的人們。
3
在九寨溝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黃孫濤家中,黃孫濤的父母親用淳樸的笑臉和友好熱情的待客方式接待了我們,端茶、倒水,果盤里還精心準備了許多吃食,水果、炒花生、葵花,忙前忙后。
如來之前所料,黃孫濤生在黑河鄉頭道城村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一九七o年十二月生的黃孫濤父親黃東平今年四十六歲了,平時主要在家務農,用他的話說,就是什么碎活都做,同時,他也是頭道城村的新農村建設管理員、清潔員;黃孫濤的母親袁菊蓉今年四十二歲,老家是北川片口人,片口毗鄰阿壩州茂縣,袁菊蓉是地地道道的羌族人,平時在黑河鄉政府食堂負責做飯,掙點收入,維持家庭開支。除了大兒子黃孫濤,黃東平和袁菊蓉還有兩個正在學校念書的女兒,老三黃嚴在樂山一所大學學會計專業,老二黃梅在南坪念初中。家頭除了這四個人,黃孫濤年邁的婆婆爺爺也跟他們住在一起。本該幸福快樂、笑語歡聲的一家人,因為黃孫濤的不幸罹難,抹上了一道沉重的陰影,出現了一個永遠都無法彌補的裂縫。
采訪之初,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和他的母親袁菊蓉眼睛紅紅的,這讓坐在沙發上的我對自己的到來深感愧疚、不安。他們的兒子黃孫濤因救人而英勇犧牲的事情雖然過去兩年多了,但我依然能夠從他們的皺紋和表情中讀出他們內心強烈的悲痛,和籠罩的陰影。我擔心的自己的言談會不經意地傷害到黃孫濤父母。多虧了黑河鄉紀委書記陳興娟的牽線搭橋,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這個隱忍而又樸實無華的父親,漸漸放松下來,向我們打開了話匣子,講述起大兒子黃孫濤生前的點點滴滴。后來,黃孫濤母親袁菊蓉不時插話進來,加以補充。
在九寨溝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黃孫濤家中,我跟黃孫濤父母隨意地拉著家常,之前存在的顧慮也漸漸消失了。我們的談話也越來越輕松自然。
黃孫濤母親袁菊蓉拿出手機,向我展示黃孫濤生前讀書時的照片,哪一張是讀小學的,哪一張是讀初中的,她都記得清清楚楚。她的手機里,還保留著大兒子黃孫濤的身份證照片,上面資料顯示:黃孫濤,男,羌族,生于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住址四川省九寨溝縣黑河鄉頭道城村015 號。照片上的黃孫濤留的是平頭,白皙標致的面龐略帶微笑,整個模樣,看上去還有些稚嫩。袁菊蓉在跟我看黃孫濤的這些照片的時候,眼眶里滾動著淚水,不過,她很快又想起來什么似的,幸福的微笑在臉上蕩漾開來,她忽然指著身份證上的黃孫濤跟我說道:“好多人都懷疑他是涂了口紅照的身份證,其實不是的,他從小嘴巴就紅。”
“就是,就是!”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也在一旁證明似地說道。
在來頭道城村的路上,獸防員王志利在我面前如此評價黃孫濤:“很少有娃娃像黃孫濤那么又懂事又心好的!”
樸素的贊美勝過萬語千言!在零零星星聽過黃孫濤家人對黃孫濤一些講述,一個勤勞踏實、積極進取、助人為樂的農村青年形象,一個普普通通而又“鳳毛麟角”的大寫的黃孫濤,漸漸清晰地在我的心頭浮現,緩緩向我走來。
我對這位見義勇為的青年英雄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黃孫濤在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這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出生了,給這個貧苦的家庭帶來了許多歡樂。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告訴我,大兒子黃孫濤自小就很懂事,從來不給家里添麻煩,每次放學回家,黃孫濤不是幫著他們照顧兩個妹妹,就是照顧婆婆爺爺,或者是幫家里生火做飯。念初中二年級的時候,黃孫濤考慮到自己的家庭情況,也為了兩個妹妹能夠繼續念書,他便狠了心主動決定輟學,他的理由很簡單,他覺得自己已經十六歲,長大成人了,為家庭分憂解難理所當然,更何況,自己還有兩個年幼的妹妹,作為哥哥,他希望妹妹們將來有更大的出息和更好的出路。就這樣,黃孫濤輟學了。任由父母好說歹說他都再也不肯上學讀書,而是回到家里,每天跟著父母起早貪黑地勞動,為自己的家庭默默無聞而也無怨無悔地奉獻著自己的那份光熱。
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是河道城村的清潔員,每天都要將全村的垃圾運到指定地點處理掉,黃孫濤作為黑河鄉企業警務室協警的第二年,由于父親生病皮膚過敏,黃孫濤便主動替父親做這些事。
黃孫濤不但懂事、勤快,還異常的節儉,從來不會亂花一分錢。在黃孫濤母親袁菊蓉的記憶中,有件事一直讓她念念不忘,或者說是“耿耿于懷”也可以。她告訴我,黃孫濤在鄉上企業警務室干上協警工作以來,每次從單位里領了工資,總是第一時間全額交到她手頭,黃孫濤自己呢,一雙好的鞋子也舍不得買。有一回,她看兒子的運動鞋壞了,給他拿了五百塊錢讓他去縣城買雙皮鞋穿,品牌店里那些鞋子后面的阿拉伯數字讓他掉頭就走,黃孫濤舍不得花錢也不想亂花錢,在縣城逛了一圈,花了四十塊錢買了兩雙布鞋,把其余的錢分給正在學校讀書的兩個妹妹手頭,就回家了。說起懂事的兒子,袁菊蓉滿臉愧疚。
黃孫濤不但為自己家里的事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也是黑河鄉頭道城村有口皆碑的“熱心腸”和“閑不住”,村里人但凡有能幫得上忙的事情,黃孫濤總是第一時間前去幫忙,有時候主人家還沒來得及說句感謝話,他早就跑得遠遠的了。
黃孫濤為村里人幫的忙,村里很多老百姓現在都還歷歷在目,無不交口稱贊。二o一四年,頭道城村“幸福美麗家園”建設中,但凡哪家缺沙少石的,哪家需要用他家拖拉機的,只要請黃孫濤幫個忙,他總是熱心地開著家里的拖拉機免費為大家服務。
在黃孫濤家的屋子里坐了一會兒,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帶領我們參觀他們家新修的房子。順著院子里的樓梯上樓的時候,他一邊遞煙一邊有些靦腆地告訴我,這個房子原本打算是蓋好了將來好為兒子娶媳婦住的。在農村,房子就是一家人的臉,是一家人的面子,也是單身青年娶親的“招牌”,房子差了,媳婦不好娶。
三層高的磚木結構房子看上去既氣派又漂亮,墻壁刷得白白的,一塵不染,墻角還貼了瓷磚,站在二樓的院壩里,幾乎可以把整個黑河鄉一覽無余。黃東平既感傷又自豪地告訴我們,這房子凝結著他和兒子的心血。修房子的時候,他們為了省掉工錢,沒有請人,而是父子齊上陣,整個房子是他們自己一磚一瓦壘起來的。每天下班回家,不忍心讓父親做重活的黃孫濤再晚都會把運沙石、搬水泥這樣的重活干完才肯休息,有時候甚至要忙到深夜。黃東平說,當時已經在黑河鄉企業警務室當協警的兒子黃孫濤總是“要求”他:“爸爸,以后像搬運沙石、水泥、鋼筋這些重活,你就留給我下班或者星期天來做。”
在參觀黃孫濤家房子的時候,我注意到,三樓上還有些地方似乎沒有完工,顯得有些凌亂。樸實憨厚、略顯憔悴的黃東平大概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實打實地告訴我,自從前年七月份黃孫濤救人出了事,自己經常性失眠,這兩年也沒精力弄房子,等以后慢慢弄。
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安慰這樣一位面容已經顯出幾分蒼老的父親。遠處,金色的陽光涂抹著群山,潺潺流淌的黑河水仿佛在訴說著什么。
4
二o一五年七月十七日,對黃孫濤的一大家人而言,是記憶里最為黑暗的日子,撕心裂肺、刻骨銘心的日子,也注定是讓他們永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家庭成員黃孫濤的遭遇,就像一座大山突然崩塌下來了似的,沉重地壓在這個家庭,壓在每個人的肩膀,在他們的記憶中留下了永久的傷疤。時至今日,黃孫濤的父母親似乎都不敢相信他們的兒子,為了搭救同村的落水同伴王明彪,而永遠地離開了他們,也離開了這個美好生活才剛剛開始的大家庭。
在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漂漂亮亮的家中,黃孫濤父親黃東平克制著內心的悲痛,向我們講述起那個噩夢般的日子——二o一五年七月十七日所發生的一切,也為我翻開了黃孫濤——這個九寨黑河鄉出生和長大的農村青年——生命冊頁里最為亮眼也最令人感到心痛的一章!正是這沉重的一章,無情抹去了黃孫濤生活和生命里可能出現的種種可能性,給對他無不充滿感激之情的鄉親和盼望他回家的親人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當然,也讓他成為了一個可歌可泣的見義勇為英雄,而今,他的光榮事跡,在黑河鄉,在九寨溝,在阿壩州,甚至更遠的地方廣為流傳著……
二o一五年七月十七日,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九寨溝黑河鄉的天空蔚藍,萬里無云,蔥翠的大地因為前幾日暴雨的洗禮,爆發出更為蓬勃的生機。黑河里的滔滔洪水翻卷著,咆哮聲在這幽僻的峽谷中回蕩。
午后,在家里吃過午飯的黃孫濤與村里的王明彪、何清磊、馮宇、王海濤、馮強、蔣磊等十一人邀約著結伴騎摩托車到黑河鄉水口壩村大元壩沙場河邊網魚。雨過天晴,驟雨初歇,雖然洪水兇猛,但挖沙河段的水勢卻相對平靜,渾濁的河水像凝固的金湯懸浮在寬敞的河床之上,一艘采沙船靜靜停泊在河水中央。一般來說,這樣的地方魚比較多。黃孫濤和伙伴們興高采烈,仿佛活蹦亂跳的魚兒,已經近在眼前,觸手可及。
就在這時,意外發生了。黃孫濤的同村伙伴王明彪在網魚過程中因為沒有帶裝魚器具,便準備轉身回岸邊拿,然而,沒有想到的是,他忽然腳下一滑,渾身上下就像被抽空了骨頭似的,一下子失去了重心,瞬間落入了渾濁的洪水之中。事發地為沙場采沙沒有回填的沙坑,深不見底,恐慌之中,王明彪開始本能地掙扎和大聲呼救:“救命啊……”
同行的幾乎都是些未成年人,看見同伴落水,都驚呆了,石頭一樣傻傻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此時此刻,正在不遠處沙堆上弄漁網的黃孫濤聽到王明彪的呼救聲,這才發現有人落水了。他立刻扔下手中的漁網,飛快地沖著已經溺水的王明彪跑去,來不及多想,黃孫濤便“噗通”一聲跳入渾濁的黑水河中,奮力游向溺水者王明彪。一只手好不容易抓住洪水中浮浮沉沉的王明彪之后,黃孫濤調整方向,將被嚇得失魂落魄的王明彪用力向岸邊推去。
終于,王明彪被推向岸邊,伙伴們七手八腳把他拉上岸。而奮不顧身營救落水少年的黃孫濤,因為在施救過程中體力透支,慢慢沉入渾濁的洪水之中,沒能浮出水面。
黃孫濤不見了!
“濤哥!濤哥!濤哥……”
少年們望著平靜的河面,驚慌失措的哭叫聲響徹峽谷。待他們緩過神來,個別帶了手機的孩子趕緊掏出電話跟家長親人呼救。打過電話,少年們又一陣風似地跑向旁邊的沙場,向正在上班的工人們請求援助。工人望著早已復歸平靜的水域,搖搖頭,一切都晚了。
就這樣,一個年輕的生命,消失在了黑水河渾濁的洪水之中……
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含著眼淚告訴我,聽說兒子救上同伴,自己卻沉到洪水里去了的那一刻,腦袋里分明有一顆驚雷炸響!當他心急火燎趕到出事地點,見到一群哭哭啼啼的孩子,唯獨沒有自己兒子黃孫濤的身影,這個隱忍而又堅強的父親,再也沒有忍住自己的眼淚……
頭道城村的鄉親父老們也聞訊趕來,亟待奇跡出現的大家一面報警的報警,一面紛紛順著水勢滔滔的黑河開始了緊張而又艱難的搜救工作。
從二o一五年七月十七日下午出事的時候開始,黑河鄉頭道城村的鄉親父老們迅速組織起了一支四五百人的龐大搜救隊伍,他們在水口壩村大元壩沙場的黑河下游段連續搜尋了大半夜,然后又是整整兩天,卻仍然不見黃孫濤的蹤影。
面對洶涌無情的黑河水,面對著不顧個人安危奮力搜救的鄉親父老,黃孫濤的父母心里完全絕望了。“兒子,你是不是怕爸爸媽媽傷心,才不肯露面見我們啊?”當時,黃孫濤的母親袁菊蓉這么想著。
黃孫濤為了營救落水少年王明彪自己卻消失在滔滔洪水中的英勇之舉,像春風一樣灌溉著鄉親父老們柔軟的心扉,他們一面含著熱淚,一面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表達著內心難以言表的感動,和對英雄的崇高敬意!全力以赴尋找黃孫濤,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對黃孫濤家屬最好的安撫。
持續的搜救雖然毫無結果,令黃東平夫婦感動不已的是,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在他們面前勸說他們,要他們放棄搜救。兩天時間過去了,依然不見黃孫濤的蹤影。這天下午傍晚時分,黃東平做了一個最為艱難的決定,他跟大家宣布:“謝謝大家了,人就不找了,說不定是他自己不想回來了……”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母子連心”這樣的說法或許根本站不住腳,但事實證明,“奇跡”真的出現了!就在這天夜里,傷心欲絕的黃孫濤母親袁菊蓉迷迷糊糊做了一個夢,她夢見兒子黃孫濤站在水里跟自己招手,嘴上還一個勁兒地喊著“媽媽、媽媽……”
睡夢中,袁菊蓉忍不住“濤娃、濤娃”地喊了起來。醒來后,袁菊蓉回憶著夢里的事情,告訴丈夫黃東平:“我看見濤娃了,他就在他們網魚那個河段,并沒有被洪水沖跑!”
第二天,人們果然在網魚的河段發現了黃孫濤。如此年輕的生命,卻早已停止了心跳,閉上了眼睛。人們在網魚河段找到黃孫濤的時候,這位見義勇為的青年英雄身上,救人時還沒有來得及脫下的衣服仍然完好無損地穿在身上。
“劉老師,你一定要在你的文章里好好表揚(贊美)一下我們頭道城村的村民,還有我們黑河鄉和縣上的領導干部,濤娃的事,我一輩子都要感謝他們呢!”
在我們一行人走出黃東平家的院子,準備前去水口壩村大元壩沙場河邊,轉轉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出事地點的時候,黃孫濤父親黃東平有些靦腆地懇請我務必要幫這個忙。我答應了這個憔悴而又淳樸的父親,我知道,他所謂的“表揚”,其實就是贊美的意思。其實,我也明白,熱心的救援隊伍后面,乃至黃孫濤父親深切的感激后面,更應該值得贊美和褒獎的,其實是黃孫濤那顆金子般的心,和善良的靈魂!
5
臨近中午,陽光普照的巍巍群山仿佛青銅鑄就的一般,蒼茫、悠然、曠遠。
我,九寨溝作家白林,黑河鄉紀委書記陳興娟,王志利還有黃孫濤的父親黃東平一行,乘坐鄉上的公務用車來到黑河鄉下游方向的水口壩村大元壩沙場。進入沙場,銹跡斑斑的碎石機木然闖入視線,堆成小山似的碎石在沙場也隨處可見,只是不見機器轟鳴,空蕩蕩的,沒個人影。黑河水潺潺流淌的聲音如泣如訴。
黃東平下車后,便向我指了指一座碎石堆,輕聲告訴我:“就在那后面。”
初冬的河谷靜謐而又荒寂,極目遠眺,不見鳥影,也不見人,只有黃色的樹葉不時在凜冽的風里翻飛,仿佛在追尋故鄉或是遠方。
我們踩著凹凹鼓鼓的鵝卵石慢慢朝河邊走去。我們走得很慢,生怕踩疼了或者驚擾了什么似的,每一步都很艱難,每一步都混雜著自己對一個青年英雄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惋惜!“多年輕美好的一個生命啊,就這樣沒了!”采訪過程中,我雖然極力表現得平靜自然,但我壓根就控制不了內心感情的波濤,只能任由它們洶涌澎湃,為黃孫濤,為他金子般的心,為他善良樸素的靈魂,也為他的英勇犧牲。
去河邊的路上,已經沒有隔閡的黃東平一邊吸著煙,在我面前自顧自說起了對兒子黃孫濤的愧疚。他說,他這輩子只打過黃孫濤一次,那是黃孫濤在學校里念書的時候,因為幫同學買藥,回學校遲到了。老師將黃孫濤上學遲到的事情告訴了黃東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孩子不好好念書成不了才的黃東平火冒三丈地來到學校,從來還沒有用拳頭教育過孩子的他不問青紅皂白,狠狠扇了黃孫濤幾個耳光。后來才搞清楚兒子是為了幫人買藥做好事才遲到的,黃東平后悔了好一陣子。
事情已經過去好多年了,“愧疚”仍然活在黃東平的心頭,黃孫濤為救人英勇犧牲之后,他常常想起這件事。
“我冤枉他了。那天不該打他。”頭發灰白的黃東平嘆著氣說道。
清澈見底的黑水河依然在流淌。
站在河邊高高的碎石堆上,指著黃孫濤當天的救人現場,黃東平眼淚汪汪地再次向我還原起了事情經過。他說,當時黃孫濤就坐在這邊的碎石堆上弄漁網,聽到王明彪高聲呼救,他第一時間沖了過去,衣服都來不及脫掉,直接跳進水中去了。王明彪獲救了,黃孫濤的身影卻消失在了洪水之中。三天后,差點放棄搜救的他們終于在幾十米遠外河中心位置找到了黃孫濤。
我放眼望去,看到了那片淺灘,光滑而黝黑的鵝卵石密集地佇立在水中,露出半個身子。緊緊的黑河流水繞過它們,繼續往前流著。
“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們要振作起來,好好過日子,過好日子。”
我安慰仍然眼淚汪汪的黃東平。
“有時候晚上想起他,一晚上都睡不著覺,經常失眠……”
黃東平望著潺潺流淌的河水自言自語,似乎沒有聽見我的話。
在河邊站了一會兒,我們轉身準備離開了。
淳樸的黃東平告訴我們,他的妻子袁菊蓉已經在家里準備好了午飯,要我們吃了再走。
在回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的路上,我才知道,黃東平夫婦把兒子葬在了離家兩里地的山坡上。那上面有他們自家的土地,且植被茂密,視野開闊。
河水帶走了黃孫濤的生命,卻沒有沖走黃東平夫婦一大家人對他的思念之情。
“想他了,我們經常去地里轉。”黃東平說。
危難時刻,九寨溝黑河鄉年僅十九歲的黃孫濤挺身而出,縱身一躍,換來了同伴生的希望,他用自己的行動,用自己寶貴的生命點燃了他人的生命,闡釋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和舍己為人的精神。
如今,兩年時間過去了,九寨溝黑河鄉頭道城村四組見義勇為青年黃孫濤的英雄事跡依然在黑河鄉,在美麗的九寨,甚至更遼闊的土地上被人傳頌和謳歌,也深深感動著知道他的每一個人,每一寸時光。
九寨赤子黃孫濤人是不在了,可我又分明感到,此時此刻,他就在我的生命周圍,在我們的生命周圍,他那顆金子般的心,善良樸素的靈魂,仍在感動我們,感動更多的炎黃子孫。
“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們要振作起來,好好過日子,過好日子。”
分別之際,我在因見義勇為而不幸罹難的黃孫濤父母黃東平夫婦面前,重復起我在河邊上跟黃東平說過的話。這也是那一刻我唯一想要表達的祝福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