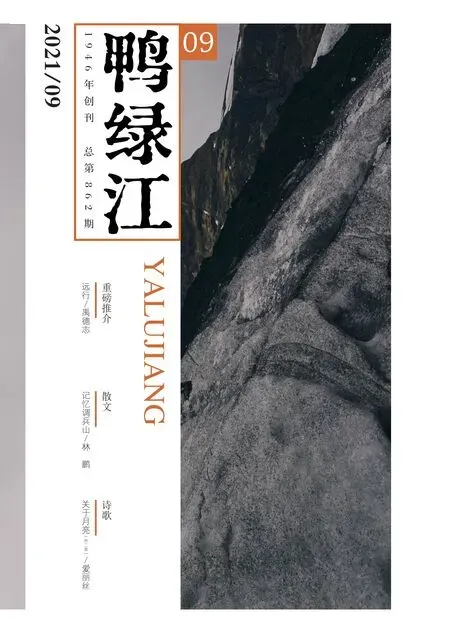我的父親
周堅飚
父親離開的時候,我還在家里靜候他的消息。我沒能去醫院送他最后一程,因為母親的阻攔。母親是個迷信的人,我屬相狗,與父親的龍相沖,小時候我要叫父親為叔叔,一直到父親走了,我也沒能叫他一聲爸。
那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不見了,我忍不住號啕大哭。
父親第一次中風,是在一個初秋的傍晚,他在廚房搬運洗手池,突然一個趔趄摔倒在地。我們趕緊把他扶起來,學醫的二姐一看父親笑起來,嘴角歪了,知道父親是中風了,及時送醫。之后,父親病情逐漸有了好轉,但他的舌頭癱了一半,說話含糊笨拙。在他住院的兩個多月里,我剛巧在銀行上一休一,與同事調了半個月的班,在醫院一直陪護著他。那是我的人生中陪伴他時間最長的一段日子。
十年后,父親第二次中風住院,我看著一直昏迷不醒的父親,頭發花白,蒼老了許多,近乎陌生。我開始在腦海中極力搜索那個父親,那個五官清秀、中年時即使長出幾根白發也會叫我去拔掉、很注重個人形象的父親,再也找不到了。我內心充滿了愧疚。那些年,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無序的生活狀態里,很少關注他的健康。
父親十六歲跟隨爺爺從農村出來。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十八歲參了軍。正值青春年華的他,風華正茂,在部隊結識了一位女兵。后來聽父親說,那是一位首長的女兒,江蘇人。如果不是爺爺反對,可能父親退伍后就留在江蘇了。
是爺爺極力撮合父母的婚事。母親是個吃苦耐勞的女人,與爺爺同村。母親三歲時候沒了外公,六歲時外婆也走了。聽母親說,外婆臨終前,母親就睡在她的腳邊,早晨外婆叫了她幾聲:“囡哎,起來,起來……”就再也沒有聲音了。從此母親跟隨哥嫂生活,受盡了白眼,小學沒畢業,他們不再供她念書,母親就輟學了。母親就一個人,每天走山路去遠在十幾公里外的大隊公社食堂幫工,養活自己。母親從小就養成了十分好強的性格。
父親忠厚老實,不敢違背爺爺的意愿,假期被爺爺騙回老家匆忙與母親成了婚。現在我能體會到,當時的父親內心肯定充滿了極度的不滿和不安。不滿的是,父親無力拗過爺爺定下的婚約;不安的是,父親該如何面對他在軍營結識的初戀?幾十年后,也就是在父親第二次中風后,曾經托付以前的戰友打探到她的消息,有一天在我們子女的鼓勵下,父親終于鼓起勇氣撥通了她的電話,但電話那頭只平淡地說了一句:“我不記得了,真對不起。”電話這頭的父親,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般,憋紅了臉,手足無措。大家沉默下來,我知道,那一直隱藏在父親內心最深處的一份美好記憶,在這一瞬間完全破碎了。
母親并不介意這件事。因為在她內心,有比這些可能莫須有的感情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不停地賺錢,給自己老來的生活、給家庭一份更堅實的保障。貧困的經歷對母親刺激極大,她深知小時候寄人籬下的痛苦,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雙手去創造。母親一直任勞任怨不怕吃苦,在單位退休前干的是跟男同志一樣的重活兒——鋸木工,她能將一根百來斤重的木頭輕松搬到鋸木臺上。退休后,即使我們子女每月給了她生活費,她依舊不肯停歇,不辭辛苦地搬過水泥、去菜場擺攤。
父親中風后,原本不善言辭的他變得易怒暴躁,常因一點小事就氣急敗壞地責罵母親。為了讓他安心養病,我們決定全家人每天一起回家吃晚飯,陪護著他。大家相互配合,向父親傳遞一種積極的、樂觀的心態。那是屬于一家人最完整的快樂時光,我們也樂于享受父親健在時建立起來的日常家庭秩序。其樂融融的氛圍,也讓父親感覺到些許舒心。那段時間,父親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晚飯后,他常一個人呆呆地坐立窗前書桌,用手輕輕撫摸、注視著像寶貝一樣珍藏多年的肩章、帽徽、紀念章等物品,有時一坐就是一晚上。我們總是輕輕地繞開,生怕打擾了他的思緒。可能父親一直沉浸在那段讓他一輩子感到驕傲的從軍經歷,和一段不再青春往返的歲月時光吧。
但好景不長,父親再一次被病魔擊倒。這次他沒能再站起來。母親白天仍舊在菜場擺攤,晚上趕到醫院陪護。有時來得晚了,父親緊皺著眉,握著拳頭把她一把推開,責怪母親賺錢不顧他的死活。母親總是一句“不做,吃什么”來篤定自己的理念。后來父親病情不斷惡化,甚至不能說話,無法吞咽。母親終于放下生意,日夜陪護在他身邊。因為長期臥床不能運動,父親身體像泄了氣的氣球,無力地干癟下去,直到骨瘦如柴。康復的希望日漸渺茫,父親開始每天醒來睜著眼,側身在病床上,一動不動地注視著病房外的天空,始終無法開口再說一句話。然而,在父親離去前的一天,他竟奇跡般地開了口。記得那天,病房外的天空格外陰沉,見我進來,父親掙扎著想坐起來,我趕緊去扶,他氣喘吁吁地癱靠著,極力調動臉上的肌肉對我笑,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出我的名字,淚珠一直在他深陷的眼眶里打轉。病床上的父親,虛弱得像暴風雨來臨前的枯葉,渺小、無力,即將隨風飄蕩。那一刻,我真切地從他混濁的目光里感受到了一份惦記,以及另一份無助、不舍、對活著的渴望。
生命的結局終究是注定的,該來的總是會來。無法忘懷父親在生命的最后時光,默默惦念著我的名字,而我卻從此永遠地失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