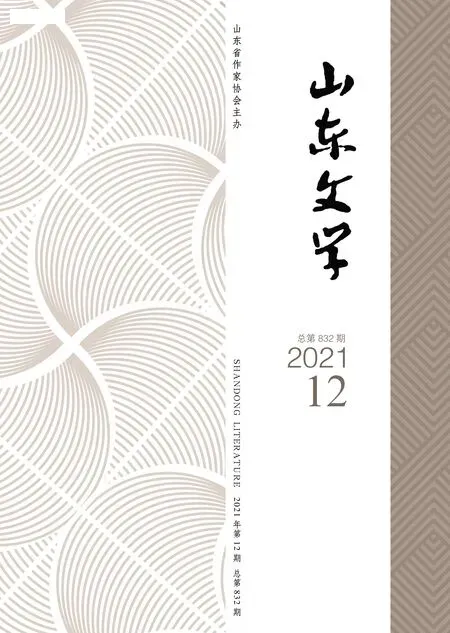四姐搬家
劉榮哲
四姐大我19歲,生于1944年。
四姐其實是我父母的長女。之所以稱為四姐,是從我父親哥哥家的女兒輩排行下來的,到我大姐,排行老四。這種大排行,在過去很普遍。
這些年,我們一大家子人相聚聊天,聊著聊著,常常就聊到四姐的搬家上來。因為每逢她搬家,大家都要去幫忙或湊熱鬧。算來算去,自她結婚到現在,大大小小的搬家,竟有十幾次之多。大家笑著說,四姐一輩子光忙著搬家了。
笑,讓生活變得輕松,大家都在創造這種輕松,享受這種輕松。許多當時很艱難的事,時過境遷,也都成了笑談。而當事情發生時,卻是萬萬笑不起來的。
有房子才是家,沒房子就不是家。沒有合心意的房子,就沒有幸福的家。若在一個地方住得滿意,誰會輕易搬家?搬家,表面上看,換的是房子,其實,換的是心情,換的是生活。
借住的新房
1968年上半年,四姐24歲,在濟南市畜產進出口公司地毯廠工作;四姐夫29歲,在濟南鐵路局濟南車輛段工作。兩人相識半年多,情投意合,也都是大齡青年了,想結婚卻沒有住房。當時,住房都靠單位分,人口不斷增長,一般單位一時無力解決。房子的緊張程度,未經歷過的人是體會不到的。許多無房的青年人結婚,只能依靠父母,與父母、弟弟妹妹,甚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滿屋是床,兩口子拉個布簾,就是私密空間了。我們家連老帶小十二口人,擠住在兩間各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不可能給四姐提供幫助;四姐夫家在青島,在濟南是單身,也沒辦法搞到房子。想想也真是可憐!就是一對小鳥,到了育齡,也要找個樹枝搭個窩的。兩個大活人卻連安身之處都沒有。
四姐夫的同事,也是他們的介紹人張方岐師傅說:結婚先到我家去住吧,我騰出一間來給你們。張師傅住濟南市經一路二十一鐵路宿舍,里外兩間,兩間一般大,通過外間進里間。張師傅一定要把里間騰給他們,他夫婦和兩男一女三個孩子住在外間。他們的孩子大的八九歲,小的三四歲。有了這間房,四姐總算可以結婚了。
四姐當時的工資是每月21.5元。我家上有需要贍養的爺爺、奶奶、姥姥,下有七個子女,只有我父親和四姐有工作有收入。四姐十六歲參加工作,工作后的工資大都貼補家里了。婚前,母親問四姐想要點什么作嫁妝,四姐說,您養我這么大,我有工作有收入,能夠自食其力了,什么也不要。母親給四姐買了兩塊人造棉包袱皮。包袱,諧音為“包福”,以此表達對女兒的祝福。這就是娘家的嫁妝了。四姐、四姐夫各買了一床被面、買了點棉花,請母親幫助做棉被。做結婚的棉被是有講究的,按習俗,母親請來了兩位兒女雙全的鄰居,一起做了兩床棉被。缺一床新被里,四姐夫就把自己用的舊床單洗洗拿來替代了。
張方歧師傅幫他們買來一張舊床板。四姐夫買了一副床頭、一張方桌、兩把椅子、兩個凳子、一個半櫥、一個鋼精鍋和簡單的炊具。暖瓶、臉盆、茶壺、茶碗、茶盤等,都是關系親密的同事送的。母親的鄰居湊錢贈送了一面大鏡子,大鏡子右下角印著一朵大牡丹,牡丹上印有“敢于斗爭”四個字。
那時,講精神遠遠大于講物質。四姐認為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是一位名叫劉安東的同事加“戰友”送的兩本印著“雄心壯志”字樣的筆記本。筆記本里,貼著劉安東用了好多夜晚細心剪刻、描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魯迅頭像,頭像下邊抄錄著精心選出的偉人語錄、名言。比如在列寧的頭像下邊,工工整整地抄著:“要革命嗎?你就應當是強者。”在毛澤東頭像旁邊,抄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要達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
四姐多年用的一個帆布箱子,四姐夫多年用的一個舊箱子也搬了去。碗筷也沒買,各帶各的。這就是他們結婚的全部家當,總共花費也就300元左右。
新人總要穿身新衣服。四姐用攢的幾個月的獎金和當月的工資,買了布,做了一件斜紋布上衣,一條有點檔次的褲子,買了一雙布鞋。
姐夫那邊的家境也非常困難。沒有能力辦婚宴,兩口子就對濟南的親友說在青島辦,對青島的親友,就說在濟南辦了。在青島,舉行了極簡的結婚儀式。四姐夫的母親早逝,在四姐夫的父親和他二哥、四弟兩家同住的房子里,新郎新娘給老人鞠躬,給大家鞠躬。一個鄰居小伙子拉著手風琴,大家合唱了一曲《東方紅》,就算是婚禮了。
四姐夫的父親買了三塊處理的浴巾,縫在一起,算做毛巾被,這就是一位父親送給兒子的結婚物品。見四姐還穿著一雙普通布鞋,不忍心,拿出10塊錢,要她去買雙皮鞋。四姐收下了錢,也沒買皮鞋,應急用了。
青島的這套房子是并排三小間。二哥一家五口住一間,四姐夫的父親和他的小女兒住一間。中間那間有十平方米,是四弟夫婦的住處兼廚房。四弟夫婦只隔出一個不足六平米的空間,擺一張床和一只柜子。四姐他們去了,四弟夫婦就另找地方住,騰給四姐兩口子暫住。
這期間,他們和張方歧師傅一家組成了一個奇怪的大家庭。張師傅讓他的孩子們稱四姐“劉姨”,稱四姐夫“高叔”。兩家共用一個燒煤球的爐子做飯。張師傅燒水時,都要給四姐他們灌滿暖瓶;買了白菜,他們吃菜幫,把菜心留給四姐兩口吃。逢張師傅倒班,白天在家,打掃衛生時把四姐的屋子也一并打掃了,連保溫瓶、桌子,都要精心擦拭。四姐要交點費用,他們不讓,反復推讓,才答應每月收3元錢。四姐兩口子在感激中度過了新婚最早的一段日子,心里甜甜的。
在那間臨時新房里,四姐和四姐夫請人拍過一張照片,兩個人靠在桌邊,胸前戴著毛主席像章,一起專注地讀《毛澤東選集》。那張照片一直貼在我家鏡框里,我經常盯著看。
那年我4歲。四姐帶我到她新房去玩。那房子一半在地下。下階梯,左拐,進到外間,里間的門在墻壁中央。印象中,外間都是床,四姐住的里間倒挺寬敞。半夜,我爬起來到院里上廁所,外屋黑乎乎的,睡了一排人頭。回來時,踢翻了一只尿盆。
四姐兩口子與張師傅一家在一個屋檐下生活了半年多。這半年,四姐四姐夫銘記一生,感激一生。張方歧,是四姐和四姐夫念叨最多的名字。52年后的2020年春節,四姐來濟南,還專程去看望張師傅的夫人。張師傅已在多年前去世了,老夫人已近90歲高齡了。
一間女更衣室和辦公大樓地下室
盡管張師傅一家與四姐兩口子親如一家,但畢竟不是長法。四姐夫反復找領導申請房子。四姐夫所在的車輛段內有個小院,院里除了一個幼兒園外,還有男女兩個更衣室。當時沒有女職工,領導就同意把女更衣室給他們暫住。不管怎么說,總算有了屬于自己的窩。借了輛三輪車,拉上所有的家當,高高興興地把家搬了。
車輛段靠近濟南站,以濟南站為終點站的旅客列車,到站后就把車輛停靠在這里,車輛段負責保養和維修。四姐住的小院,周圍是十幾條鐵路。到了晚上,工人下班,四周漆黑一片,一列列列車在黑暗中臥著,鐵軌中高高低低地亮著紅綠藍各色信號燈,空曠無人,只能聽見路過火車的行駛聲和汽笛聲。
人住進去,心卻懸起來了。
“文革”狂瀾翻卷,四姐夫也在一個“派”中,雖不是頭面人物,但因有文化,讀書看報多,能分析時勢,被敵對方稱為“黑參”。在這樣的小院中,一旦敵對的人闖入加害,逃無可逃,呼救也沒人聽到。越住越心驚膽戰,夜不成寐。四姐夫就到處尋找可安身的地方。到鐵路局機關辦事,偶然發現辦公大樓的地下室全空著。于是每天晚上,兩人就帶著鋪蓋來到地下室,隨便找個角落和衣而睡。雖然有點像盲流,但總比在小院里睡得踏實。后來兩人想想,也覺得可笑:如果有人真想整你,在那地下室又怎能躲得過?
我和兩個姐姐常去那個小院玩。那小院有幾棵大樹。有個星期天,四姐四姐夫來我父母家,見到我就說,早上樹上掉下來個知了,想帶給我玩,撿起后用茶杯扣在桌子上,走時忘了。兩個姐姐馬上騎自行車去取了來。知了拿在手上,還在喳喳地叫,讓我高興了好一陣。
住上了樓房
1970年,四姐夫分到了正式住房,在濟南二七新村二區一棟新建的凹字形樓上。二七新村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濟南鐵路局建設的規模比較大的鐵路住宅小區,多是簡易的平房,位于英雄山下英雄山路西側。當時濟南市樓房并不多,新建的幾棟簡易樓在一大片平房中如鶴立雞群,看上去挺高大上。每層四戶,沖樓梯道是個水池,兩個水龍頭,四家共用;水池兩頭一頭一個廁所,兩家合用一個。四姐夫分到的房子在三層,一間14平米的房間外加一個一米多寬的過道,在門口支爐子做飯。房間陽光充足,打開門窗,風無障礙地穿過屋子,夏天十分涼爽。
總算有了屬于自己的正規的住房,這房子又體面又寬敞,兩人高興異常。借了一輛地排車,一趟就把家搬了。
住二七新村期間,四姐生下了大女兒高鴻,二女兒高爽。其間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四姐生下大女兒高鴻,我母親去伺候月子。每天,母親從我們家住的堤口鐵路宿舍乘7路公交車,坐七八站后到大觀園站,再倒4路車,坐六七站后在二七新村站下車,再步行一里多到四姐家。那時,堤口和二七,在濟南市的一南一北,都屬于郊區。公交車又少,等車、乘車再加步行,一切順利的話,單程至少也要一個小時。每天一大早,母親要趕在四姐夫上班前到四姐家,傍晚,等四姐夫下班到家后,馬上返回。家里還有姥姥、我和幾個哥姐一大家子需要母親照料。有一天母親返回時,電閃雷鳴,狂風暴雨,母親在堤口鐵路宿舍站下車時,路邊的排水溝濁浪翻滾,急流滔滔,溝上的小橋被淹沒了。母親急著回家,撐著傘蹚著水試探著找橋過河。有一個在房檐下避雨玩耍的女孩一邊大喊一邊用手比劃:“別往前走啦!別往前走啦!橋在那邊!往那邊走!往那邊走!”按小女孩的指點,母親才蹚著水安全過了橋。命運安危就在那多走或少走一步上。此后母親多次提起此事,說多虧那女孩……
第二件。二女兒高爽出生后,四姐夫請來他的十五六歲的、在家等著就業的妹妹前來照看。小爽身體素質好,十一個月就能跑了。一天上午,小姑看小爽睡了,就去樓道上廁所。哪知,小爽被尿憋醒,醒了就向窗戶爬去。窗戶分上下兩部分,下部是兩扇小窗扇,上部是兩扇大窗扇。因天熱,大小窗扇都開著。小爽扶著床頭站起來,撒了泡尿,接著向窗口攀去。
對面小院里站著個人,不經意地往樓上看,發現三層有個娃娃獨自爬上窗戶玩。正納悶,卻見娃娃翻過窗戶,栽了下來。
樓下二層那家,在窗外支了個晾衣物用的架子。小爽被那架子擔了一下。這一擔,起了緩沖作用,也躲開了下方的水泥散水。小爽落到土地上,但額頭卻磕在一個花盆上,把花盆砸碎了。
一樓那家聽得院子里“咚”的一響,趴在窗戶上一看,地下趴著個孩子,滿臉是血,正哭著仰頭向上看。
“樓上掉下小孩啦!”一時間,對面小院里的人也喊,樓下那家的人也呼。
小姑回到房間,不見了小爽。聽得外邊一片驚叫聲,從窗戶探出頭去,見樓下好多人沖著她的窗口喊,一時魂飛魄散。
鄰居們快速把小爽送到四姐工作過的二七飯店,店主任急忙找來輛卡車,火速把小爽、小姑和熱心幫忙的鄰居送往醫院,同時電話通知四姐的單位。把小爽送到急救室后,主任帶卡車返過頭去接四姐。四姐接到電話,說孩子摔著了,也沒怎么當回事,騎上車往二七趕。路上遇到那輛卡車,主任不由分說讓四姐上了車。看這個陣勢,四姐預感到出大事了。越急越出事,卡車熄火了。主任又跑著找公用電話,打電話又借了一輛車。到了鐵路醫院門口,見好多鄰居站在那里交頭接耳,見四姐來了,圍上來說:“放心吧放心吧,孩子安頓好了。”四姐仍不知情,緊張得要崩潰了。沖進病房,小姑“嗷”的一聲撲上來,抱著四姐大哭。再看病床上的小爽,頭上粘著塊紗布,鼻子和下巴抹著紅藥水,正睡著。醫生說,額頭有傷,縫了三針。是否影響到其他器官,還要觀察。
小姑依然大哭不止。四姐知道了原由,后怕的同時,也心疼起小姑來。這次意外,對小姑的打擊太大了。她也只是個孩子啊。
星期天節假日,四姐常約我和哥哥姐姐們到她家玩。一般是上午去,在四姐家吃過午飯,四姐、四姐夫,還有小鴻、小爽,一起爬英雄山。在烈士紀念碑前的臺階和大理石地面上玩耍打鬧,到山林里摘酸棗,每次都極開心。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四姐夫舉止文雅,四姐和藹可親。他們住過的地方我都住過。去四姐家,是讓我歡快的大事。
樓房又換成平房
濟南緯十一路,俗稱十一馬路,一個小四合院里有一套18平方米的住房,住著一對夫婦三個孩子共五口人。這家人想找單位換大點的房子,但現住的房子有點大,理由不充分,就想換個小點的房子再找單位。四姐和四姐夫得知了這個信息。一是因為小爽的事對高樓有些懼怕,二是那里面積大出四平方米,三是離我母親家近了許多。1976年,四姐一家就與這家互換了住房。那房子里間6平方米,外間12平方米。房子不知道建于什么年代,看著挺舊,屋內頂棚都破了,露著房梁和屋頂。四姐找同事幫忙,用報紙重新糊了頂棚。
這個小四合院住著5戶人家。每家在門口安放個煤球爐做飯。廁所和水龍頭在院外胡同里,幾個院子的居民共用。就一個粗鐵管的水龍頭,二十多戶居民又洗菜又刷碗又洗衣,經常需要排隊。四姐家就買了一只大水缸放在屋里儲水。洗衣服,要在家里打肥皂搓洗完,半夜水龍頭處沒人了,才去涮干凈。冬天,水龍頭處結滿冰,凍手滑腳,洗衣服很受罪。
不管怎么說,總算擁有里外間的房子了,覺得比二七寬敞實用多了。他們在外間屋安了張床,四姐夫把父親從青島接來住,四姐一家四口在里屋睡在一張雙人床上。一家三代過得也其樂融融。屋子潮濕不通風,夏天天長,又熱,晚飯后,一大家子五口人在屋里呆不住,就卷著涼席,拿著蒲扇,沿鐵道往西走,找個空地鋪上涼席,或坐或躺,乘涼,拉呱。
兩間換成三間
鄰居在閑聊時,提供個信息,說有人想用館驛街那邊的一套房子換這邊的房子。四姐兩口子就去看房。在天橋南頭,一個小院里住著五戶人家。那套房子在進院門右首南排第一戶,外間6平方米,里間12平方米,另在東排還有一間單獨的6平方米的小屋。比十一馬路又多出一間,而且離四姐、四姐夫的單位都近,離小爽的幼兒園也近,隔兩條馬路就是濟南市經一路小學,距公交車站也不遠,感覺挺合適。發現房子的一面墻有條大裂縫。屋主人說這是土坯墻,很厚,沒事。于是決定搬家。這是1977年的事。
這次換房是三家輪換。這套房的房主是A,A家要搬到B處,B家搬到四姐處,四姐搬到A處。四姐蹬著三輪車,把家具從十一馬路拉到館驛街。要卸車時,鄰居告訴她,這房子不是房管局的房子,是企業代管房,不用交房錢,企業是不是負責維修很難說。四姐聽了,心里嘀咕,這不交錢的房子可不敢住。馬上通知B家暫時不要搬。去找到房子所屬的企業詢問。企業說有大修計劃,但什么時候修不知道。四姐越想越害怕:要是遇到大風大雨惡劣天氣塌了怎么辦?蹬著三輪往回返。回到原來的家一看,門上了鎖。原來,B家接到四姐電話后,生怕有變化,馬上把家搬了。等到那家人下班回來,對她說,不是不讓你們搬嗎,怎么搬進來了?那房子是危房,我們怎么住?那人也不理,開鎖自個進了門,反身關門。四姐要進,她不讓,在門里頂住門。房子沒換成,還沒了住處,四姐也急了,就在外用力擠,邊擠邊說:你不開門,我在門口守著,你也出不來。那家聽了,想想也是,只好把門開開,四姐這才把家具又搬了進去。那段時間,那家人住里間,四姐一家住外間。里間外間,滿是家具,僅有插腳的地方。兩家就這樣心里憋著氣,開一把鎖,進一扇門,在一套房子里分別吃住。真是抬頭不見低頭見,見了也不愿意搭訕。兩家都反復找那企業,企業終于同意馬上修。十幾天后修好,四姐一家才搬過去。
不久,那企業決定對那里的代管房進行大修,四姐又借了我八哥的一間屋,搬進去暫住,修好后再搬回,這才正式享受那三間房。多出的小房,支了張床,來人可住;在屋門口壘了間不到一平米的小廚房,終于也有了單獨做飯的空間。
四姐一直念叨,說家搬來搬去,我八哥的貢獻最大。那時,我的六哥七哥上山下鄉去了,我八哥正年輕,同學、朋友多,也熱心。一聽說要搬家,馬上借車、找人,沒少忙活。
這里和十一馬路一樣的是,水龍頭和旱廁都在胡同里,五六個小院的居民共用。四姐家的院內,住著五家,都在各自的門口建了小廚房,院子空間就很小了。有一家把廚房建得較大,影響了其他兩家,那兩家反對,但這家還是硬建起來了,鄰里由此不和。但四姐一家和他們處得都挺好。四姐家對門的李大嬸是個熱心人,每天在蜂窩煤爐上用一只大鋁壺燒開水,水開后就提著大鋁壺到四姐家來,把三四個暖瓶給灌滿。
1980年,四姐家的二女兒小爽就近上了濟南經一路小學,大女兒小鴻也從原來的鐵路職工子弟第三小學轉入該小學,姊妹倆相伴一起上學,一起放學。自那開始,生活漸漸地好起來。當年,買了一臺黑白12吋電視機,1981年買了小鴨牌洗衣機,1983年請人做了一個大立櫥。
1981年,離高考還有幾個月。我為找不到安靜的地方學習發愁,四姐就讓我去她那間6平方米的單獨的小屋去學習。小屋內擺了一張單人床,一只箱子就當書桌了。每天晚上,我就去那間小房復習功課。星期天全天都在那里。房子很小,但獨立、封閉。想想陳景潤當年就是在一間六平米的小屋里論證的歌德巴赫猜想,覺得有這小房就非常幸福了。我還在那里讀了托爾斯泰的《復活》和一些經典散文。
那時,全社會興喝紅茶菌,據傳包治百病,延年益壽。四姐也做了一些,每天晚上,都要給我送一杯,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喝。經常讓小鴻或小爽給我送西瓜和水果。早餐與他們一家一起吃飯,面條里,一定有荷包蛋。
新樓房,三室,有廚房,有廁所
四姐夫是中專學歷,在那個年代,也是為數不多的高學歷人才。他又肯學、肯鉆,在技術、業務方面都很出色。改革開放,鐵路也重視經濟效益了,四姐夫被調入鐵路局裝機廠,憑知識和技能,為廠里贏得了大效益,成為重要的技術人才。還研制了一種液壓機,獲了鐵道部的科技創新獎。1985年,裝機廠在濟南南門富安街建了一棟五層的樓房,一至三層安置當地的拆遷戶,其他房子由四姐夫優先挑選。四姐夫選了四層一套三室的房子,套內面積有六十多平方米,有廚房,有廁所。從當時看,是比較寬大高檔的住房了。地理位置也好,就在黑虎泉、趵突泉附近。在1985年4月14日的日歷上,四姐夫寫下“今日搬富安街新居”幾個字,并把這頁日歷撕下來,夾在記事本里。當天,我找了十幾個朋友去幫忙搬家。
樓房高聳在一片平房當中,東西朝向。東邊的房間可以看到日出,西邊的房間可以看到日落。樓下有專門存放自行車的車棚,不像別的樓房,還要往樓上家里扛自行車。
房子,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到了現在,住得如此寬敞舒坦,哪會不心滿意足?房子,也是社會地位、人生價值的體現,有了好房子,出出進進都覺得體面,覺得活出了尊嚴。
遷居青島
四姐夫的廠子為了增加收入,搞了不少外委工程,青島一家機械廠是他們的客戶。那廠的廠長雄心勃勃,要把廠子做大做強,在業務往來中,看中了四姐夫,決意要把他作為特殊人才挖去。四姐夫的一位親戚也有意促成此事,兩邊鼓動。
四姐夫猶豫不決,一是在單位干得正順風順水,二是不舍得這套好房子。廠長到家里來看,說,就這房子啊,放心吧,我在青島給你解決,保證不比你這房子差。還打包票,說只要四姐夫到他們廠,就給解決職稱和入黨等問題。還答應給四姐找好單位,給孩子找好學校。之后多次給四姐夫寫信,催他盡快決定。
青島那邊,四姐夫的幾個兄妹的住房都非常緊張。四姐夫的父親先和二兒子同用一套房,二兒子的兩個女孩一個男孩都大了,生活諸多不便,又搬到四兒子家,只因四兒子的一兒一女年紀稍小,還可勉強跟老人擠在一間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住。可老人越來越老,孩子越來越大,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這成了四姐夫的心病。那邊如此器重自己,事業上可大展宏圖,待遇上會提高職稱,政治上能夠入黨,生活上提供好的住房并安置妻女的工作和上學問題,去了就可以把老人接到身邊贍養,一舉多得。匯總種種理由,四姐夫決定答應那廠長。可是四姐堅決不同意。
四姐的工作經歷比較曲折。她十六歲參加工作,在地毯廠織地毯。1970年,工廠處停頓狀態,被調入濟南市飲食公司紅旗核算店火車站供應點,工作就是在濟南站站臺向旅客售賣肉燒餅和肉包子。旅客列車來之前推著售貨車去站臺,火車開走后再推著車回到供應點。每個班往返多次,推著車過鐵路,再上站臺的陡坡,危險且辛苦。后因懷孕,調到離家近的二七飯店,主要工作是和面蒸饅頭。這是個出大力的活,每天上班,往大案板上倒上四袋子二百斤面粉,在面粉中掏出個大坑,里面放上大塊頭的老面,再加入溶有堿粉的溫水,用手攪拌、擠按,讓老面、堿均勻融入新面,再搓揉成一條條粗面柱。然后把粗面柱疊摞在一起,用刀橫著切出一塊塊的面團,反復揉搓,為的是蒸熟的饅頭口感“筋道”。最后制作成一個個“高樁饅頭”,入屜。籠屜很大,一屜能放一百個饅頭。整個飯店的面案工作,只有四姐和一位女工負責。隨著身體越來越笨重,每天累得直不起腰,邁不開腿,走起路來像鴨子一樣。在大女兒鴻鴻出生后的哺乳期里,利用把籠扇抬到鍋上開蒸的半個小時時間,跑著回家給孩子喂奶,除休產假外從未影響過工作。后來,被安排到旅館部做登記工作。偶然機會,調到核算店當會計。后機構調整,核算店撤銷,成立區中心店,被安排到中心店做主管會計工作。中心店又改為區飲食公司,被提拔為飲食公司財務股股長,負責管理幾十個國營、集體、代營飯店的財務財會工作。
四姐工作順利,領導器重,1985年就入了黨。她舍不得工作,也舍不得濟南的父母弟妹。為此,和四姐夫暴發了激烈的爭執。四姐夫性格易急易暴,說:“你有父母兄弟姐妹,我也不是石頭縫蹦出來的!”四姐夫去找我父親,做我父親的工作。
我父親社會經驗豐富,又是極理智的人。仔細聽了四姐夫的述說,發現那廠長的有些承諾超出他能操控的范圍,設想也比較空泛,便這樣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你講了好多回青島的理由,除了照顧你父親這一條,其他我都不同意。”
四姐夫有了這“尚方寶劍”,四姐只好妥協。
著手辦理調動。兩口子興致勃勃地來到青島,落實房子的事。廠長卻改口說,青島房子不比濟南,那是相當緊張的!你們先來上班,慢慢解決。兩人一聽,心冷了半截。回來馬上跟單位說,暫停辦理調動。廠長得知,打包票馬上解決。他們又去了一次青島。在廠里提供的三套住房中,選中了瑞昌路一棟樓三層三居室的房子,和濟南的房子面積差不多,建于1984年。里邊正住著一戶拆遷戶,說七月份才能搬走騰房。辦妥了住房手續,他們心才踏實下來。那邊催著上班,騰出了一間工會招待室讓他們暫住。這才正式辦理了工作調動和孩子轉學等手續。先從濟南把生活必需品拉去一車。一家四口住廠里,諸多不便,又被安排到嘉定山一間倉庫臨時湊合。嘉定山上沒有水,只有一個蓄水池,有送水車一周往池里送一次水,水里生了不少小蟲,不能飲用。他們只能用自行車馱著大水桶到山下人防工程接自來水運到山上。山上蚊子成群結隊,天再熱也得穿長袖衣褲,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可蚊子隔著衣服也咬,咬得人亂蹦。想盡辦法也斗不過蚊子,每天只好早早地躲進蚊帳。熬了四個多月。
直到1988年11月20日,那戶拆遷戶才搬走。21日,廠里派人簡單粉刷了房子。22日,四姐一家正式搬入。
從濟南往青島搬家,家具也多,曲折也多,從1988年放暑假開始到11月,總共來了三次汽車才搬完。
入住的第二天,23日,正好是四姐夫父親八十一歲生日。在嘉定山時,四姐夫的父親就過去與他們一起住了。在這套住房中,老人有了單獨的屋子,這是老人多少年沒有的享受。生日宴會是在新家舉辦的。青島的親戚能來的都來了。老人開心,大家也都高興。老人喝了幾口酒,說:“享福啦!我還能享三年的福。”老人的預感真是神奇,就在三年后這一天的11:45,老人與世長辭了。這三年,有自己的居室,又有四姐、四姐夫和兩個外孫女的精心伺候,盡享了天倫之樂。
四姐夫來到新廠子,沒有像想象得那樣順利。人際關系難處,工作開展受阻,職稱、入黨等承諾的事均被擱置。兩個孩子上學也費了好大的周折,最后終于在十六中和十八中分別安置了。四姐也沒像承諾的那樣被安排到先前許諾的大單位,而是被安置到青島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下屬的一個服務公司,而且沒有具體工作,整整被閑置了半年。從工作獨當一面到被閑置,所產生的失落感和苦衷,只有她自己知道。
服務公司下屬有幾家飯店、旅館,還有面包房、小賣部、土產店和一個光華機械廠。第二年春節后,四姐被安排做服務公司的內部審計工作,也參加一公司計劃科、機械設備科、計量室的會議和這些部門的檢查和部署等工作。不久,上調一公司審計科,從負責人干到副科長、科長,直到退休。
搬到青島的第六個年頭,1994年初,四姐夫因病早逝,終年54歲。
小鴻、小爽漸漸長大,成家。開始時生活也很艱難,結婚時都沒有自己的住房,完全靠自己,從無房到有房,從小房到大房,日子過得越來越好。小鴻搬了6次家,小爽搬了8次家,各有各的豐富的搬家史。現在都不止有一套住房。
住上了好房子
瑞昌路的那套房子在馬路邊。青島修建地鐵,晚上,裝滿渣土的重型大卡車從這里穿城而過,把路面的井蓋軋得咣當咣當響。夜深人靜,響聲格外驚人。四姐晚上沒法安睡,多次找有關部門,也沒辦法解決。這成了四姐的一塊心病。小女兒小爽兩口子經濟條件好一些,為母分憂,選中了遼寧路一處住房,買下給四姐住。這是四姐想不到的。那是一套寬敞的大房子。兩室一廳,127平方米,比原來的住房大一倍還多,僅門廳就有二十多平米。兩個主臥和門廳都朝陽,透過大窗戶向外看,可看到南邊的儲水山。平時四姐一個人住,兩個女兒周未和丈夫孩子來一起過,一大家子七口人,熱熱鬧鬧。年節或生日,為了不讓四姐勞累,常常下個飯店。四姐也一再約弟弟妹妹們去住。去年11月我在那住了好幾天,太陽一出來,陽光就曬進半間多屋子。陽臺種養了些花草。這房子住得好寬敞、好自在。
在這樣的房子里,就只有享受了。我問四姐,一個人住這么大的房子,寂寞不?她說挺好的,喜歡靜。現在正在老年大學書法班學習,終于也圓了大學夢,無事時就練字,字已寫得有章有法。春節時有不少求楹聯裝飾大門的,四姐都是來者不拒。
現年70多歲的四姐,樂觀開朗,不急不慌,心靜似水。談起往事,每個細節都歷歷在目,記得很清楚。那銘刻在心頭的印記,那苦澀的往事,曾掀起過多少情感的波瀾,怎么會忘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