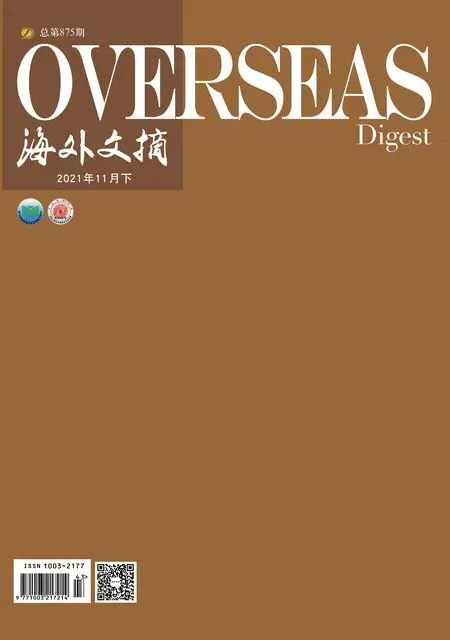論中國翻譯史上政治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王思齊
(青島大學,山東青島 266071)
1 意識形態中的政治因素對翻譯實踐的影響
意識形態,屬于哲學范疇,可以理解為對事物的理解、認知,它是一種對事物的感觀思想,是觀念、觀點、概念、思想、價值觀等要素的總和。意識形態不是人腦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會存在。人的意識形態受思維能力、環境、信息(教育、宣傳)、價值取向等因素影響。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同一種事物的理解、認知也不同。意識形態中的“政治”是個寬泛的概念,它包含了各種集體的政治行為和個體政治行為。翻譯的實質是翻譯主體的譯者進行主觀選擇和決定的過程。
美國翻譯學家安德烈·勒菲弗爾闡述了影響翻譯的“兩要素”理論,即翻譯自始至終都會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觀的影響。譯者的意識形態和翻譯當時接受文學中的主流詩學是決定翻譯所投射的文學作品形象的兩個基本因素,而其中譯者的意識形態又是首要因素,他決定了譯者所要采取的基本翻譯策略。操縱翻譯策略選擇的主流意識形態可能是譯者本身認同的,也可能是贊助人強加給他的。翻譯活動的贊助人對意識形態往往比詩學更感興趣,他們會通過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左右譯者的翻譯策略,保證譯作所反映的意識形態符合其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而不會破壞社會體制的 整體穩定和正常運作。
根據Lefevere 的理論假說,政治因素作為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方面也必然對翻譯實踐產生重大影響。而其中譯者的政治意識形態,贊助人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民族意識形態都是政治因素的具體體現。目的語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操縱著譯者的翻譯策略。一方面,處于政治的考慮,對遇到可能引起麻煩或糾紛的內容,譯者或者加以刪除,進行淡化,一般都會自覺地避免譯入那些有可能觸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論或描寫。另一方面,出于某種政治心理或者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果需要,譯者也會竭盡渲染之能事,濃墨重彩地突出與之政治意識形態相吻合的部分。
中國的四次翻譯史高潮,從政治意識形態和翻譯作品之間的關系分析來看是可以印證Lefevere 的這一理論的。不同時期的主要翻譯作品隨著各個不同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而變化。
2 翻譯的第一次高潮——佛經翻譯
我國翻譯史上第一次翻譯盛況始于佛經翻譯。它始于東漢,鼎盛于唐代,延續至宋元,歷經一千多年。意識形態對于翻譯的影響由此次佛經翻譯盛況中可見一斑,主要反映出社會意識形態直接促進了我國翻譯的發展,并影響了當時譯者選擇的翻譯內容和方法,而翻譯內容又反過來促進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兩者互相影響,相互制約。
東漢時期,群雄割據,政治腐敗,社會動蕩不安,給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民間對統治者的壓迫怨聲載道,不斷爆發農民起義。由于宗教能夠麻痹人們的思想,幫助統治階級統治人民,鞏固地位,佛教的傳入順應了當時的統治需要。此外,佛教教義與儒教、道教的道義有契合之處,也能夠融入我國宗教主流。
佛經翻譯在隋唐時期達到全盛,在初唐時期佛教發展到達頂峰。一方面,唐朝國力強大,統治階級繼承以往傳統,對佛教發展極為重視,另一方面,統治者也認識到勞動人民的重要作用,實行親民政策,對儒、道、釋各教加以利用。這一階段譯經活動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佛經翻譯事業達到了頂峰。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了國立翻譯院,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這時的譯者主要是僧人,其中較為著名的翻譯家有支謙、道安、鳩摩羅什、玄奘、贊寧等。這一階段翻譯理論興起,其中支謙為集大成者。他撰寫的《法句經序》開啟了“文與質之爭”,為我國翻譯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實際上,佛經在中國的翻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本土文化思想在譯經的過程中對其譯文和翻譯方法的選擇產生重要指導作用,其意識形態逐漸滲透于譯文當中。例如,印度佛教起初有悖于中國傳統的元氣靈魂之說,然而為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譯文主要采取歸化策略,選擇用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儒家、道教等意識形態來翻譯原文。
3 翻譯的第二次高潮——明末清初科技翻譯
不同于之前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時期翻譯了大量的自然科學書籍,掀起了中國翻譯史上的又一次高潮。當時的意識形態的變化直接促進了此次翻譯盛況的出現。15-16 世紀西方世界已經基本經歷了文藝復興時期,而且進入了資本經濟發展時期,科技領域出現了許多重大的發現。中國封建文明經歷唐宋以來的高峰,開始進入沒落時期,再加上南宋以來新儒學長期排斥禁錮人們的思想,佛學過于虛幻,已逐漸失去優勢。而中國正處于明朝末年,統治階級昏庸無能,宦官專權,政治腐敗,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趨于式微,本著強國愛民思想,士大夫階層主張向外求索,有選擇地引進并翻譯了大量有關西方哲學和科學相關的書籍,以期達到開啟民智的愛國理想。
另一方面,明朝中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明末清初時,西方殖民者入侵我國東南沿海,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進行傳教活動,在傳教的同時,也與中國的學者合作翻譯科學著作。由于當時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開明人士也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科技技術來抵御侵略鞏固封建統治,于是和西方傳教士一起翻譯西書,促進了中國翻譯史上第二次高潮的出現。
這一時期共成書400 余種,其中科學譯述186 種左右,內容涉及天文、物理、地理、生物等學科領域。利瑪竇和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和《測量法義》一卷,《測量法義》使中國從此有了經緯度的精確概念。李之藻與利瑪竇合譯了《同文指算》,使筆算在我國重新開始普及。在其他學科方面,中西人士合作的翻譯也都帶來了不小的成果。例如在生物學上引進達爾文的進化論;地理學上翻譯了世界地圖;醫學上引入了解剖學的概念等。
社會環境背景不僅影響譯文內容的選擇,還影響著翻譯策略,使譯文融入當時的社會語境,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例如,在《天主實義》一文中,譯文無論是從語言修辭上還是句式句法上都趨向我國當時的語體文化,將源語文本映射到譯語文化,譯者的意識形態在這里起著決定性作用。
4 翻譯的第三次高潮——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時期
這一時期,中國國運多舛,矛盾凸顯,社會思想激變,強國救民成為這一時代主題。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國內的有識之士在痛苦和屈辱中開始深刻反思并逐漸覺醒。可以說,中國近代的翻譯事業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入侵開始的。人們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和機器制造。洋務派設立了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等譯書機構,大量有關工程技術、軍事武備和自然科學類的西方著作被介紹到中國。甲午戰爭之后,有識之士意識到光學習西方的技術是不夠的,同時還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于是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開始大量譯介西方具有先進民主思想的社會科學書籍。1898 年,嚴復翻譯《天演論》,他向國人介紹了弱肉強食的道理。書中宣揚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思想成為當時救亡圖存的理論基礎。他先后翻譯了10 多種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和邏輯學著作。此外,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為20 世紀中國翻譯的發展奠定了基調。林紓,作為同時期另一翻譯大家,譯文采用歸化策略。不同于嚴復多譯介關于西方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的文本,林紓翻譯了大量的外國小說,其作品是個人民族意識和社會救國思想的結合。林紓與王昌壽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開啟了文學翻譯的新紀元。包括林紓作品在內的翻譯小說的風行,實質上是知識分子以通俗文學啟智國民,譯介當時西方資產階級的先進意識形態,抨擊封建傳統禮教,以達到文學救世的目的。與此同時,梁啟超也翻譯了大量日本小說,以《佳人奇遇》《經國蘭談》《日本東海散事》為代表。這些小說作品大多數表現了主人公少懷大志、心系國事、指點江山的慷慨情懷,這些小說被譯者看作是啟迪智慧、救國開化的政治教化工具,符合了當時有識之士進行社會變革的需要,具有醒世的社會功用。
與嚴復、林紓的歸化翻譯方法不同,20 世紀另一偉大的翻譯家魯迅則主張采用直譯的方法。但殊途同歸,魯迅所提倡的直譯同樣旨在運用外國的先進思想救國啟民。魯迅主張“寧信而不順”,要保留“原作的豐姿”,要完整忠實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魯迅將翻譯中技術上的決策上升到政治層面,并發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來闡述自己的翻譯理論。這都表明了當時社會語境中的政治改革的意識形態對魯迅等文人學者在翻譯內容和策略上的選擇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5 翻譯的第四次高潮——現當代翻譯
進入新世紀,中國為了發展經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此形勢下,中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也愈加頻繁,政治、經濟、文化等交流也愈發深入,這就促成了中國翻譯活動的又一次蓬勃發展,翻譯也越來越走向跨學科、專業化等方向。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意識形態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翻譯家的翻譯目的,并且會進一步影響翻譯家的翻譯思想。同一時期翻譯家的目的及思想又都比較相似,這就使得政治因素得以顯現。
這一時期,翻譯的作品的數量也越來越多,但是翻譯家翻譯作品的初衷都是為了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中國的翻譯事業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也對翻譯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大力支持,這就導致了翻譯事業呈現了蓬勃發展的狀態。中國同世界各國各個領域的交流使得譯者翻譯的領域和分工也更加明確,針對性也更強,翻譯的材料向學科化發展的趨勢也更加明顯。
外交關系對翻譯活動也有影響。兩國間文化的交流,常系于兩國間政治和經濟上的關系。外交關系愈加密切,其文化關系亦愈加廣泛。翻譯家翻譯的原文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所處時代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決定的,經常出現的情況就是在某一時期與哪一國關系更親近,翻譯的這個國家的作品就更多一些。從19 世紀末直至當代,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不同階段。從1842 年鴉片戰爭至1895 年甲午戰爭,有數據顯示,當時翻譯的作品有50%都來自英國。從1895 年甲午中日戰爭到1919 年五四運動,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的崛起以及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對中國造成的刺激,改革運動主要目標在于仿效日本,因此這一時期從日文翻譯的著作高達60%。而后隨著日本對于中國的侵略,使得中日關系惡化,留學生更傾向于留美,引入了大量翻譯美國科學和文學作品。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采取“一邊倒”的外交策略,只與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這個時期的翻譯的俄文譯作則成為了主流。直到20 世紀70 年代中美建交,帶動了一大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中國建交的熱潮,中國則又開始傾向翻譯西方各個國家的作品。綜上所述,政治意識形態能夠起到推動翻譯活動不斷發展的作用,也會對翻譯活動起到阻礙甚至破壞作用。因此,要想翻譯活動能夠健康穩定地發展,如何適應并積極回應政治環境的要求也是翻譯家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之一。
6 結語
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符號的轉換,它與社會環境緊密相連,具有明顯的時代特點。中國的翻譯史與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和思想銳變息息相關。翻譯活動從來都是與一定歷史條件文化環境緊密相連并受到主流意識形態控制和影響的。意識形態從翻譯理論、文本選擇、翻譯策略等多方面影響著翻譯活動的發展。因此,翻譯活動應被視作一種復雜的文化行為,而意識形態則是進行翻譯研究時不可忽略的一項關鍵因素。本文通過重點分析政治層面的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影響來為翻譯活動研究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