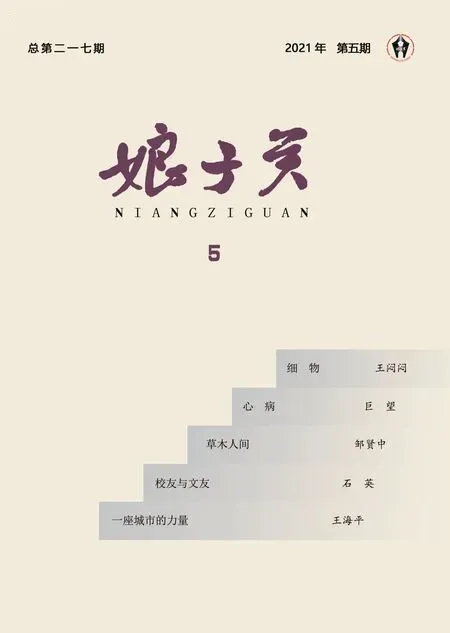校友與文友
◇石英(北京)
本世紀初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的一個電話,說近期組成一個作家訪問團赴臺灣,成員有我,時間十一二天吧,希望我有個精神準備,隨后再把相關資料寄給我。
去臺灣,這是我久所盼望的機會,心里當然是高興了,在過了些天收到的資料中,我最為關心的是訪問團的名單了。看后約略記得有十人左右(今天真的記不確切了),其中有的我認識,但一半以上是不認識的。即使在認識的作家中也無深交,只是在某個會議上見過面點頭之交而已。但名單中的作家“成一”卻引起了我的注意:雖然以前沒見過面,但對他絕不陌生。他好像是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同我——是校友;畢業后分配至山西工作,寫了不少小說及其他作品,其代表作《白銀谷》獲過獎,我還曾讀過,是一位功底扎實而不那么張揚的作家。既然是同校同系的校友,未曾見面之前先有幾分親切感。
過程毋須細述,一切手續辦理完畢后,定日在首都機場聚齊。第一次與成一見面便覺得與我想象中的形象高度契合,也是我歷來最認同的那種類型。原來,他早就知道我也是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老校友,而且都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畢業的,只不過我是在頭(我是1961年),他在尾(1968年)。
在從北京至香港,又從香港轉機飛臺北的途中,恰巧座位又挨在一起,一路之上,又聊了不少的話。記得最深刻的是關于當年給我們授課的老師,有好幾位是重合的,而評價同樣是十分相似,足見彼此的看法尤其是價值觀這一點是非常相近的。
更加巧合的是,在臺灣住過幾家不同的賓館,在分配房間時我們每次都是同居一室。我想這絕非是誰的有意安排,卻使我不經意間覺得“恰到好處”。在一起住,自然交流更多,彼此更為熟悉。尤其是他對我,處處注意照顧和禮讓。也許是他考慮我比他年長之故,乘車時讓我坐“好座”,就餐時推我坐“上位”。為此常常相互推三讓四,最后往往是我不得不“服從”。因為我感覺到他很執意,還說“你是大學長,應該如此”。其實我心里明白:這是他尊重他人的品性使然。
另有兩件事使我永遠難忘:一件事說明他在“獲得”面前不僅不爭先,而是一個“自覺后退者”。那是在全部活動即將結束前夕,我們訪問團去參觀了一個臺灣業余畫家活動室。有數十位丹青手都在作畫,表面上的平心靜氣,也能看得出他們無不在全力展示自身的才藝。
我們大家看了一個時辰之后,對方畫家的負責人落落大方地高聲說:“大陸采訪的文友請不必客氣,可以與在場的畫家自由交流;如果哪位喜愛我們中任何一位的畫作,也請盡情表示,我們都可以慷慨贈予;凡是到場的大陸朋友,都不會讓你們空手離去的。”我們訪問團的作家也很熱誠,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審美眼光,與對方業余畫家們交談起來。在這當中,我和成一表現得最為靦腆,遲遲地不肯向前,更不好意思張口“點畫”。最后還是一位舉止文秀的中年女畫家主動提示我倆:“我們負責人有言在先,您可是要賞光的喲。”到這時,我們不可再拘謹了。最后我拿了她的一幅小面紫羅蘭;成一也拿了一幅,我忘記畫的是什么圖案了,反正也是小幅的。對這件事,事后我們彼此啥也沒交流,只不過我心里還是覺得:這是他本性的一部分,完全合乎邏輯。
另一件事與我有關。同樣是在環島游歸來的最后日程中。大約是在淡水附近的一個古鎮(至今連名字也忘記了),只覺得是離大海不遠的地方。在路邊一側高高在上的一個登臨處,有很陡的臺階可以拾級而上,看上去頗為高峻,上面有傳統手藝店鋪,以及茶社、觀景點等等。在全團中,我的年齡有可能是最大的,但攀登上去也并無障礙。
上頭確實是不錯的。尤其是從最高處的觀景臺遠眺大海,景觀開闊而迷離。以我內心的判斷,似乎是大陸的方向,但沒有多嘴多舌地進行猜測。看了一會兒,我便離開觀景臺,上頭雖好,卻畢竟比較窄狹。這時我聽導游說了句:“下來的臺階在東面。”我們一行也自然地往東走。我自幼行軍慣了,一挪步就自然快步,走得慢了反覺得累。走著走著,可能自然地將眾人落在身后,倒也未細覺察,再往前走了一會兒,果然如導游所言,向下的臺階就在腳下,自覺反正就是這條路,徑走無妨。走著走著,就下到起行的馬路邊上,回頭仰視,同行者都沒下來,只以為他們走得太慢,在原地耐心等候就是。誰知等了近半個小時,也不見一個人影!這才意識到“有情況”,揣摩著是不是他們又從原路下來了?我不再猶豫,便向西撒開大步速行,也有半里開外,才走到先前上臺階的地方,仰望陡階之上,仍是一無人影,這時不敢再貿然輕動,但又等了二十幾分鐘,還是不見有人下來,于是復又東向下臺階處,再等一刻多鐘,最終失望。好歹等到有一陌生客下來,我向他打聽停車場的位置,雖有語言上的障礙,我連說帶比畫,他終于聽懂了,便為我指點了停車場方向,我這才不顧一切地向那邊飛奔,及至到達,幸而后尾尚有幾人正在上車。我急忙上前,聽司機師傅說:他們在上面本來是要下米的,但途經一個陳設優雅的茶社,臨時動議進去品茶,這才耽擱了近一個鐘頭。這時正是我在下面等得猴急,往返東西,哪里知道事情起了變化?及至他們品過茶往下走時,領隊同志才發現少了我一個,還是成一告訴他:“老石走在前頭,這時多半已經下去了。”可以想見,領隊同志這時非常惱火,匆匆下來,卻與往返穿梭的我打了個時間差。假如不是我果斷決定轉奔停車場,此刻多半還在那里傻等呢?
盡管人已“失而復見”,領隊同志仍然余怒未息:“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今后一定要保持步調一致,杜絕發生類似的事件!”我很理解:居于領隊同志的角度,他焦急上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中間也不能說沒有陰差陽錯的情由。我本人當場沒說一句話,倒是在開車之后,成一君開口了。“這事也不能全怪老石同志。開始時導游說下去的臺階就在東面,所以當時大家都往東走,老石走得快,在最前頭;后來臨時動議停下來喝茶,老石沒有聽見,他一拐彎就下去了。說實話,也就是我走得慢沒跟上,不然我也下去了。這里邊還是有些誤會的。”
他說過后,其他人都沒說話,只有領隊同志又重復說了一句:“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此番臺島之行,總的說來還是有收獲的;唯一的不甚愉快的小插曲我倒也沒太放在心上。不過通過這件事,我也更深刻地認識了一個人:他不僅是我的老校友,也不僅是一位很會寫小說的作家,更是一位該說話的時候不能故意不吭氣的公道守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