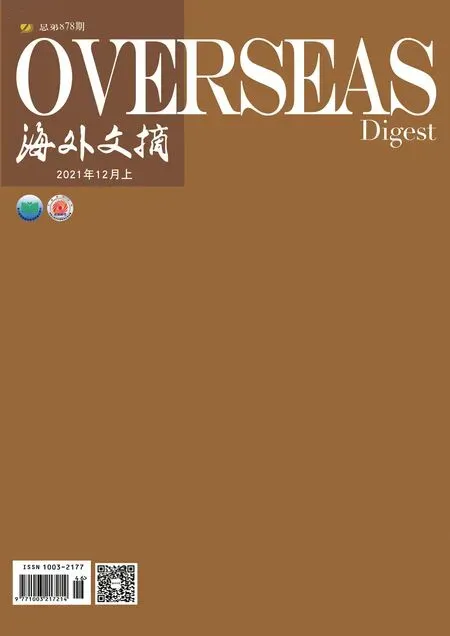張君勱與“人生觀論戰”
朱昆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遼寧沈陽 110031)
“人生觀論戰”起因是1923 年2 月14 日,張君勱應吳文藻的邀請為即將赴美求學的清華學子發表題為《人生觀》的演講。在這個演講中張君勱指出:“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他對人生觀進行了細致地分析認為:“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曰單一性的。”而由此出發,張君勱斷言:“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絕非科學所能為,惟賴諸人類自身而已。”張君勱的演講稿經整理后發表在《清華周刊》第272 期上,它是一個要求將人生觀從科學的束縛中掙脫的宣言,從而將科學與人生觀是何種關系這一難題直接放在整個中國知識界面前。從1923 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論戰文章合集《科學與人生觀》可以看出這次論戰影響之廣,直接參與論戰的學術界名流就有陳獨秀、胡適、梁啟超、任叔永、章鴻釗、孫伏園、朱經農、林宰平、唐鉞、張東蓀、陸志韋、王星拱、吳稚暉、范壽康等人。
1 “人生觀論戰”中張君勱的學術觀點
旅歐的求學經歷使張君勱對中國學界奉為圭臬的科學主義思潮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人生觀》一文中他系統闡釋了自己的文化觀點,首先張君勱要厘清科學與哲學在特質上的根本差異,按照他的觀點,科學有一定原理,而原理皆有證據。相反人生則不同,因觀察點不同,意見各異,所以自古以來最難以統一意見的事非人生觀莫屬。而關于人生觀具體的特點,張君勱列出五點:第一,科學為客觀,人生觀為主觀。第二,科學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于直覺。第三,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第四,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第五,科學起于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于人格之單一性。正是通過以上的論證,張君勱自信地得出了人生觀的五個特點,并堅定地認同人生問題的解決是科學無法解決的難題。應當說張君勱力倡這種植根于自由意志的人生觀是他在《人生觀》一文中所希望達到的直接目的,但張君勱所希望達到的又不僅僅在于此。人生觀是問題的癥結之處,但對于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建構的不確定才是張君勱所深深憂慮的,相對于西方文化的狂飆突進,中國是否已陷入到一種盲目的物質崇拜和文化精神失落的窘境中?正如他所言:“所謂精神與物質者:科學之為用,專注于向外,其結果則試驗室與工廠遍國中也。朝作夕輟,人生如機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則不可得而知也。”而這也正是他積極思考并希望能夠對當時中國知識階層有所啟發的關鍵所在。
在《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一文中張君勱開始嘗試較為系統地闡釋自己對未來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意見,“科學決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學而別求一種解釋于哲學或玄學中(或曰形上學)。”那么在張君勱心中何種哲學能夠合理地支配人生,換言之何種文化符合中國發展之方向,張君勱給出了自己的見解。在他看來這種哲學其實是一種復合體,一是首先必須向中國傳統儒學精神回歸,而且是向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心性之學回歸,其二就是借鑒以倭伊鏗、柏格森為代表的歐洲生命哲學,張君勱稱其為“新玄學”,在他看來 “新玄學”“與我先圣盡性以贊化育之義相吻合”從而實現一種東西哲學的有機結合,張君勱稱之為“新宋學”。“新宋學”對于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影響,他充滿了期待:“當此人欲橫流之際,號為服國民之公職者,不復知有主義,不復知有廉恥,不復知有出處進退之準則。其以事務為生者,相率于放棄責任;其以政治為生者,朝秦暮楚,茍圖飽暖,甚且為一己之私,犧牲國家之命脈而不惜。若此人心風俗又豈碎義逃難之漢學家所得而矯正之乎?誠欲求發聾振聵之樂,惟在新宋學之復活,所謂實際上之必要者此也。”歐游之行的切身體會,以及多年對東西文化辨析思考都使張君勱認定科學主義難以解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層次問題,甚至本身也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如他所言:“近三百年之歐洲,以信理智信物質之過度,極于歐戰,乃成今日之大反動。吾國自海通以來,物質上以炮利船堅為政策,精神上以科學萬能為信仰,以時考之,亦可謂物極將返矣。”張君勱在學術上的旨歸,確立了整個新儒家學派學術致思的方向,胡逢祥這樣分析:“很明顯,張君勱反復爭辯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目的在強調傳統文化,特別是宋明理學在現代文化的假設中仍具其特殊的生命力,它將迎合時代思潮由機械決定論轉向自由意志論的新趨勢,起到西方科學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此后現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學建設,正是沿著這一思路和論戰中提出的玄學研究模式展開的。”張君勱也因此成為新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者。
2 “人生觀論戰”中玄學派其他代表人物的觀點
對張君勱的觀點表示同情的還有林宰平、范壽康和張東蓀,這三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具有哲學家身份,他們在張君勱分辨哲學與科學的異同之時能夠產生一種學術上的共鳴。林宰平就批評丁文江想用科學一統天下的做法和“教主”無異:“現在在君先生的野心可就更大了,他不但想組織一系列的學問,還要把科學來統一一切。看他口氣,簡直像個教主。對于科學派無限擴大科學方法的做法,林宰平指出了一個他們無法回避的事實,那就是科學不能僅僅等同于科學方法,他還揶揄科學派不分科學方法與科學,把胡適之講《紅樓夢》也當成科學。科學派盲目擴大科學方法的疆域最后很容易落入空洞無物的境地。
范壽康的觀點則更為嚴謹,他首先判定科學可以分類為說明科學與規范科學,按照他的理論科學里面,凡是研究必然法則的稱為說明科學,研究當然法則的稱為規范科學。由此出發范壽康闡釋了自己人生觀與科學關系的看法:“人生觀與科學兩者,我以為大部分是有關系的,可是同時我卻主張科學決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全部。”依照范壽康的結論人生觀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管的直覺決定。后天的內容應由科學的方法決定。也就是說,人生觀的形式方面是超科學的,但是人生觀的內容方面確是科學的。范壽康的理論設計是頗為精巧的,他把人生觀與科學的論辯轉化為形式與內容的差別,這就調和了“科玄論戰”中非此即彼的極端看法,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反對科學肆無忌憚的侵入到人生觀領域。
張東蓀也是玄學派的主要代表,他在《勞而無功》一文中用馬赫和普朗克關于科學與哲學的爭論說明丁文江的做法是勞而無功,張東蓀還對丁文江無限擴張科學的做法進行了調侃,認為科學難以動搖哲學在人生觀中的基本地位:“我嘗說科學好像一把快刀,一切東西碰著了必迎刃而解,即最神秘的生命精神感情意志無一不受其宰割。但是只有一個東西仍然在外,即能宰割一切的刀其自身。換言之,即是偉大的智慧。”同時張東蓀還對丁文江混淆科學與科學方法的概念進行了批評:“科學方法與科學是不能分家的。這兩個東西,如影隨形,決不能說我們先提倡科學方法自然而然便發生科學。”客觀講將科學方法混淆為科學是科學派在論戰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也因此張東蓀的辨析在學理上的反駁比張君勱來的還要有深度。
3 “人生觀論戰”結束后張君勱民族復興理論的發展
1934 年,“科玄論戰”爆發的十一年后,張君勱發表了《人生觀論戰之回顧》一文。時間過去了十一年,張君勱的學術觀點沒有發生絲毫的動搖,正如他所寫:“人事界與自然界兩方之不同,這點我現在仍然絲毫沒有變更。”雖然在文中張君勱沒有能夠提供什么新的理論,但是一種訊息卻已經明確地表現出來,那就是代表傳統思想的保守主義正逐步興起。隨著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變化,尤其是“五卅”運動,“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侵華戰爭的步伐,民族危機日益嚴峻,救亡逐漸超過啟蒙成為時代的主題,玄學派開始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理論,以圖在此中國民族存亡絕續之際實現民族復興之大業。
張君勱認為要實現民族復興的偉業首先必須有堅實有力的信念,進而塑就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如他在《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一書緒言中所講的:“民族建國之大前提,曰民族情感民族思想民族意志之融化,此一事也。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強致,要在有全國人所推崇之文藝與學說,則情感、思想與意志自隨之而集合而融化。”德意志民族由四分五裂到團結統一,是在歌德、席勒、費希特、黑格爾和李斯特等杰出學者所奠定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基礎上實現的,而這種歷史經驗正激發了張君勱創建民族復興學術基礎的信心。在張君勱看來,建立符合民族精神的新哲學必須有三個基本因素:第一,自信;第二,毅力;第三,思想。而在具體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關系的問題上,張君勱認為必須要實現中西思想的溝通,相對于“科玄論戰”中雙方對于科學和形而上學過于極端化的看法,此時張君勱提出的見解要更為平和客觀,對于西方思想他認為:“關于域外智識域外語言,吾國人應盡量吸收盡量學習,……吾人在學術上立場言之,應當大開門戶不分界域。”而對于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張君勱認為應當給予重視,反對用民族虛無主義的看法對待傳統:“吾國人近來注重外國科學政治社會,視吾國舊文化為一文不值,然試思四千年之舊國,生存至于今日,豈無多少精華,可供子孫之保存者乎?……既為四千年之民族,必有其能生存之理由,從此點以下考察,則中華民族之成績,定有可以垂后者在,奈何吾國人并此自信力而無之乎?”很明顯這是針對全盤西化論的有力反駁,當科學派因倡導科學信仰而逐漸走向極端后,玄學派則努力希望矯正這一過失,從傳統思想中找尋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可資利用的思想資源。在《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一書所收錄的二十多篇文章無不體現了張君勱對傳統文化的理解與認同,他期待國人能夠在抗戰這一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實現民族信仰的吐故納新,最終創造符合時代特點和現代化要求的民族精神。從理論建構的層面來說,張君勱對于實現中西思想溝通的操作方法仍顯得空泛,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他理論探索的現實意義,在面對神州陸沉的危機時刻,張君勱力倡民族主義,高揚民族復興的理論旗幟,有利于振奮人心,堅定全民族抗戰的決心、信心,同時這也是新儒家思想開始系統理論建構的開始,是新儒家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注釋
(1)張君勱:人生觀,劉夢溪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張君勱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97-603.
(2)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劉夢溪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張君勱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43-660.
(3)胡逢祥.社會變革與文化傳統: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4.
(4)林宰平.讀丁在君先生的《玄學與科學》(張君勱,丁文江.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7.
(5)范壽康.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張君勱,丁文江.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320-321.
(6)張東蓀.勞而無功[A](張君勱,丁文江.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231-238.
(7)張君勱.人生觀論戰之回顧(張君勱.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80.
(8)張君勱.緒言(張君勱.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5
(9)張君勱.中華歷史時代之劃分及其第三振作時期[A](張君勱.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66.
(10)張君勱.中外思想之溝通(張君勱.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