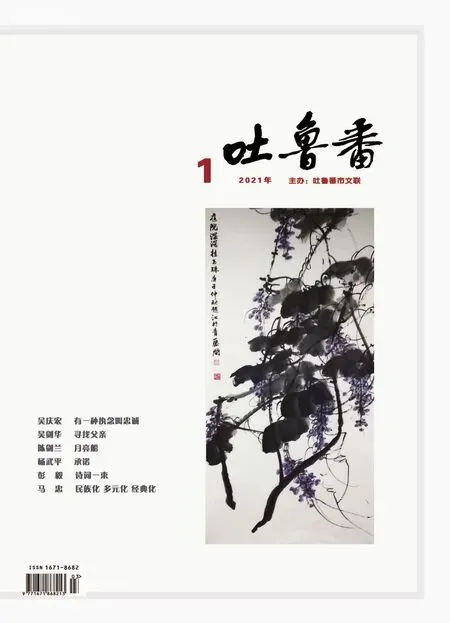傾聽一條河流的生命低語
如風
詩歌,或者說文字,是一個人內心的河流。
這個冬天,一個個安靜的夜晚,在燈下閱讀張發軍的詩集《回歸》,就像在傾聽一條河流的生命低語。這部名為《回歸》的集子,是張發軍一路走來,對生命對人生對世間萬象的徹悟。在自序中,他說:“生活中的我們,其實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追本溯源。無論是刻意還是不經意,我們都在不住向這個目標靠攏。當我將我的這本文集定名為《回歸》時,我被‘回歸’這個兩個字豐富的內涵所震動,我怕我的文字不能背負這兩個字的壓力,但我必須用這兩個字為我的這本文集命名。因為‘回歸’已是當下這個社會必須去追尋的主題,也是生活的呼喚和希翼。”
認識張發軍,是在沙灣雪水坊酒業董事長魯克文做東的一次聚會上,穿著黑T恤,悶頭喝酒,歌聲卻豪邁深情,詩人,社會身份是科技局副局長。席間,他送給我一本他的詩集《穿越》。后來的日子,我漸漸發現,張發軍是一個很有風骨和個性的真人。
而文學,是需要有硬度和風骨的。
文學,要給這個時代獻唱,不要給這個時代獻媚,要發自內心的抒寫,為天理立言,為百姓立命,為未來開風氣。薩特提倡作家們“介入”時代。這樣的“介入”,并非簡單的社會運動,而是要求介入者首先是一個存在者,在“存在”里“行動”,才是真正的“介入”。在當下的中國,有這么多尖銳的問題等待作家們來回答,作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絕擔負寫作在個人心靈中的責任,這樣的寫作,確實很難喚起別人的尊重。因此,作家要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眾人,面對現實;他寫的作品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這個時代肝膽相照,只有這樣的文學,才是有存在感的文學,有靈魂的文學。無疑,張發軍是位敢于面對現實直言不諱、針砭時弊的。他堅守個性,堅守著一種叫真誠的東西。他多次表示為當下一些作家缺少真誠的作品表示遺憾,他堅持著自己,堅持聽憑內心的呼喚寫作,不媚俗,不迎合。每次聽他這么說時,我看著他,默不作聲,內心在為他鼓掌叫好。
文學的真,是在心靈意義上的一種精神確證。一部好的文學作品,作者一定要把自己擺進去。文學只有寫出了“靈魂的深”,才稱得上是真文學。有的文學作品,即便技藝優美,詞句精煉,如果情懷是空洞的,心靈是缺席的,它也不過是文字游戲罷了。在這些作品中,摸不到作者的心,看不到作品后面有作者這個人,或者后面的那個人精神狹窄、靈魂干枯。文學的力量,也許是渺小、輕逸的,但它關乎心靈的自我援助,也關乎一種更高的人生實現。在文字中與作者的人生、心靈相遇,這是極為美妙的人生體驗。我們作家在創作的時候,都有一個想法,我們的價值何在?我們是否真的在某一個方向、某一個層面、某一個角度上試著打開人類生活的某種可能性,或者人類精神的某種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是有價值的。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整個社會提供的“場”的不真實,在這個“場”發生的許多事民眾不愿意去相信,或者,已不敢相信。粉飾、獻媚、自說自話,就像一場霧霾在你我身邊漫延。這使得當前“偏激的虛無主義”在作家中大有市場,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欲望化處理,或者在寫作中充滿精神的屈服感,沒有一種讓人性得以站立起來的力量。文學應該向我們展現更多的信念和誠實,從而告別虛假和平庸;面對觸目驚心的心靈衰敗,作家們應該尊靈魂、養心力,積蓄健旺、發達、清明的生命氣息,來為寫作正名。在一個沒有靈魂的社會,進行一種無關痛癢的寫作,不過是在浪費生命而已——要意識到這一點,需要作家們有一種寫作的膽識,真正在文學上精神成人。
在這樣的“場”中,詩人張發軍試圖用手中的筆撥開一個清朗的世界。在感慨于多年生活在仕途圈,已被官場的慣性帶離了心靈的軌跡,信仰和理想漸漸模糊,他痛苦地問自己“我是誰”?是啊!我們奔波在泥濘的路上一直向前時,常常忘了看看自己“滿面塵灰煙火色”的面容,忘了停下來,擦拭蒙在心靈上的浮塵。欣慰的是,當社會、生活或文化都在向前走,被潮流裹挾向前走的時候,總是有些人會停下來彷徨,甚至會往回走。這點,張發軍做到了。
——在他滿懷憂傷的寫下一段一段心靈囈語時。
——在他尋一處僻靜的小飯館,一盤花生米,一盤泡菜,一瓶雪水坊,在香煙的飄散中,一個人慢慢自斟自飲時。
這兩種狀態中的詩人,是真性情的,是不為紅塵左右,靈魂與肉身相統一的,是本真的。猶如一瓶純糧釀造的雪水坊老酒,令人迷醉。
我想說,真正的詩人,是一種精神。
詩人的天職是還鄉。每個人的心中都揣有一個故鄉。從青藏高原到祁連山,隨著祖先的足跡一路匍匐走來,滿懷憂傷和傷痛里,張發軍在天山腳下的沙灣,在大盤雞的香辣和雪水坊的芬芳里,以及牧民的氈房和奶茶的飄香里,找了原鄉。對故鄉溫情與敬意,讓詩人激情澎湃,寫了大量關于故鄉的詩篇。沙灣的蒙古廟、安集海的紅辣椒、哈薩克氈房的手抓肉紛紛入詩。沙灣,已成為詩人靈魂扎根的地方,成為詩人精神的來源地。
我想家了
想念我的家鄉
西部邊陲那個叫沙灣的地方
那是天山腳下
戈壁上生長出的一片綠色
在群山與大漠之間
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神奇地方
是我先人埋骨的地方
我的親人生活的地方
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
我似乎看見了
家鄉人一個個熟悉的身影
在親切地向我招手
哈薩克牧民兄弟的氈房
還有那手抓肉
飄香的奶茶和馕
大盤雞又辣又香
一想起就讓我口水直淌
雪水坊散發的芬芳
讓我止不住一杯又一杯
浪跡天涯的我
總是在夢里聞到家鄉的氣息
鹿角灣自由馳騁的牧場
東大塘迷人的山水風光
瀚海柳浪的原始粗獷
還有沙灣的棉田麥浪
我知道
我該回家了
回到那個叫沙灣的地方
因為我……忘不掉
家鄉的味道
這首《家鄉的味道》,平白直敘,卻意象紛呈,一個有滋有味的有山有水的故鄉呼之欲出。鄉土和大地是中國人的精神基座。而古今中外,最好的文學作品都是對鄉土的敘述。詩人張發軍飽含著對故鄉的熱愛和傷懷,用濃墨重彩一次次讓故鄉的場景出現在筆下,使自己成為一位真正擁有并真實地生活于故鄉的詩人。
魯若迪基在他的《選擇》中寫到——
天空太大了
我只選擇頭頂的一小片
河流太多了
我只選擇故鄉無名的那條
茫茫人海里
我只選擇一個叫阿爭五斤的男人
做我的父親
一個叫車而拉姆的女人
做我的母親
無論走在哪里
我只背靠一座
叫斯布炯的神山
我懷里
只揣著一個叫果流的村莊
“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物之源”,魯若迪基的這種“退守”品質,是努力要為自己的藝術生命從腳下的土地尋得生命的源泉。詩中的事物和情感,都是每日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和情感,魯若迪基不需要再去“想象”它們,更不需要去“虛構”它們,他要做的就是直接去描摹和表現它們。
雷平陽說:“我希望能看見一種以鄉愁為核心的詩歌,它具有秋風和月亮的品質。為了能自由地靠近這種指向盡可能簡單的‘藝術’,我很樂意成為一個繭人,縮身于鄉愁。”鄉愁是地理學的,也是精神學的,所以,偉大的作家往往都熱衷寫自己所熟悉的故鄉。魯迅寫紹興、沈從文寫湘西、莫言寫高密東北鄉、賈平凹寫商州、福克納寫自己那像郵票一樣大小的家鄉——每一個偉大的作家,往往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寫作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如同白洋淀之于孫犁、北京之于老舍,上海之于張愛玲,額爾古納河之于遲子建。沒有精神根據地,盲目地胸懷世界,他所寫下的,不過就是一些公共的感嘆罷了。
從《穿越》到《回歸》。詩人從欲望敘事走向精神重返,我看重這樣的努力。
從俗世中來,到靈魂中去。我想,這正是張發軍這本集子所要表達的精神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