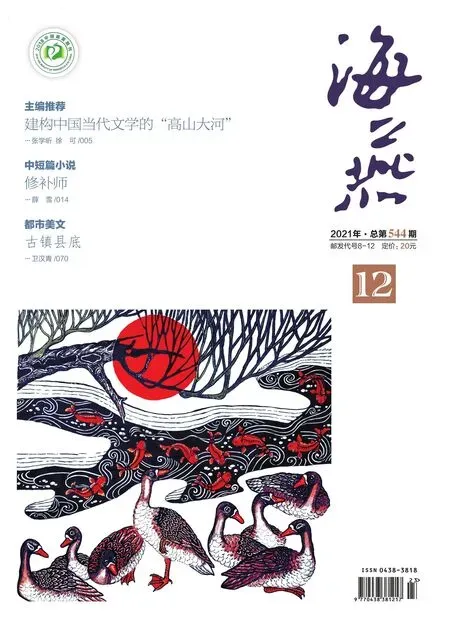門前有條河
王微微
一
近幾年,我時(shí)常會(huì)陷入一種恍惚的混沌的幻象里,陷入一條河流倏忽明滅的蒼茫里,時(shí)常被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動(dòng)攫住氣息難喘。對(duì)于每一條河流,我都是熱愛(ài)的,卻從未有生發(fā)過(guò)如此的憂郁、依戀、疼痛,甚至窒息。
一條寂寂無(wú)名的小溪,環(huán)繞著一個(gè)寂寂無(wú)名的村莊,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幾百年,它從未流進(jìn)文人雅士的視野里,當(dāng)然也流不進(jìn)歷史厚重的記載里。但它一直在我的心里流淌,從未丟失,從未間斷。近幾年,越發(fā)地清晰起來(lái)。
它是飛云江水系北面支流峃作口溪上游的一個(gè)小支流。發(fā)源于石垟林場(chǎng)崇山峻嶺間,穿越奇峰峽谷幽林,一路飛揚(yáng)瀲滟,經(jīng)梧溪、西坑,與發(fā)源于石垟鄉(xiāng)楓樹亭的西坑(溪名,因位于梧溪之西而得名),在西坑屬地匯聚,再流經(jīng)葉岸村、下背村,然后浩浩蕩蕩一路向東南,經(jīng)三板橋、巖門、雙溪、匯溪,最終在小溪口注入飛云江。
流經(jīng)下背村這一段,我們叫它“下背坑”。“坑”,本義是溝壑或地面凹陷處,而在我們的方言俗語(yǔ)里就是河流的意思——坑邊、溪坑、坑兒,坑澗等等,指向都是或大或小的河流。
下背坑寬20米左右,順著山勢(shì)林帶婉蜒,如一條伸長(zhǎng)的手臂,緊抱著略顯蒼涼弱小的村莊。竹林松林灌木林,沿河依山排列的水稻田,田岸下的野花雜草,甚至炊煙農(nóng)具狗吠蟬鳴,都朝向它,朝向它吮吸暢飲,朝向它彎腰致意。那時(shí)候,水清岸綠,河道豐茂幽美,陽(yáng)光穿透樹冠,水流聲劃過(guò)耳際,歡快簡(jiǎn)單而富足。
二
那是乾隆年間的事了。
一條河,撞撞跌跌,從發(fā)源地出發(fā),翻山越嶺,剛好在它最健碩的年齡,遇見(jiàn)一座柔美的村莊,于是,它落在這清山秀水的纏綿里,再也繞不過(guò)去了。
王氏七兄弟,為了逃離生活的苦難,拖家?guī)Э冢瑥母=ü盘镆宦钒仙缴嫠瑲v經(jīng)磨難,來(lái)到了這人跡罕見(jiàn),林木蔥郁,溝壑幽深,清泉激湍的地方,并最終在這里定居了下來(lái)。從此,西坑畬族鎮(zhèn)的地圖上多了一個(gè)叫“下背”的自然村,飛云江支流的細(xì)枝末節(jié)上,有了一條叫“下背坑”的河流。
聽爺爺講,那時(shí)候河流兩岸樹林灌木高大森茂,河流狹窄處,拽著枝條,一晃蕩,就可以蕩到河的那一頭。或許,祖公們相中的就是這一條河岸的清幽寧?kù)o,超然塵外。他們?cè)谶@里定居了下來(lái),開始開山造田,補(bǔ)充耕地,他們種植水稻紅薯棉花,也種植藍(lán)草煙草蓖麻。他們將煙草晾曬切成上好的煙絲,自用也拿來(lái)交換,將藍(lán)草加工成靛青,挑到碼頭,沿著水路,一簍一簍遠(yuǎn)銷溫嶺、福建等地,換成銀元,再回來(lái)購(gòu)田置地。農(nóng)民是靠雙手吃飯的,因?yàn)榍趧冢又值苕ㄦ矆F(tuán)結(jié)合心,一大家子相親相愛(ài),小日子很快就安穩(wěn)踏實(shí)起來(lái)。
那還是個(gè)缺衣少吃的年代,許多窮人家“窮得揭不開鍋”的時(shí)候,就去砍燒火柴,挑到大戶人家去兌換點(diǎn)大米,或去大戶人家?guī)凸ぃ跃徑饽暝吗嚮摹R粨?dān)大秤100斤的燒火柴,可以換一斗米,一天的工錢也是一斗米。據(jù)說(shuō),其他地方的大戶人家量米時(shí),總是把米斗刮得平平的,而祖公們不計(jì)這些小頭,雖然他們不是大戶人家,也僅是剛夠溫飽而已,但看到比自己窮的人,總是盡量多給一點(diǎn),米在斗上堆得飽滿,有時(shí)甚至另外再加一大把番薯絲。慢慢地,一傳二,二傳三,許多人慕名而來(lái),幫工的,交換的,小村莊越來(lái)越熱鬧了起來(lái)。
下背村村口有一株大香樟樹,底下有一塊石頭,深陷在香樟樹盤錯(cuò)的樹根里,略略凸起,像門檻一樣,攔擋在路中間,人們來(lái)來(lái)往往時(shí),都要抬腳從石頭上跨過(guò)去。有一年,一位挑燒火柴的農(nóng)人向祖公們提了個(gè)建議,說(shuō)這塊石頭居路正中,你們自己來(lái)來(lái)往往已經(jīng)習(xí)慣了,其他人挑著東西,每每都要很費(fèi)力氣地抬腳跨過(guò)這塊石頭,何不把它挖掉,方便來(lái)往行人行走,這也是你們王家人積德積善。
祖公們覺(jué)得他說(shuō)的有道理,就把那塊石頭挖了。就在當(dāng)年,一場(chǎng)史無(wú)前例的大水差點(diǎn)把村莊淹沒(méi)了,幾天幾夜,山洪退去后,所有菜地稻田種植園全部被毀,山上泥土被沖刷得干干凈凈。從此往后,下背村災(zāi)年連連,洪水瘟疫,沒(méi)有停息。據(jù)說(shuō),那人是鄰村請(qǐng)來(lái)的一位陰陽(yáng)先生,鄰村人看到下背人把日子過(guò)得“芝麻開花——節(jié)節(jié)高”,認(rèn)為自己的風(fēng)水都被下背村拉走了,于是,心生詭計(jì)。而那塊石頭,是村莊的風(fēng)水石,等祖公們醒悟過(guò)來(lái),趕緊把石頭按回原來(lái)的位置……200多年過(guò)去了,這事件口口相傳,早已經(jīng)無(wú)從查證。但可以證實(shí)的是,遷居到下背村的王氏祖先,經(jīng)過(guò)200多年的繁衍生息,并沒(méi)有發(fā)展壯大,當(dāng)年七兄弟,病的病,死的死,外遷的外遷,留下的幾份,子孫后人們各立家門。到1995年下背村移民時(shí),加上葉姓金姓,還不到100人。
三
這是一條河流的前身。
我對(duì)一條河流的最初記憶,應(yīng)該是剛剛有記憶的年齡吧,五歲?六歲?或者七歲?晚飯后,大人牽著小人的手,拎著一個(gè)小水桶,水桶里放著一個(gè)寫著“為人民服務(wù)”的搪瓷杯和一支手電筒,搪瓷杯是父親退伍時(shí)發(fā)的,洋氣得很,一般人家沒(méi)有,手電筒也是那時(shí)候最珍貴的小電器,有三節(jié)電池的,很多人家也沒(méi)有。
拿著手電筒干嘛?當(dāng)然是去河里抓螃蟹和蝦,走夜路有星月罩著,我們的視力是很好的,我們一直生活在燭光煤油燈的年代,我們對(duì)光是很敏感的。
我們坐在河邊等星星等月亮,等天色昏暗下來(lái)。天地開始混沌的時(shí)候,河蟹螺絲小蝦就分不清天南地北了。我們只要將腳丫子伸進(jìn)水里,一動(dòng)不動(dòng),不一會(huì)兒,就有小魚小蝦跑過(guò)來(lái)親你吻你撫摸你,有趣得很。老螃蟹駝著紅褐色的背蓋橫行,蝦弓著背,捋著胡須,在淺灘上閑庭信步,螺絲們伸吐著舌頭,大個(gè)幫小個(gè),在巖石上水草間疊羅漢,星星在眨眼,溪水在輕唱,風(fēng)順著山溝呼呼地竄下來(lái),在我們的衣衫里頭鉆來(lái)竄去捉迷藏,大人們卸下一天的疲倦,眉頭舒展,陪著孩子們摸螺抓魚潑水嬉戲,在水里忘情。
小魚在水里竄來(lái)竄去,跑得飛快,是抓不住的。螃蟹長(zhǎng)著兩個(gè)大鉗子,耀武揚(yáng)威,小人們也是不敢去觸碰它的,螺螄緊緊吸附在巖石的邊緣上或底部,一動(dòng)不動(dòng),最容易抓。而最有趣的是抓小蝦,你抓它的時(shí)候,它不是往前跑,而是倒退著逃跑的。父親教我,抓蝦就是打太極,要悠著來(lái),先把左手弓成弧形,擋在蝦屁股后面,然后把右手放在蝦前面,它只看前不顧后的,駝著背,一弓一弓防備著倒退著,一下子就退到你左手的掌心里。哎,小蝦米嘛,玩不過(guò)人類的。
再長(zhǎng)大一點(diǎn),就是上學(xué)的年齡了。每天都要跨過(guò)這條小河,到西坑鎮(zhèn)去上學(xué)。記憶里的河流是情緒的,我能否上學(xué)完全取決于它的心情,它溫順的時(shí)候,我們可以在它上面輕松地來(lái)來(lái)往往,它哭泣發(fā)脾氣的時(shí)候,我們就整夜整夜地提心吊膽。
那個(gè)小木橋,從這頭到那頭分架三條,最盡頭的那一條小木橋,基本上是發(fā)一次洪水,就被沖走一次。村里的叔伯們呼三吆五,幾天時(shí)間,新的木橋又架上了,如此反復(fù),越到后面,木橋越小,被沖走的次數(shù)也就越多。記得有一次,好幾個(gè)月都是在零亂堆疊的石頭上跳著過(guò)河的,幸好不是河流的中間段。我想,可能是砍得多了,村里再也沒(méi)有這么大的可用作木橋的樹了,也或者是砍得煩了,隨意就近砍一根松樹就架上去了。所以,最后那一段小木橋越來(lái)越窄,橋面也是越來(lái)越不講究,時(shí)常連樹皮都沒(méi)有削干凈,而走上去的時(shí)候,步子倒是得越來(lái)越小心越來(lái)越講究了。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那是暮春時(shí)的河流,兩岸那些開得筋疲力竭的花開始零落,它們飄飄搖搖,栽落到草叢里、淺灘碎石上,隨著流水的漲退悄然退場(chǎng),有的在水洼旋渦處,稍作停息,小憩那即將隨波逐流的靈魂。少女時(shí)期的我,時(shí)常捧一本書,坐在河邊看著它們發(fā)呆。落花有些還是完整的,只是少了顏色,多了蒼白,有些則已支離破碎,瘦骨伶仃,它們?cè)谒菪郎u里一聲一聲的嘆息,也輕輕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流水將會(huì)把它們載向哪里?它們將會(huì)在哪一截流水里下沉、淹沒(méi)、幻化、重生?我們將會(huì)在哪一年的春天相逢重遇?
那些無(wú)數(shù)的看不見(jiàn)的小生命,被河水收容著,這些生命,從水里開始,又從水里結(jié)束,循環(huán)往復(fù),這是自然的輪回,也是人類的輪回?
水一直在往前走,水邊上的人,也沿著水流的方向,一直往前走,村莊是不動(dòng)的。她看水,比如看自己,一滴一滴匯聚成澗成溪成江河湖海,接受它的沉潛干枯,也接受它的激流澎湃,它滋潤(rùn)你也侵蝕你,在河邊居住久了,把自己一點(diǎn)一點(diǎn)交付給它,不知不覺(jué)也成為河流的一部分。
與它相處的20多年里,我早已習(xí)慣于它的情緒語(yǔ)言,喜歡它偶爾的剛烈暴躁,更喜歡它平常日子的低柔深情,我也像那條小木橋一樣,任由剛烈或低柔反復(fù)拍敲捶打,心里永遠(yuǎn)盛著滿滿的感動(dòng)。不知道哪一位哲人說(shuō)過(guò),人道就是如水的天命。下背坑,那就是我的天命,生命的原初。
四
暮春之后,夏就來(lái)了。
七月流火,那個(gè)山里干農(nóng)活回來(lái)的男人,身上臉上頭發(fā)上掛滿了草葉與雜屑,他多像山林間用力生長(zhǎng)的一棵樹啊!他正大步跨過(guò)小橋,撲通一聲跳進(jìn)河里暢游了起來(lái)——村子里的男人婦女們,白天在山上田里砍柴吆牛開山種地,傍晚回家時(shí)順帶背回一捆燒火柴或一捆喂兔子的草,如果是炎夏,就順帶跳進(jìn)河里清洗清洗再回去。一位正在河邊洗衣服的女子,一件衣服不小心被調(diào)皮的流水沖走了,“呀”,她輕輕地叫了一聲,他三下兩下游過(guò)去,撿起衣服扔給她。晚飯時(shí),男人家里響起了河?xùn)|獅吼:你敢?你敢?往后你給我離那個(gè)狐貍精遠(yuǎn)點(diǎn)!
男人沉默不語(yǔ),河流沉默不語(yǔ),“狐貍精”沉默不語(yǔ)。
但河流曉得,一個(gè)村莊的善良、簡(jiǎn)單與辛酸,他們有愛(ài)就用力去愛(ài),有恨就用力去恨,有肉就大口大口地吃,有醋就仰起脖子一飲而盡。愛(ài)恨可以是蓬頭垢面的村婦,可以是干凈得體的賢妻,也可以是體態(tài)風(fēng)韻的“狐貍精”。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這是《詩(shī)經(jīng)》里最美麗最浪漫最清明的一條河流,人間歲月,縱使衣食艱辛,亦可春思浪漫。什么事也沒(méi)有,又仿佛什么事都有,這些無(wú)因無(wú)由的,從水里一躍而出的心思,唯美又清和,這是人世間的可愛(ài),亦是人世間的酸楚。
有一次暴雨山洪,小橋被淹沒(méi)了好幾天。第一天,從山那邊來(lái)了幾位水淋淋氣噓噓的男子,說(shuō)他們是上游某某村莊的,村里一位壯年男人被山洪沖走了,他們沿河一直在找,如果有看到,請(qǐng)幫忙,請(qǐng)給他們捎信。村里幾位熱心人,馬上陪同他們?cè)谙卤晨舆@一段來(lái)回打撈尋找,直到第三天洪水退去,落出半橋,橋上隱隱掛著一個(gè)人,被洪水漲泡的發(fā)白。村人吆喝一聲,第一時(shí)間拿上麻繩、竹桿等,手拉手跳入河里將死者打撈上岸,取舊衣物蓋之。這位死者的親人來(lái)了以后,千恩萬(wàn)謝,跪在河邊嚎啕大哭。
這件事當(dāng)時(shí)給我極大的恐懼,也給我極大的震憾,至今記憶猶新。恐懼是因?yàn)樾⌒∧昙o(jì)的我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尸體,一個(gè)被洪水石頭沖撞得傷痕累累的尸體,震憾是因?yàn)榇謇锬切┦宀畟兒敛华q豫跳進(jìn)激流去拖尸的樣子,是因?yàn)槟切┍瘣碛^的哭泣。水江邊的人,跳河救人是時(shí)有的事,除了膽大藝高水性好,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熱血與人性。是的,人性。
上善若水。河流,從《詩(shī)經(jīng)》開始,就是一個(gè)村莊的全部柔情,也是人世間的全部柔情。一個(gè)沒(méi)有河流流經(jīng)的村莊,看不到太陽(yáng)月亮云霧山巒水里嬉戲的身影,聽不到溪魚蝦米水中搶食吧吧唧唧的聲音,感受不到“關(guān)關(guān)睢鳩,在河之洲。窈窈淑女,君子好逑”的唯美意境,還能稱其為村莊嗎?什么是“一溪流水秀空靈,云自無(wú)心水自閑”?什么是“誰(shuí)道人生無(wú)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fā)唱黃雞”?你看,這就是河流,有河流,才有人世間的悲苦歡喜,才有人類的文明,才有靈魂的詩(shī)意,才有近在眼前的遠(yuǎn)方。
水是生命之源,亦是文明起源,自古以來(lái),人類逐水而居,從古中國(guó)文明與長(zhǎng)江黃河,古埃及文明與尼羅可,古印度文明與恒河,古巴比倫文明與兩河,甚至塞納河之于法國(guó),泰晤士河之于英國(guó),黃浦江之于上海,錢塘江之于杭州,甌江之于溫州,當(dāng)然,還有“下背坑”之于下背村,都印證了這一點(diǎn)。
沒(méi)有下背坑,就沒(méi)有王氏祖先的遷徙定居,就不會(huì)有小橋流水人家,就不會(huì)有煙草靛青苧麻,就不會(huì)有順著流水漂走的衣衫,就不會(huì)有河?xùn)|獅吼狐貍精,就不會(huì)有一個(gè)沉沒(méi)的村莊,就不會(huì)有我和我看到的悲歡與離合。
五
是的,村莊沉沒(méi)了,小橋流水消失了。
飛云江上游支流多,沿河的小村莊多,春夏暴雨洪水也多。支流水系皆盤纏在高山深谷之中,一個(gè)村到另外一個(gè)村,幾里長(zhǎng)的路,有時(shí)就要涉水好幾次,石拱橋、木橋、碇步,甚至是河里幾塊天然的不規(guī)則的大石頭墊起來(lái)的“橋”,人們?cè)谏厦嫣S著走,水在腳下歡快地流。
如今,這景致越來(lái)越少了。農(nóng)村道路四通八達(dá),生活水平也是節(jié)節(jié)攀升,原來(lái)的窮山惡水,變成了現(xiàn)在的青山綠水。旅游業(yè)發(fā)展蓬勃,小水電更是如雨后春筍般建起來(lái),它們給一個(gè)地方帶來(lái)社會(huì)效益與經(jīng)濟(jì)效益的同時(shí),也極大地改變了當(dāng)?shù)氐淖匀痪坝^。
一條條河流再也不能奔跑歡唱,它們被層層攔河筑壩,它們的手腳肢體被截了再截,堵了再堵,它們的肌膚筋骨老了又老,千山萬(wàn)壑里,它們不是肌黃枯瘦旱渴荒涼,就是臃腫膨脹淹沒(méi)窒息。它們?cè)谌f(wàn)家燈火的輝煌里,無(wú)聲無(wú)息地倒下了。我心疼它們。
擴(kuò)張的水庫(kù)代替了清澈秀美的溪流,水位下降后裸露的黃土石窟和五顏六色的腐植垃圾,灼人眼目。再也走不進(jìn)看不到河流兩岸細(xì)碎的小花,茂盛的水草,以及沿水草而息的小魚小螺小蝦。是的,峽谷深山,深潭淺碧,風(fēng)過(guò)處,水波粼粼,許多人愛(ài)慕它現(xiàn)在的蓄滿水時(shí)的容顏,贊美它為人類的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發(fā)光發(fā)電,卻看不到它的阻滯郁悶的內(nèi)傷,看不到水位回落后的傷痕累累,更忘了它原先的健康清秀的模樣。
我對(duì)“下背坑”是有特殊的感情的,高山流水,日日清唱,它就在我家門前,每天早晨推開窗,它就像儀式一樣出現(xiàn),接納我,滋養(yǎng)我,溫暖我。這儀式,仿佛俗常日子里的修行。而那時(shí),我不能洞悉全部,直至,星月浮云,時(shí)間如流水。
20多年了,它沉潛了下來(lái),往日的清唱,變成了沉默的思想。它包容了這個(gè)小村莊200多年的大是大非和雞毛蒜皮。它也在我的內(nèi)心沉潛了下來(lái)。我不用每天跨過(guò)小橋去上學(xué),但我時(shí)常跨過(guò)這條河,追尋我曾經(jīng)的童年和少年,追尋那些逝去的親人,我仿佛看到他們?cè)诤舆厰嚢柚沂旌椭迩啵逑戳罆裰鵁煵萜r麻葉,清洗那一雙被靛青染藍(lán)的雙手,清洗著河流邊上那一段最清寧安穩(wěn)的日子。
這是我生命的河流,承載著歲月的全部。無(wú)戒備,不申訴,那緘默無(wú)聲里,一定藏著一條河流的古老神靈。我搭乘著它,盡數(shù)這途中浮世風(fēng)景,無(wú)論是深山峽谷,卵石沙灘,它總能流出一條最深的美色。它平凡得無(wú)從著筆,也美麗得無(wú)從著筆。
每一條河流都不年輕不容易,甚至那些雨后山澗路邊溝渠,為了在世間明明白白走一遭,誰(shuí)知道它們?cè)诘叵箩j釀了多久?要冒多大的險(xiǎn)遭多大的苦難?我們對(duì)它永遠(yuǎn)只有汲取與消化,我們不屑去體會(huì)它在人間消失的情感事實(shí)。
我在一條河流的影子里,看清了所有的河流。
有多少人像我一樣,享受著它的現(xiàn)在,卻又念想心疼它的過(guò)往?我不知道。對(duì)于一條河流來(lái)講,轉(zhuǎn)身變成水庫(kù),這樣的狀態(tài)好還是不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用什么樣的價(jià)值來(lái)評(píng)判,我也不知道,我該以怎樣的一種方式面對(duì)它。
幾十年過(guò)去了,我還在這里來(lái)來(lái)回回,我把我的童年交付于它,我的少年青年交付于它,直至現(xiàn)在。作為河流的它,早已消失在實(shí)際意義的地理地圖上了,而我依然在它的前面來(lái)來(lái)往往,我并不感到它消失了,它在我心里一直流淌著,它的貧瘠與富有、它的狹隘與寬厚,它的蒼涼肅殺與清音繞耳,我坐在昏黃混濁的塵世里,任由它掀起我內(nèi)心的烽火狼煙與萬(wàn)般柔情,是那么無(wú)奈與矛盾。
唉,我不能過(guò)多地描述現(xiàn)在的它。
歲月催我衰老,但我內(nèi)心角落仍藏著一個(gè)多愁善感的少女,藏著一條清明通達(dá)的河流,它一直柔軟在我的胸腔,它是我永遠(yuǎn)的文學(xué),是我溫涼的淚。
六
文字寫到情緒高潮的時(shí)候,心里傾訴的欲望也像一條河流一樣,汩汩地流了出來(lái)。
但是,就是這一條小小的河流,卻讓我感到筆力不濟(jì),找不到準(zhǔn)確的詞匯去描述,去概括它蘊(yùn)含的精神,進(jìn)而感到內(nèi)心的破敗不堪。但還是要寫,只有寫,才能傾聽到它的掙扎,才能找到自己內(nèi)心的平衡。
河流養(yǎng)育著我們的生活,也養(yǎng)育著我們生存的語(yǔ)言語(yǔ)境。我們談?wù)撎斓氐年幥鐖A缺,談?wù)撐骞入s糧的播種收獲,談?wù)摬菽緲s枯,昆蟲發(fā)蟄、候鳥往來(lái)的時(shí)序,談?wù)撀萁z的屁股剪多少,煮起來(lái)的時(shí)候更好吮吸一點(diǎn),談?wù)摵永锬囊环N魚魚刺更少更長(zhǎng)膘,談?wù)擉π肥裁醇竟?jié)肥怎么腌腌多久恰恰好,談?wù)撐r為什么倒退著走人為什么往高處爬,談?wù)撚行┫x子為什么與樹葉長(zhǎng)得那么像以后人類會(huì)不會(huì)也變成這樣,談?wù)撎焯玫鬲z的距離人鬼狐仙的差距,從而告誡自己,要好好做人,否則來(lái)生就會(huì)墜入地獄淪為魔鬼,談?wù)撨h(yuǎn)方到底有多美多遠(yuǎn),當(dāng)然,僅僅是遠(yuǎn)方,與詩(shī)歌無(wú)關(guān)。
我們的語(yǔ)言只有泥土味草木味人情味,沒(méi)有商業(yè)味金屬味。吃了嗎?喝了嗎?要幫忙不?我們隨意地問(wèn)候輕松地聊天,輕聲細(xì)語(yǔ)敞開通透,沒(méi)有負(fù)重心,沒(méi)有敏感脆弱的神經(jīng),沒(méi)有居高臨下的冷漠。不怕自己的笨嘴笨舌被人取笑,也不怕自己講錯(cuò)話不小心傷害到了誰(shuí),或傷害到了自己。
我對(duì)這種不設(shè)防的簡(jiǎn)單充滿了依戀。溪流聲在耳旁叮叮當(dāng)當(dāng),嘩嘩啦啦,偶爾怒吼一聲,隨即回歸清和。這些簡(jiǎn)樸自然的聲音,一直珍藏在我的內(nèi)心世界里,那是我最珍貴的文學(xué),幾乎沒(méi)有敗筆。
“草木管時(shí)令,鳥鳴報(bào)農(nóng)時(shí)”,那是生態(tài),沒(méi)有被破壞的自然生態(tài)。村莊是河流的一部分,村莊里的人也是河流的一部分,我們都是河流里的一滴水,清清爽爽,簡(jiǎn)簡(jiǎn)單單。
而離開一條河流,走進(jìn)城市,走向生命的繁華喧囂處,這漫長(zhǎng)的生命之旅,卻把“我”變得復(fù)雜了。
生態(tài)與文明,生活與儀式,或許,我們是可以減負(fù)前行的。
我想念門前那條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