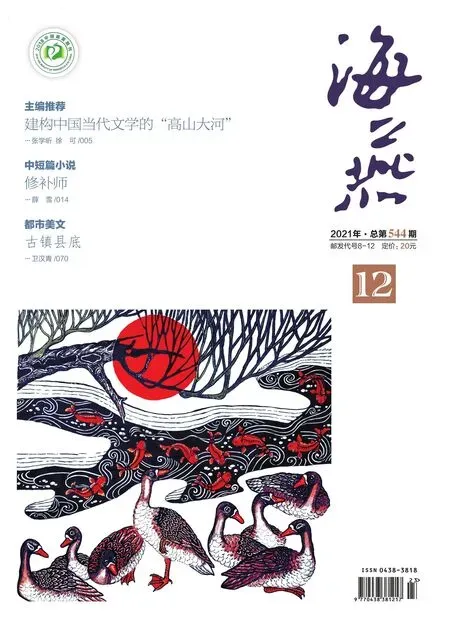偶然的桃花
高詠志
夢見父親
記不得是第多少回了
我夢見父親
他坐在那兒
默默地吸著旱煙
每一次
我都被他劇烈的咳嗽
震醒
這個在我夢里生活的人
就這么坐著
不說話
他的藍布衫
明顯有些舊
胡子也老長時間沒修了
我已不能盡孝
快二十年了
父親
弓著背,蹲坐在
我黑夜的腹內(nèi)
我多想把他生下來
將他一點一點
養(yǎng)大
夜歌
深夜
一個人坐在房間里
獨享滿滿一屋子的黑
我感覺我像一塊糖
在慢慢融化
我明明知道
這一屋子的黑里面
其實什么都沒有
可我還是感到
說不出的充盈
我敬畏黑夜
它是夢的腹地
它告訴我
有時候只有閉上眼睛
才能看得更遠
從母親的子宮
到大地的子宮
是黑暗孕育和收留了我們
而所謂人生
不過是我們路過的一段光明
端水的女人
在醫(yī)院走廊里
我看見一個女人
雙手端著
滿滿一碗水
滿得都快溢出來了
她小心地
向前挪著腳步
看她緊繃的表情
我都跟著緊張
我在想
她為什么要
端滿滿一碗水呢
而且那樣子
一點也不好看
偶然的桃花
我走進桃園
那些桃花
一下子全開了
它們像是等了我好久
就像心愛的女人
在我推開門的剎那
忽然亮出這么多
驚喜
寫到這里
我有點猶疑
或者這些
不過是我的幻覺
事實上
那些桃花常常在
我們想不到的時候
已經(jīng)一朵朵開好
而且
它們也不會像女人
它們是桃花
所以才開得那么好
陌生的風景
凌晨2點,我突然醒來
墻上的石英鐘里
闖進了一匹馬
有節(jié)奏的蹄聲
細碎而激越
電源上的指示燈
異常地閃
幾乎照亮了整個房間
睡前它還微弱得
可以忽略不計
外面忽地起了一陣風
沙沙地打著旋兒
把一個破舊的塑料袋
貼在窗玻璃上
抖動著
數(shù)公里外一列火車
疲倦而興奮地鳴叫
帶著巨大的震動停靠在
耳朵的隧道里
我仿佛來到了另一個世界
在雨夜深處
他不敢入眠
怕睡著了
結(jié)出穗子
打著燈籠闖進自己的夢里
他撞見一朵花
解開了懷春的紐扣
他像猶疑的鐘擺
在白天與白天的黑色夾道
拿不定主意
風一直在勸那棵旁觀的樹離開
樹也想走
但它陷得太深了
正好夠
我身體里的鐵
正好夠
打一把鍬
一把鍬
正好夠
挖一眼井
一眼井
正好夠
養(yǎng)一棵樹
一棵樹
正好夠一場
根深葉茂的愛情
槐花與小販
路旁
一樹淡紫的槐花
開得正好
賣菜的小販
推車過來
放慢了她的腳步
沒走多遠
忽然
她停下車
徑直走向樹下
就像被槐花的香氣
給拉回來的
小販嗅著那些花
摘下一朵
放進嘴里
她睜大眼睛
仿佛第一次嘗到生活
還有這樣一種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