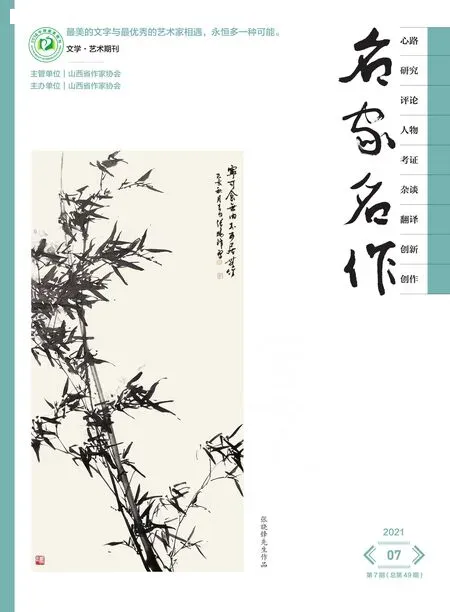深耕文化沃土 筆繪心靈圖像——談王曉明《所羅門的瓶子》之方法論
楊 妍
王曉明是一位帶有較為強烈的個性意識的批評家,著有《沙汀艾蕪的小說世界》《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所羅門的瓶子》等。其批評文字雖然不具備出色的思辨理性意義,卻令人讀來酣暢又親和,有值得品味的空間。批評文集《所羅門的瓶子》于2014年11月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舊文新版,將王曉明20世紀80年代所撰寫的文章集中帶到新世紀讀者面前。作為運用文化心理批評研究方法較為成功的范例,此集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一、從魯樞元到王曉明
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發展流動的長河中,批評者自我意識的回歸是一個突出的轉變特征,批評標準和價值判斷中的許多集體因素也為個人化因素所替代。在此前,注重外部因素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學理念占據主導地位,社會歷史批評方法是主要方法。本體論的出現將人們的目光引向文學內部,呼喚批評家們關注作品內部因素。
魯樞元站在威廉·馮特心理學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理論的肩膀上,創造了文學心理學理論。文學心理學理論的誕生,打開了從心理世界出發去考察文學作品的新路徑,建立起作家與作品的聯系,展示了作家內在精神世界的圖景。在此影響下,一批從心理學角度研究作家作品的成果接連涌現,王曉明《所羅門的瓶子》便是其一。但王曉明有所發展,將心理批評引向了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批評是以心理為視角,主要運用現代心理學、文藝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作家作品及讀者接受的內涵進行深入探析和評論的模式。”王曉明注重人的意識結構和心靈的結構特征,將文化心理批評方法用于現代文學,考察了魯迅、茅盾、張天翼等作家的精神世界。孫郁指出,這種批評方法的思路其實更接近于思想批評。
黃子平總結王曉明的研究是“生平文本”和“作品文本”之間的互文。在王曉明看來,作家的傳記材料并不絕對可靠,作品可彌補作家傳記的局限性,從作品入手推測作家的心態是相對可靠的選擇。“要分析知識分子的心態,總得由具體的現象入手,而在文學研究領域里,我能夠用來作分析對象的,就只有作家。”
二、心理世界的潛流與漩渦
王曉明論述作家的角度是獨特的。他不斷探索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所發揮的主體性,注意作家試圖掩蓋的東西,用深潛的姿勢追蹤和描繪作家內心世界的旋渦與暗流,總結作家的認識習慣,把握其創作心理的流變。
(一)創作心理的探析
王曉明認為,少年遭遇家道中落,飽嘗人情冷暖,聽聞腌漬眼睛的怖事等使魯迅形成偏重陰暗面的認識習慣,這是造成其著力深挖民族精神缺陷的深層原因。“感受習慣和邏輯判斷的分歧,對病態精神現象和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的認識分歧,最終都造成了他整個理性世界的分裂。”在獨行的道路上,魯迅的內心始終充斥著深廣的孤獨,深惡與達觀互相補充,處處接近絕望,又無不反抗絕望。通過追溯,王曉明一定程度上還圣人魯迅為真人。
探索茅盾的生平,可瞥見其始終熱衷政治生活的內心。他的靈魂,一部分是指向政治的熱情,一部分閃爍著敏感的文學天賦。《幻滅》和《動搖》是茅盾被社會浪潮擊打所打造出來的“自救之舟”,《虹》和《三人行》更表明他無法抑制自己關心政治的那一半靈魂。兩個靈魂的斗爭,使茅盾在文學觀念、文學創作上都顯示出分裂,以至于茅盾在之后的創作過程中,即使妄圖從抽象命題出發,非理性因素也不覺占據主導地位。
張天翼自小善模仿,具備快速抓住對象突出特征的能力,而王曉明認為張天翼的局限恰在于此。他習慣將一切都交代清楚,過分偏重邏輯,將人物心理變化梳理明白,缺少一絲朦朧與深沉的意味。在刻畫人物方面,張天翼仍像揭示理智思維那樣采用突出主導傾向的方法,不免表現出單一和抽象的弊病。因此,張天翼總傾向于將“復雜的精神現象還原到一個最簡單的內核中去”,片面強調人物的某一種心理品質,這是現代作家在認識論上的幼稚表現。
深入張賢亮的內心,王曉明則從其作品敘事人的姿態入手。1980年后,張賢亮拋棄他擅長的傳統敘事方式,制造了一個名為章永璘的敘事人。他持續關注敘事人的背叛行為,描繪生活壓迫造成的精神病態。衣食足而知榮辱,當溫飽還無法得到滿足,靈魂和道德就成為無法被顧及的存在,章永璘和張賢亮皆如此。張賢亮贏得了生存的勝利,卻付出了心理變形的代價。他企圖從審美的目光去回望過往,卻被道德的鐐銬困住手腳。王曉明認為,感受記憶和理智意圖的矛盾,是張賢亮選擇這種獨特敘事方式的決定性因素。
在對地理、歷史著作的閱讀中,王曉明得出,“不自覺的忍讓和自卑情感”和“倔強執拗的反抗之心”深扎苗族人民心中,這樣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質也在沈從文的文字中暗自流淌。王曉明將沈從文定義為“湘西社會的逆子”:筆下眷戀湘西,卻安居城市;嘲諷教授先生們,自己卻也成為一名教授。“在某種意義上,他對昔日湘西的整個向往之情,都是被他與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觸所激引起來的。當他決意用現代小說的形式來抒發這種感情的時候,他就已經注定要陷入那行為和情感之間的矛盾了。”
(二)個案與普遍的交融
在對作家個體的深入探求中,王曉明之筆并不囿于作家個體的表現,而是融入大的歷史背景,推論出群體的普遍文化心理,這不僅增加了論證的可信度和容納空間,也深化了批評文章的內涵。
“但同時,張賢亮的小說創作又使我感到擔憂,中國作家要在對內心情感的懺悔式的解剖中達到真正深入的程度,恐怕先得排除掉那種完全只依據理性觀念去解釋的沖動。”談論張賢亮時,王曉明慨嘆中國知識分子苦難之深重。中國作家遭受苦痛,生發出外向的憂患意識,也生發出內省的懺悔意識。要想從苦痛中恢復,作家們必須釋放出痛苦的感情,從生活的遭遇去解釋和辯護,以求得精神的平衡。
中國新文學是反思的文學,如何看待知識分子是重要問題。王曉明由對張賢亮寫作方式和理念的分析,上升到中國作家群體面對苦痛的寫作出路問題,這蘊含著他對20世紀文人群體深切的人文關懷。
三、特點與局限性
王曉明的文章多是逐層深化的結構。他較完整地梳理作家創作歷程的心理變化時,仿佛在一層層剝下洋蔥的表皮和肉瓣。“層層剖析對象世界的話語方式,不僅在感知的細膩上讓人贊嘆不已,更主要的是靈魂解析過程的那份嚴峻和冷靜”。面對批評對象,他手握解剖的手術刀,不緊不慢,獨樂其中。
于《讀〈沈從文文集〉隨想》篇尾,王曉明坦言自己試圖分析作家內心世界面臨的較大的研究困境。他以自我經驗激活文本,注重個人閱讀感受。但閱讀感受是一種主觀常新的東西,若要盡力顯得客觀一些,確是極為困難的事情。當然,歸根結底,所有的文學批評都可以說是一家之言,理解和剖析本就是在尊重客觀事實基礎上的能動性表達。
王曉明擁有較強的審美能力,我們應當肯定他體味和思考精神價值的深刻性。然過于注重那些非確切、非理性的因素,也側面表明他對確切因素、理性因素一定程度的忽略,從而使探析略顯狹窄。孫郁指出:“藝術其實與人的心靈有著復雜的、非線性因果的聯系。如,談論張賢亮的時候,如果單純地把作家某種心態的畸形與藝術的畸形等同起來,在方法論上就顯得簡單化。”
四、結語
王曉明打開了所羅門的瓶子,但從瓶口中涌出來的不是魔鬼,是豐富靈魂的無數個心靈的側面。“先分析作品,再一步步推論出作者的心態,乃至普遍的文化心理”,這種思路是對傳統演繹式方法的顛覆,充分呈現批評者自我觀念,也融入了歷史的考察。王曉明推崇批評家與文本和文本中的對象融合互滲的批評方式,其批評和作家的文本與心靈構成了真正的對話關系。為作家的心靈畫像,挖掘作家的心靈困苦,直面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弱點,王曉明提供了一種內外結合的文化心理研究范例。用孫郁的話來說,就是“以理論家的思維方式,完成了散文家式的雕塑人物的過程”。三十多年前的批評曾引起關注與爭議,如今雖時代變遷,卻尚有參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