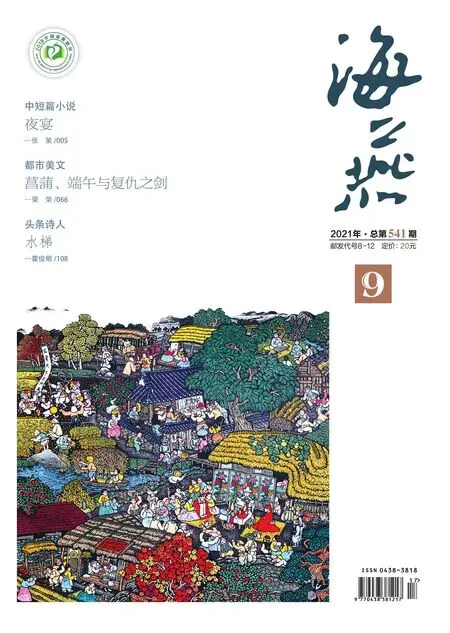三疊
文 吳少東
與孔子書——《與子書三疊》之一
四月將至,春水東流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晚生雖未能聆聽教誨
但熟讀夫子留傳的論語。
兩千五百年過去
我們依舊逃不脫仁義禮智信。
我們依舊缺失這五味苦藥
那年在曲阜
手撫你植下的檜樹
如同觸碰指引的巨臂,
隨你十四載,周游列國。
壯年之后,我克己復禮
擇善者而從之,思無邪
寫詩,樂山又樂水。
卻對時局與人心的叵測,
常感困惑。兼濟的沸水
幾近止息,如臨淵履冰。
我也曾如你一般,在一座
城郭前迷失過,
累累若喪家之犬。
但朝聞道,夕死可矣。
你我都是理想主義的大個子
而今,年知天命,我信天
信命,每日心中仍念誦——
“我欲仁,斯仁至矣!”
與莊子書——《與子書三疊》之二
愈發(fā)愛先生的瑰麗之論,
在對立中消弭,統(tǒng)一
三十歲前
如你所言,我懷鯤鵬之志
煉翅,飛翔,拿天邊云
沖擊九萬里的寬度
三十歲后
附同你與惠子的濠梁之辯
收斂疲憊的翅膀,樂做
一片水域里游動的鰷魚
而現在
我的夢越來越輕
卸卻了背負的泰山
立在枝頭,為一枚蝴蝶
忘我。忘成心、機心與分別心
此生,外儒內莊,自然而然
與墨子書——《與子書三疊》之三
在非儒即墨的先秦,
我定會陷入兩難。
本與標,動與止,是與非
選邊站隊,我必隨先生
同為“北方之鄙人”
我敬重奔走列國的短褐草鞋
擯棄坐而論道,身體力行。
先生巨子,兼愛天下人,
敢與魯班一起掄斧拒敵,
阻止以利刃斬斷王旗
二十一國山水縱橫,
哪有什么儒俠
只有死不旋踵的墨俠。
身懷匠人絕技的你,終生
只為打造一個堅固的義字
你是非攻的戰(zhàn)士。
和平主義的述而并作者。
我幻想成為城市獵人久矣,
卻至今仍是待沽的儒生。
離你2400年圈禁的獅子
中秋夜與兒對弈——《中年三疊》之一
返校前,他又央我對弈
十一年了,已形成習慣。
前十年,他輸多贏少
后十年剛開始,我們輸贏各半
我明白小子的心思。
他試圖用戰(zhàn)勝老子的方式
標注長成的速度與高度
人進中年,我已慣看成敗
落子觀三步,轉山轉水
抱守日益陡峭的帆桅
渡己,又渡人。
許多事就這么成了
許多事不為外人道
窗外,月光正逼迫窗臺
他架炮躍馬,我支士飛象
一心將一枚卒子送過界河。
日漸縝密的青春步驟,讓我
連連退卻。
而我在困境中竟獲幸福
父親你離開我們十一年
你的棋子與棋盤都還在。
車馬炮,象士卒都還在。
他挺進的每一步,我都
感知你傳輸的規(guī)則與力度。
我們在一次次對立中統(tǒng)一,
共同完成一次次對你的紀念
我的中年——《中年三疊》之二
我從另一個城市,踏上
回程的動車時,
妻子正在空中航行。她要
出席東京的一個項目推介會。
幾乎每個月,她都要
飛來飛去。
而我的兒子,此刻正坐在
高鐵的某節(jié)車廂里,戴著耳機
聽歌,用微信與同學聊天。
他常為一場籃球或足球賽
拒絕我們的輪番挽留
果斷提前返校
我們難有完整的聚會
我們都在各自的途中
清晨——《中年三疊》之三
喜愛此時樓體的灰白
在陽光到來前干凈亮堂。
我手提公文包走下臺階
圖書館的塔鐘正好敲響
十幾只麻雀,立在枯枝上
像沒有落去的樹葉。
透過稀疏的叢林,看得見
河對岸慢跑的女子
月亮在西南的上空
薄得不能再薄,像下一秒
就會完全融化的冰塊。
沒有上凍的河水往南流淌
我和妻子各自駕車上班
放寒假的兒子在睡懶覺。
沒見霧霾與街頭的受苦人。
我愛這一天輕快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