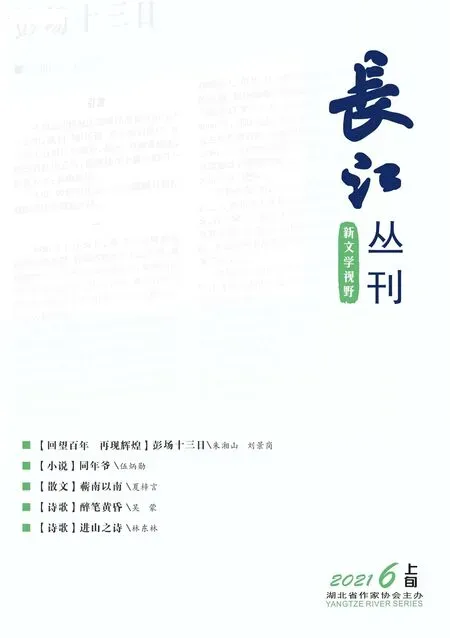播種者
任儒舉
1938年10月,抗日戰爭正進入膠著狀態,日本人進占華北后繼續南侵,我黨為了顧全大局,已經接受國民黨政府對我軍的改編。但是,日本人仗著武器精良,餓虎般地撲來,屠刀插進中原的腹地——武漢。我黨的緊要任務是在中原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時任湖北省工委常委、宣傳部長的陶鑄受黨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派,臨危受命,來到大洪山的腹地開辦抗戰干部培訓班。
那年冬天特別冷。下車伊始,陶鑄顧不得舟車勞頓,急忙向接待他們的中共地下黨員詢問辦校的相關情況,選址、招生、學校基礎設施配套、保密措施……
經過五天的實地調查,陶鑄對大洪山有了全面了解。大洪山位于京、鐘、隨三縣交界處,主要部分在隨縣。山脈由西北到東南長約200公里,西南至東北寬約100多公里,總面積約2萬平方公里,其間峰巒疊嶂,巍峨起伏,地勢險要,除主峰海拔1000多米外,其余山峰都在500米上下,很少斷崖絕壁,易于迂回隱蔽。而且土地革命時期,紅軍經常在這里活動,群眾基礎好。另外這里土地肥沃,盛產稻棉,有利于解決部隊給養。如果武漢淪陷,在這里建立抗日根據地,當是理想之地。
陶鑄來大洪山辦抗戰培訓班,說白了就是培養干部,就是播撒抗日火種。陶鑄就是地地道道的播種者。說起這培訓班的由來還得從一年前說起。
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形成,中國共產黨準備利用湖北省合作委員會等機構訓練幾批合作指導員深入農村,宣傳動員和組織民眾抗戰,訓練地點設在湖北省應城縣的湯池。經周恩來、董必武研究決定,派陶鑄以共產黨員身份公開領導這個訓練班的工作。
1937年12月22日,訓練班第一期開學了。這個訓練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陜北公學的榜樣辦的,教師和學生六七十人,主要學習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游擊戰爭戰略戰術。這些學員除課堂分組討論和軍事練習外,還到農民家里進行調查研究,幫助農民勞動。
從1937年底至1938年5月,訓練班共辦了四期(前三期在湯池,第四期在武昌),先后培訓了300多名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導員的名義分配在應城、京山、鐘祥、天門、漢川、云夢、安陸、荊門等縣,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東地區。這幾批革命火種撒到湖北省各地,在黨的領導下與抗日民族先鋒隊、假期回鄉知識青年及各縣知識青年、各地進步人士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
徐州失守后,黨中央1938年5月22日明確指示長江局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民眾,準備發動游擊戰爭,有計劃地建立幾個游擊隊和游擊區”。周恩來和董必武將中央這一指示傳達后,董必武又指示:“湯池訓練班還須辦下去。”
陶鑄堅決擁護和執行了黨中央這一指示,他堅定地說:“湯池訓練班不能在湯池辦,就換個地方辦;訓練班遭到反對,就改為‘臨時學校’;不能公開辦,就秘密辦,唯內容不變——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培養我黨游擊戰爭骨干力量,武裝民眾,準備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游擊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湯池創辦的“農村合作訓練班”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懷疑,就更名為“臨時學校”,后遷到隨縣均川賀氏祠堂。
1938年10月,武漢和鄂中相繼淪陷。陶鑄從沙市轉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縣丁家沖與鄂中特委書記楊學誠會合。在鄂中黨委的領導和組織下,成批男女青年紛紛來到丁家沖,要求參加抗日隊伍。黨委決定建立縣、區組織,廣泛深入發動群眾,并派沈少華、安琳生(余秉西)與應城縣礦區資本家搞好統戰關系,團結他們共同抗戰。
在黨的領導和陶鑄直接指揮下,鄂中抗日斗爭形勢發展的如火如荼。1938年11月,第五戰區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成立,陶鑄被聘為顧問,參與政治指導部的領導工作,開辦了長崗店訓練班。他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派干部分赴鄂中各縣發動民眾抗戰,組建抗日武裝,改造舊的保甲政權,協助地方進行文化教育和發展生產,把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只是這種良好的發展勢頭,由于全國性的反共浪潮沖擊受到影響。12月,陶鑄臨危受命,前往大洪山開辟新的抗戰培訓班。
1939年初,黨中央察覺到國民黨頑固派會有反共逆流出現,特派李威(李先念)、馬致遠(劉子厚)、婁光琦等南下至長崗店鄂北專員公署與石毓靈交涉南下打游擊的事宜,以便增強鄂中抗日游擊戰爭的力量,頂住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發動的反革命政變。
3月9日,陶鑄事先得到情報,有五六十名日軍押送幾十條船,由應城縣沿富水向京山宋河運輸物資。據聞船上還有一些軍火,陶鑄決定打一次伏擊。他在動員時說,這次伏擊戰斗的目的,一是打擊日寇的囂張氣焰,擴大政治影響,更好發動群眾,給害了恐日病的國民黨軍隊一副清醒劑;二是可以鍛煉部隊;三是可以繳獲敵人的軍火物資。他指定蔡松云、黃定陸為這次伏擊戰的正副指揮。
當敵船進入伏擊有效射程時,機槍、步槍、手槍同時開火,手榴彈在敵船上爆炸,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有的中彈落水,有的死傷在船上,有的慌忙藏在甲板下,有的跳入水中向對岸鼠竄。偵察員報告發現宋河方向有敵人騎兵前來增援時,陶鑄當機立斷,命令部隊撤出戰斗,迅速轉移。
這次伏擊戰,斃傷敵軍20余人,繳獲“三八”式步槍20支和一部分勞軍物資(船上并無軍火)。事后得知,在擊斃的敵人中,有日本皇族親王一人,是勞軍團的團長。宋河至應城一帶的敵人,還為他戴孝三天,后用飛機將其尸體運回東京。
在這種艱苦卓絕的狀態下,陶鑄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邊抗日邊播種。培訓班培養了大批黨的骨干力量,大洪山快速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建了鄂中抗日武裝力量和游擊根據地,武裝隊伍集中在楊家河進行第三次整編,為新四軍五師南下打下了牢固基礎。
4月,第五戰區在蔣介石的高壓下撤銷了抗敵工作委員會,陶鑄和國民黨愛國人士、湖北省建設廳廳長、抗敵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范一先生被迫離開長崗店。
這段時間,陶鑄和李范一的交往非同一般。從應城湯池到長崗店,兩人就一直在一起合作共事。他倆赤誠相待,相互尊重。在訓練班里,陶鑄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踏實的工作態度影響和感動了李范一,他對陶鑄講:“以前聽你們共產黨宣傳抗日綱領,我覺得符合民意國情,實為救國之道;現在我親眼看到你們為挽救民族危亡而踏實工作,堪稱楷模,老朽深受教益。”他還親筆寫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的條幅,掛在陶鑄的宿舍墻上,以表達他對陶鑄的贊揚和欽佩之情。陶鑄賦詩回贈:烽火漫天敵氣濃,垂楊難系別離情。長崗不住斯人在,仰望高山不見峰。
隨著干訓班的影響日益壯大,引起了當地國民黨頑固派的恐慌,他們千方百計地破壞和阻撓干訓班的正常運轉。試圖將這支新生力量驅逐出境。
六月中旬,隨縣專署專員石毓靈以邀約陶鑄到長崗店參加縣長聯席會議為由,將陶鑄扣押起來。此時的陶鑄臨危不懼,他對同時被押的應城縣長孫耀華說:“我們這些人沒有什么可怕的,戰爭、日寇、國民黨監獄沒有把我們折磨死,我們還怕什么呢?我們還要為共產主義干到死!”
第二天上午,石毓靈找他談話,勸他不要打游擊,以免引來日軍。陶鑄當面斥責石毓靈背信棄義,破壞團結抗戰的大局,已經成為民族罪人。鄂中區黨委獲知陶鑄等被扣消息,立即與鄂西北區黨委聯系設法營救。后在地下共產黨員鄭紹文以國民黨二十二集團軍特種工作總隊副總隊長身份出面周旋,陶鑄方才脫離虎口,離開大洪山。
1939年10月,陶鑄隨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重返大洪山,發展抗日武裝,并在隨南接待來訪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中國著名作家安娥和翻譯方練百等人。他們是從大后方專程來訪問李先念部隊的,陶鑄以部隊政委的身份代表挺進支隊致了歡迎辭。客人們看到陶鑄滿面胡須,形容憔悴,關心他的身體狀況。陶鑄說:“兩年前,我在漢口時,醫生說我的肺病已經到了二期半,要我買藥打針。我哪有錢買藥?”陶鑄接著說,他在隨縣一帶干了兩年,翻山越嶺,甚至吃穿都有困難,按病期推算,從那時到現在至少該是第三期了,可反而覺得比第二期半的時候好得多了!你看這個奇怪不奇怪?安娥在她的日記中這樣寫道:“陶鑄并沒有讀過很多的書,但他卻能發現這個敵后游擊地區!利用了這個地區,創造了一個游擊根據地!訓練出這樣一批抗戰斗士來。”
1940年3月,陶鑄奉命調任中央軍委秘書長,離開大洪山,取道重慶去延安。從此留在延安工作。
陶鑄雖然離開了大洪山,但是他作為一個播種者,在這里留下了抗日的種子。他親自為干訓班編寫的三字經,至今還在大洪山廣為傳唱:
我中華,是大國,人口多,土地闊。
氣候好,物產多,全世界,第一個。
小日本,是近鄰,人同種,書同文。
到明治,講維新,翻了臉,不認人。
九一八,沈陽城,被侵戰,東四省。
遭淪陷,我同胞,遭槍殺,或蹂躪。
七月七,挑事端,盧溝橋,戰火起。
我將士,不畏敵,勇往前,奮抗擊。
蔣介石,怕抵抗,丟上海,失南京。
坐四川,觀戰機,磨著刀,擦著槍。
打內戰,害人民。共產黨,是救星。
她一心,為人民,領導著,八路軍。
抄后路,打游擊,建立了,根據地。
搞統戰,喚人民,擴大了,抗日軍,
在敵后,殺敵人。日本鬼,膽戰驚。
汪精衛,嚇掉魂。軍和民,團結緊。
持久戰,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