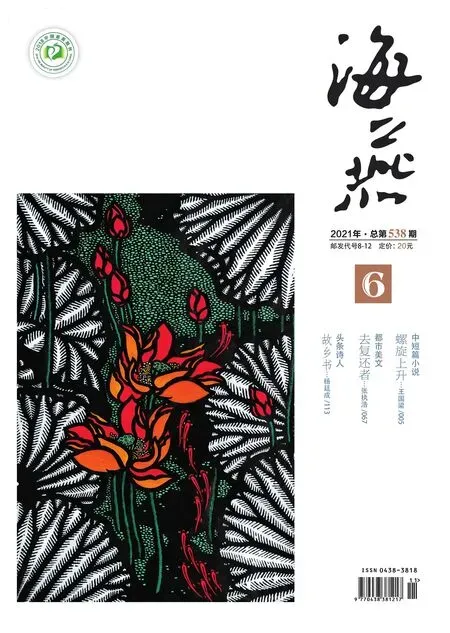讀詩記(十二)
劉向東
砍光伐盡
清點
這是我的帽子,
這是我的大衣,
還有刮臉用具
放在麻布袋里。
裝食品的罐頭:
我的碟子、杯子,
我的白鐵皮上
刻著我的名字。
我刻字用的是
我珍藏的釘子,
我不讓看見
免得別人眼饞。
干糧袋里放著
一雙羊毛襪子,
還有我不對任何人
透露的一些東西;
夜間我就拿它
當作我的枕頭。
在我和地面之間
鋪著一塊厚紙板。
我最心愛的乃是
我的鉛筆芯子;
白天它給我寫下
我夜間想好的詩。
這是我的筆記簿,
這是帳篷帆布,
這是我的手巾,
這是我的縫線。
(錢春綺 譯)
有評論家稱以艾希為代表的詩歌風格為“砍光伐盡派”,而這首詩就被譽為“砍光伐盡派”的開山之作。所謂的“砍光伐盡”,是對艾希詩歌話語特性與寫作者心理特性的統一概括。
《清點》寫于1945年美軍戰俘營中,是打開德國戰后“廢墟文學”先河的作品之一。它通過一個卑微的戰俘清點他可憐的“財物”,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戰爭在給別國人民帶來災難的同時,也給本國人民帶來了災難。它沒有正面寫戰爭,也沒有直接議論式的反思,而是歷數著一個個物象,就更為驚心動魄地將一個受動于不義戰爭、為法西斯所利用的小人物——盲目的犧牲品——的心靈、肉體、物質的艱難困苦表現了出來。從這個受害者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縮影。瘋狂而痛苦的戰爭留下了無數廢墟,與人的物質生活一樣,人的心靈也是荒蕪貧瘠的。使用簡勁甚至“干枯”的口語寫作,恰好達成了語言與生存現狀的合一。這里,詩歌的內容與形式是互為表里的。
你瞧,這個卑微的戰俘,在機械木訥地“清點”他那根本無須清點就可一目了然的可憐“財物”:除了遮體的破衣服和睡覺時充作“褥子”墊的爛紙板外,還有什么呢?一只破罐頭盒既當杯子也當碟子,這是“我”個人的財產,為防被“盜”,“我”得用一枚釘子在它的白鐵皮上刻上自己的姓名。而那枚釘子更屬我的“細軟”,別人望著它眼饞呢,“我”得藏匿好。在這些“財產”中,有“我”最心愛的東西——一截鉛筆芯。夜里“我”心潮翻涌,想著詩句,白天它幫“我”記下來……
這首詩仿佛客觀紀實,沒有任何多余的話語,但內中飽含著沉痛的感情。一個個物象代替詩人“說話”,客觀紀實與內心獨白混而難辨了。“砍光伐盡派”詩歌中強勁滋生的骨肉沉痛之情,于此可見一斑。
謙恭未免過晚
我們整好了房間
掛好了窗簾,
地窖里有足夠的儲備,
煤炭和油,
在皺紋中間用小藥瓶
把死亡藏起來。
從門縫里我們看見世界:
一只被剁掉腦袋的公雞
在院子里到處跑。
它踐踏了我們的希望。
我們在陽臺上扯起了被單
表示投降。
(綠原 譯)
這首詩的標題就告訴人們,對世界血腥戰爭的發起者和參與者而言,為敗勢所迫僅僅謙恭地“在陽臺上扯起了被單/表示投降。”是不夠的。他們必須挖掘導致荒唐、罪惡戰爭的根源,痛徹地反思、懺悔,以免人類歷史的災變再一次出現。
這首詩寫得極有層次。第一節是戰爭的準備,貌似戰備物資儲藏豐富,殊不知,死亡的可能也在同步積累著。第二節寫戰爭那瘋狂殘酷的非理性性質:“一只被剁掉腦袋的公雞/在院子里到處跑。”這個駭人的意象,將戰爭的性質說盡了。這可怕的一刀,其實既砍向了全世界無辜的受難者,也砍向了揮刀的人群。第三節寫戰爭給物質和精神遺留下的無窮的災禍。物質的災禍畢竟可以彌補,那難以彌補的是“它踐踏了我們的希望。”
是的,“謙恭未免過晚”,但愿人今后不要在制造了巨大的災難后再被迫謙恭,而是要時時保持對理性、和平、慈愛的恭謹敬護。艾希的詩總是在極度簡省的筆墨里傾注著直指人心的力量。死亡的小藥瓶——剁掉腦袋瘋跑的公雞——陽臺上投降的白被單,這三個精審的意象,以其嚴密的歷史邏輯和痛苦的情感,不僅為二戰也為一切血腥的戰爭進行了命名。詩人反思的深刻和詩藝的精湛一同呈現出來。
承受孑然一身的孤獨
1926年5月9日,俄國詩人茨維塔耶娃在致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信中,異乎尋常地寫出了這樣的話:“在您之后,詩人還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個大師(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則意味著(也許意味著)去超越詩。”
其實里爾克早期的作品,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抒情詩。一朵凋萎的花可成為一個被遺棄的少女,一顆眼淚也能成為洞察天宇的星辰。這是一種“寓言”式的作品,由彼及此,本質上還是以抒情主體為中心的詩歌品格。
對于早期的詩,里爾克曾自我評論說:“那時,大自然對我還只是一個普通的刺激物,一個懷念的對象,一個工具……我還不知道靜坐在它面前。我一任自己內在心靈的驅使……就這樣,我行走,眼睛睜開,可是我并未看見大自然,我只看見它在我情感中激起的淺薄影像。”
中年里爾克認為詩不再是情感,認為“詩是經驗”,他的詩,也發生了質的轉變。
“經歷和體驗”,它不是一種純熟的技藝,而是通過對藝術獻身的“工作”去尋覓和發現被遮蔽的事物中原始的內涵,是置身真理中的一種創造。
冷靜地面對世界而達到客觀化,超越情感的層面。在這樣的詩中,不是“我喜歡這”,而是“就是這”。
豹——在巴黎植物園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鐵欄
纏得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條的鐵欄桿,
千條的鐵欄后便沒有宇宙。
強韌的腳步邁著柔軟的步容
在這極小的圈中旋轉,
仿佛力之舞圍繞著一個中心
在中心一個偉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時眼簾無聲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圖像浸入,
通過四肢緊張的靜寂——
在心中化為烏有。
(馮至 譯)
這首詩是寫豹子還是寫人?整日被關在籠子里的豹子怎會有這樣復雜的心情,會感到“千條的鐵欄后便沒有宇宙”?顯然這是里爾克將自己的心情移至豹子身上的結果。豹子是豹子,也是人,這種人與豹合而為一,不知何者為豹、何者為人的一體狀態,或也可稱之為移情的例證。
預感
我像一面旗幟為遠方所包圍。
我感到吹來的風,而且必須承受它,當時下界萬物尚一無動彈:
門悄然關著,煙囪里一片寂靜;
窗戶沒有震顫,塵土躺在地面。
我卻知道了風暴,并像大海一樣激蕩。
我招展自身又墜入自身
并掙脫自身,孑然孤立
于巨大的風暴之中。
(陳敬容 譯)
里爾克強調寫作首先要對事物進行長期而多樣的觀察,并把觀察結果爛熟于心:“為了寫一行詩,必須觀察許多城市,觀察各種人和物,必須認識各種動物,必須感受鳥雀如何飛翔,必須知曉小花在晨曦中開放的神采,必須能夠回想異土他鄉的路途,回想那些不期之遇和早已料到的告別;回想朦朧的童年時光,回想雙親,當時雙親給你帶來歡樂而你又不能理解這種歡樂(因為這是對另一個人而言的歡樂),你就只好惹他們生氣;回想童年的疾病,這些疾病發作時非常奇怪,有那么多深刻和艱難的變化;回想在安靜和壓抑的斗室中度過的日子,回想在許許多多的海邊度過的清晨,回想在旅途中度過的夜晚和點點繁星比翼高翔而去的夜晚。即使想到這一切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回憶許多愛之夜,這些愛之夜各個不一,必須回憶臨盆孕婦的號叫,臉色蒼白的產婦輕松地酣睡。此外還得和行將就木的人做伴,在窗子洞開的房間里坐在死者身邊細聽一陣又一陣的嘈雜聲。然而,這樣回憶還不夠,如果回憶的東西數不勝數,那就必須還能夠忘卻,必須具備極大的耐心等待這些回憶再度來臨。只有當回憶化為我們身上的鮮血、視線和神態,沒有名稱,和我們自身融為一體,難以區分,只有這時,即在一個不可多得的時刻,詩的第一個詞才在回憶中站立起來,從回憶中迸發出來。”在這一大段文字中,里爾克揭示了一首詩誕生的艱難前奏。其中的核心環節是觀察、體驗和回憶。回憶被里爾克視為詩歌誕生的策源地,里爾克強調一定要使回憶成為身體上的某個器官,它必不可缺但是常常不被察覺。直到有一天,這種回憶突然自動涌現出來。只有這樣,才會轉入文字表達階段。里爾克認為表達就是對客觀事物做冷靜描述,并使自己的特定心境彌漫于描述之中,從而借助客觀事物象征詩人的整體心境。因此,里爾克的詩歌被稱為“事物詩”,《預感》就是其“事物詩”的代表作。
在這首詩中,詩人把旗幟作為自身的象征,把風暴作為災禍或苦難的象征。全詩可以分成兩個階段:風暴來臨之前與風暴來臨之后。所謂“預感”指的是風暴來臨之前,并和后一階段的真實感覺互為映照。詩中的第一個關鍵詞是“包圍”,它體現出來的是遠方帶給詩人的壓抑感。詩人之所以說包圍自己的是“遠方”,是因為遠方是醞釀風暴的地方。“包圍”和后面的“承受”相應。“承受”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焦慮感。事實上,無論是“包圍”還是“承受”都處于“預感”當中。也就是說,這時候并沒有風暴。但是,敏感的詩人已經預感到它就要來了,因而心里時刻處于有意識的“迎接”狀態。以下幾句用“下界萬物”作為反襯,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詩的空間。到第二階段,風暴真的來了,詩人試圖像大海一樣與風共舞。但是,在風中飄揚的旗幟卻又返回了原地。結果,詩人只能像旗幟一樣在掙脫自身與返回自身之間來回翻騰。苦難之中的詩人既感到不由自主的無奈,又承受著孑然一身的孤獨。
靈魂像河流一樣深沉
黑人談河流
我熟悉河流:
我熟悉那些像地球一樣古老的河流,比人類血管里流的血液還要古老的河流。
我的靈魂成長得像河流一樣深沉。
我在幼發拉底河中沐浴,當朝陽還是年輕的時候。
我在剛果河畔蓋小茅屋,河水撫慰我進入夢鄉。
我眺望著尼羅河,在河邊建起金字塔。
我傾聽密西西比河的歌唱,當亞伯?林肯順流而下新奧爾良,我看見它的渾濁的胸膛在夕陽中閃著金光。
我熟悉河流:
那些古老的幽冥的河流。
我的靈魂成長得像河流一樣深沉。
(曾卓 譯)
蘭斯頓·休士,美國著名黑人詩人。他的《黑人談河流》,是一首不同凡響的具有深刻思想內涵、強大藝術表現力的佳作。
此詩寫于他的中學時代,是他發表的詩歌處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詩人懷著無比自豪的感情,以世界著名的大河為喻,展現了黑人繁衍的地方,深情地歌唱了曾為世界和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黑人種族。對他們的歷史、他們的現實、他們勇敢的生命給予了熱情的贊美。河流的呼嘯就是黑人古老種族生命的吶喊。更深刻的是,這首詩還把黑人形象和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奴隸的形象聯系起來,從而使詩具有了更為深遠的意義和普遍價值。作者禮贊河流,更謳歌黑人,在人與自然渾然合一之中,使人深入理解了在漫長歷史背景下偉大的黑人種族頑強的精神。
為了烘托凝重的感情,詩中還寫了流淌在廣闊土地上的那些河流的朝陽、落日和黑夜,詩人以不同地域、不同時間的不同景物,渲染出一派雄渾絢麗的色彩。
這首詩把爵士樂的韻律和節奏融會于自由體詩歌之中。反復吟唱,極具黑人通俗民謠的風格,準確地體現了黑人詩歌的精髓是“聲音”而不是印刷符號這一特征。
時間是流動的,歷史是流動的,生命是流動的,血和淚也是流動的。這首短詩,竟含括了如此博大的內容,如此廣闊的空間!
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
圣誕駛車送雙親回家
穿過風雪,我駛車送二老
在山崖邊他們衰弱的身軀感到猶豫
我向山谷高喊
只有積雪給我回答
他們悄悄地談話
說到提水,吃橘子
孫子的照片,昨晚忘記拿了。
他們打開自己的家門,身影消失了
橡樹在林中倒下,誰能聽見?
隔著千里的沉寂。
他們這樣緊緊挨近地坐著,
好像被雪擠壓在一起。
(鄭敏 譯)
美國詩人羅伯特·勃萊懷著善良又驚奇的詩心,體味著大自然及人倫親情。讀這首詩,我們感到寧靜的心音清晰,卻又有微微的悵惘涌動。短短十幾行,時空交錯,意緒紛飛,將我們引向了親情——家——積雪的山谷——橡樹林……甚至更遠的地方。
在風雪的圣誕之夜,詩人送二老回家。看來父母真的老了,“在山崖邊他們衰弱的身軀感到猶豫”,這種至為細膩的體察只會出自一個孝子。詩句是最不能騙人的,它運行在詩人的血液里。一對相依為命的慈祥老人,悄悄地談話,在瑣屑的日常細節及難舍孫兒等“不重要的話題”里,恰恰涌動著最本真的親情。詩人感受著這一切,溫馨而傷懷:爹娘已過秋風遲暮之年,他們生命的旅程已是最后季節的沉寂冰雪,“他們這樣緊緊挨近地坐著,/好像被雪擠壓在一起。”最后四行詩,在寫實的場景中“深層意象”翩然躍起,生命與大自然構成了彼此的觀照,直覺與推測凝而為一。這是詩人對自己誠樸而復雜的警醒:讓“我”常常看望他們,度過對二老來說已所剩不多的共同時空,因為“橡樹在林中倒下,誰能聽見?/隔著千里的沉寂。”
詩歌不應拒絕對日常生活的表現,但也決不能成為枯燥的生活小型記事。
考慮放棄所有的野心是多么奇妙!
突然,我清楚地看見
一朵剛剛飄落在馬鬃上的
潔白的雪花!
(彭予 譯)
讀《飲馬》,想起了王維的“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它們有相同的凝神感。《飲馬》的后三句是對第一句中提到的“放棄”的真正放棄。不知道勃萊是否讀過道家的哲學,這詩的感覺是深入、安靜。短短的四句,實際走出了很遠,最后雪花那個詞也不像終點,像開始。這種靈光一現,回歸自然的體驗我們每個人都有過。
反對英國人之詩
風穿樹林而來,
像暮色里騎白馬奔馳,
是為了國家打仗,打英國人。
我不知道華盛頓是否聽樹的聲音。
整個早晨我坐在深草里,
草長得能遮住我的眼睛。
我從樹下抬頭,聽樹葉里的風聲。
突然我發現還有風
穿過深草而來。
宮殿,游艇,靜悄悄的白色建筑,
涼爽的房間里,大理石桌上有冷飲。
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
(王佐良 譯)
這首詩題名為“反對英國人之詩”,其成詩背景可能很復雜。但詩就是詩,我們只能把它當詩來讀。因此,在詩中勃萊寫了一系列帶有幽靜、隱秘、清暢之美的大自然畫面。伴著陣陣清風的吹拂,使我們領略了一種有著清風般活力和美質的詩學立場的真義。要注意,這里的“為了國家打仗/打英國人。”可能只是一種幽默的說法。
“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這句話意味深長。它既是自豪,又是反諷:對詩而言,那種連風聲和自然之美也不聽不看的“大詩”,難道就真是“富有”的嗎?那些喪失了對情感和自然的敏悟的詩人是“不好”的,而能“聽著風聲”的貧窮詩人,才是真正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