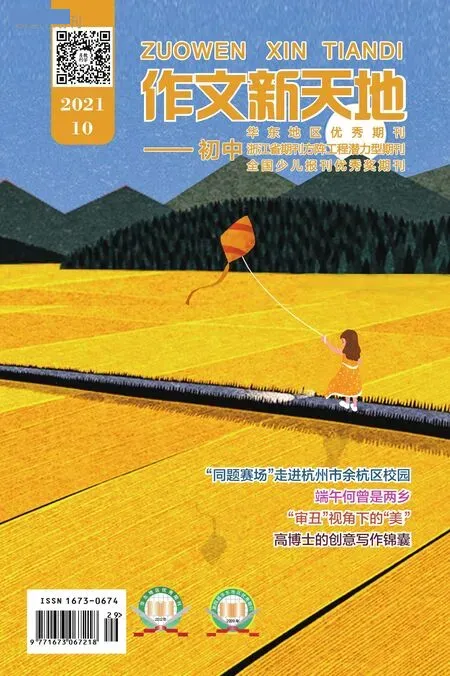“審丑”視角下的“美”
——關于寫作中的“審丑”視角
◎特約主持:浙江省湖州市第四中學教育集團 沈提花

德國學者鮑姆嘉通在《美學》一書中說過:“丑的事物,單就它本身來說,可以用一種美的方式去想。”一個丑的對象,我們可以用美的方式去想象、去表現,從而使人興味盎然,情不自禁地叫道:“丑得如此精美!”
就如賈平凹的《一棵小桃樹》,文中的小桃樹在作者筆下是病態的。作者在用“丑”詞描寫小桃樹的同時,投射以自己最真摯的情感,如文中多次稱呼小桃樹為“我的小桃樹”。卑微中蓄積的夢想更為難得,弱小者的堅強更加可貴,飽經磨難后的執著更令人動容。作者的“審丑”,讓小桃樹在激烈的沖突中彰顯一種崇高的壯美。現代丑學開創人羅森克蘭茲說:“吸收丑是為了美而不是為了丑。”作者用“審丑”這一寫作視角,使尋常的“一棵小桃樹”由外形的審丑走向內質的審美,擁有了別樣的審美沖擊力。
審丑視角下的“丑”不是作者為了“美”而故意用的“抑”筆。就內容而言,直面“丑”而帶來的不和諧感、厭惡感,在你了解并接納“丑”以后,懷著欣賞和理解時,便不再有畏懼和反感,這時“丑”轉化為“美”,最后轉化為一種真正的美感。
卡西莫多
◎維克多·雨果
“妙呀!妙呀!妙呀!”四面八方一片狂叫。
果然,這時從花瓣格子窗窟窿里伸出來的那個鬼臉可真了不起,光艷照人。狂歡激發了群眾的想象力,他們對于荒誕離奇的丑相已經形成一種理想的標準,但是,迄今從窗洞里先后鉆出來的那些五角形、六角形、不規則形的鬼臉沒有一個能滿足這個要求。而現在,出來了一個妙不可言的丑相,看得全場觀眾眼花繚亂,奪得錦標是毫無問題的了。科柏諾老倌親自喝彩;親身參加了比賽的克洛班·特魯伊甫,天知道他那張臉達到了怎樣的丑度,現在也只好認輸。我們當然也要自愧勿如。
我們不想向讀者詳細描寫那個四面體鼻子,那張馬蹄形的嘴,小小的左眼為茅草似的棕紅色眉毛所壅塞,右眼則完全消失在一個大瘤子之下,橫七豎八的牙齒缺一塊掉一塊,就跟城墻垛子似的,長著老繭的嘴巴上有一顆大牙踐踏著,伸出來好似大象的長牙,下巴劈裂,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切都表現出一種神態,混合著狡獪、驚愕、憂傷。要是能夠的話,請諸位自己來把這一切綜合起來設想吧!
全場一致歡呼。大家趕忙向小教堂沖去,把這個上天賜福的丑人王高舉著抬了出來。這時,驚訝贊嘆達到了頂點:怪相竟然就是他的本來面目!
更恰當地說,他整個的人就是一副怪相。一個大腦袋上棕紅色頭發耷拉著。兩個肩膀之間聳著一個大駝背,前面的雞胸給予了平衡。從股至足,整個的下肢扭曲得奇形怪狀,兩腿之間只有膝蓋那里才勉強接觸,從正面看,恰似兩把大鐮刀,在刀把那里會合。寬大的腳,巨人的手。這樣的不成形體卻顯露出難以言狀的可怖體態:那是精力充沛、矯捷異常、勇氣超人的混合。這是奇特的例外:公然違抗力與美皆來自和諧這一永恒法則。這就是丑人們給予自己的王!
簡直是把打碎了的巨人重新胡亂拼湊成堆。
這樣的一種西克洛佩出現在小教堂門檻上,呆立不動,厚厚墩墩,高度幾乎等于寬度,就像某位偉人所說“底之平方”。看見他那一半紅、一半紫的大氅,滿綴著銀色鐘形花,尤其是他那丑到了完美程度的形象,群眾立刻就認出了他是誰,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
“這是卡西莫多,打鐘的人!這是卡西莫多,圣母院的駝子!卡西莫多獨眼龍!卡西莫多瘸子!妙呀!妙呀!”
可見,這可憐的家伙綽號多的是,隨便挑。
“孕婦可得當心!”學生們喊道。
“還有想懷孕的也得當心!”約翰接口喊叫。
女人們當真遮起臉來。
一個女人說:“呀,這混賬猴子!”
另一個說:“又丑又壞!”
還有一個說:“真是魔鬼!”
“我真倒霉,住在圣母院跟前,天天整夜聽見他鉆承溜,在屋檐上轉悠。”
“還帶著貓。”
“他總是在人家屋頂上。”
“他給咱們家從煙筒里灌惡運。”
“那天晚上,他從我們家窗戶向我做鬼臉,我以為是個男人,把我嚇死了!”
“我敢說他是參加群魔會的。有一次,他把一把掃帚落在我家屋檐上了。”
“啊!駝子的丑臉!”
“噗哇哇……”
(節選自維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沈老師點讀】
卡西莫多,在拉丁語中是“差不多”“略差一點兒”的意思,經常被作為丑陋的代名詞,即使沒有讀過《巴黎圣母院》的人,也會拿來形容那些面目丑陋、形體畸形的人。雨果先生用極其夸張的手法將卡西莫多的丑陋形象觸目驚心地展現在了讀者的面前。作者直視“丑”,并極盡所能地描繪“丑”,描繪眾人在這“丑”面前望而卻步、唾棄、侮辱……幾乎是人人止步于“丑”,可作者偏偏又賦予卡西莫多一種“美麗”,一種隱含的內在美。作者以其獨特的審美情趣引導讀者透 過 這 個“又 癡”“又 呆”“又聾”的形體,去窺視一顆混沌、蒙昧、與世隔絕的心靈里還有多少善良、純潔、美好的人性火花在閃耀。這種“表里不一”的反差就是“審丑”帶來的藝術沖擊力。讀完《巴黎圣母院》你會明白一個人生哲理:人性的“內在美”和“外在美”是不能畫等號的。卡西莫多,不應是丑陋的代名詞,而是真善美的另一種象征。
審丑
◎嚴歌苓
拾垃圾的曾老頭拿爛得水汲汲的眼看無定一會,說:“你出息了,跟你爸一樣教大學了。我家小臭兒也出息了,要娶媳婦了。現在的媳婦都得要鋼琴。就跟我們年輕那時候,媳婦們都得要彩禮一樣。沒彩禮,娶不上什么體面媳婦。……一個鋼琴得五千哪。”
老頭兩片嘴唇啟開著,看得出結了滿嘴的話:“我在想,你還能不能給大爺找那份差事,就是你爸早先給我找的那份兒人體模特兒的差事。小臭兒的一房間家什都是靠那份差事掙來的。”
“大爺,可現在……”
“你不用說,我知道我現在老得就剩下渣兒了,走了樣了,沒法看了。你跟學校說說,要是給別人十塊,給我八塊就成……”
無定為他爭取到的價碼是十五元一小時。因為無定父親的“審丑說”莫名其妙地熱起來。一個頂信仰“審丑”原則的學生的畫作在全國美展中得了一等獎。許多雜志都刊出了這個“審丑”創舉——巨大的畫幅上,那丑濃烈,逼真得讓人惡心。
晚秋,老頭又出現在灰色的風里,顛顛簸簸追逐一塊在風中打旋的透明塑料膜。他告訴無定,小臭兒有了鋼琴,也有了媳婦。他們交談時,不少人默默地注視著老頭,每張臉都板硬,盛著或顯著或含蓄的惡心。
又一年,趙無定被介紹到一個畫商家。敲開門,里面男主人對他叫:“哎呀,是你呀!不認識我啦?”男主人身后是一屋锃亮的家具,锃亮的各“大件兒”,锃亮的鋼琴,锃亮的一個女人。
“你媽給過我一塊冰糖呢,那時糖多金貴!忘啦?”
無定明白了,面前這個雙下巴、頭開始拔頂的男人是小臭兒。
“快請進,快請進!唉,咱家來稀客啦!”他對女人說。
無定在寬大的沙發上落下屁股,挺寒酸地把幾張畫靠在茶幾腿上。
“這幾張畫……”
“先不談生意,先吃飯!哥兒們多少年了!”小臭兒揚聲笑起來,“包了餃子,三鮮餡兒,正下著。冰箱里我存了青島的啤酒。瞅你趕得這個巧!”
這時有人輕輕叩門。媳婦從貓眼兒看出去,踮著腳尖兒退回來:“你爺爺!”“我哪兒來的爺爺?他不要老臉,我可要臉!”小臭兒說。他起身,囑咐媳婦:“先不開飯,不然他下回專趕吃飯時間來!你就告訴他我不在家。”然后轉臉向無定,笑又回來了:“拿上你的畫,咱們上臥室談。”
無定跟著進了臥室,小臭兒將門掛個死,客廳里傳來一清亮一渾濁兩副嗓音。
“臭兒又不在嗎?老也沒見他,想得慌。”
“他一時半會兒還不會回來!”
“那我多等會兒。”
“哎哎!……別往那兒坐,那沙發是新的!您坐這兒吧!……”
無定早沒了談生意的心思,心墜得他累。一個小時后,老頭走了。一鍋餃子捂在鍋里的時間太長了,全漚爛了,成漿了。
無定客氣而堅決地在他們擺開飯桌時離開了。
不久,學校會計科的人告訴無定,老頭的計時工資算錯了,少付了他百把塊錢。無定揣了錢,但從夏天到冬天,一直沒遇到老頭。他只好從學校找了老頭的合同,那上面有他的地址:某街三百四十一號。街是條偏街,在城郊。無定沒費多少時間便找著了三百四十號——這條街的最后一個號碼,再往前就是菜田了。
無定走出了街的末端,身后跟了一群熱心好事的閑人。在闊大無邊的菜田里,有一個柴棚樣的小房,門上方有一個手寫的號碼:三百四十一。門邊一輛垃圾車……
“哦,您是找他呀!”閑人中有人終于醒悟似的,“曾大爺!他死啦。去年冬天死啦!”
那人說:老頭有個很好的孫子,孝敬,掙錢給爺爺花,混得特體面,要接爺爺去他的新公寓,要天天給爺爺包餃子;但老頭不愿去,天天喂他餃子的好日子他過不慣,他怕那種被人伺候、供著的日子……這是老頭親口告訴街坊的。
“你是曾大爺的什么人?”那人問。
“朋友。”無定答。
“也認識他孫子小臭兒?”
“對。”
“他真對他爺爺那樣好?”
無定停了好大一會兒,說:“真的。”
(選自嚴歌苓《審丑》,有刪改)
【沈老師點讀】
嚴歌苓的《審丑》是一篇直接以“審丑”為題的審丑佳作。文中曾大爺的命運遭遇令人唏噓不已。他外貌丑陋:“晚秋,老頭又出現在灰色的風里,顛顛簸簸追逐一塊在風中打旋的透明塑料膜……他們交談時,不少人默默地注視著老頭,每張臉都板硬,盛著或顯著或含蓄的惡心”;做人體模特被人們視為“丑”事;小臭兒不孝,嫌棄爺爺,晚景凄涼。作者別有用心地拿其孫子小臭兒的外表光鮮、內心不孝來對比著寫,突出曾大爺吃苦耐勞,深愛自己的孫子并為之全力付出,說假話維護孫子的形象。這是典型的審丑寫法:作者是以同一人(曾大爺)外形之丑比同一人心靈之美,并以彼(小臭兒)之丑襯此之美。曾大爺形貌丑陋卻內心高尚的形象不由讓我們聯想到楊絳筆下的老王等人物的特殊命運,這些卑微的生命都寄居于社會的底層。在閱讀時,比起關注寫作技巧的運用,如何真正從更為內在的方面去關注、關心或關切人的精神世界乃至靈魂世界,更為重要。
會唱歌的墻
◎莫 言
高密東北鄉東南邊隅上那個小村,是我出生的地方。村子里幾十戶人家,幾十棟土墻草頂的房屋稀疏地擺布在膠河的懷抱里。村莊雖小,村子里卻有一條寬闊的黃土大道,道路的兩邊雜亂無章地生長著槐、柳、柏、楸,還有幾棵每到金秋就滿樹黃葉、無人能叫出名字的怪樹。路邊的樹有的是參天古木,有的卻細如麻稈,顯然是剛剛長出的幼苗。
沿著這條奇樹鑲邊的黃土大道東行三里,便出了村莊。向東南方向似乎是無限地延伸著的原野撲面而來。景觀的突變使人往往精神一振。黃土的大道已經留在身后,腳下的道路不知何時已經變成了黑色的土路,狹窄,彎曲,爬向東南,望不到盡頭。人至此總是禁不住回頭。回頭時你看到了村子中央那完全中國化了的天主教堂上,那高高的十字架上蹲著的烏鴉變成了一個模糊的黑點,融在夕陽的余暉或是清晨的乳白色炊煙里。也許你回頭時正巧是鐘聲蒼涼,從鐘樓上溢出,感動著你的心。黃土大道上樹影婆娑,如果是秋天,也許能看到落葉的奇觀:沒有一絲風,無數金黃的葉片紛紛落地,葉片相撞,索索有聲,在街上穿行的雞犬,倉皇逃竄,仿佛怕被打破頭顱。
如果是夏天站在這里,無法不沿著黑土的彎路向東南行走。黑土在夏天總是黏滯的,你脫了鞋子赤腳向前,感覺會很美妙,踩著顫顫悠悠的路面,腳的紋路會清晰地印在那路面上,但你不必擔心會陷下去。如果挖一塊這樣的黑泥,用力一攥,你就會明白了這泥土是多么的珍貴。我每次攥著這泥土,就想起了那些在商店里以很高的價格出售的那種供兒童們捏制小雞小狗用的橡皮泥。它仿佛是用豆油調和著揉了九十九道的面團。祖先們早就用這里的黑泥,用木榔頭敲打它幾十遍,使它像黑色的脂油,然后制成陶器、磚瓦,都在出窯時呈現出釉彩,盡管不是釉。這樣的陶器和磚瓦是寶貝,敲起來都能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
繼續往前走,假如是春天,草甸子里綠草如氈,星星點點、五顏六色的小小花朵,如同這氈上的美麗圖案。空中鳥聲婉轉,天藍得令人頭暈目眩。文背紅胸的那種貌似鵪鶉但不是鵪鶉的鳥兒在路上蹣跚行走,后邊跟隨著幾只剛剛出殼的幼鳥。還不時地可以看到草黃色的野兔兒一聳一聳地從你的面前跳過去,追它幾步,是有趣的游戲,但要想追上它卻是妄想。門老頭子養的那匹莽撞的瞎狗能追上野兔子,那要在冬天的原野上,最好是大雪遮蓋了原野,讓野兔子無法疾跑。
前面有一個池塘,所謂池塘,實際上就是原野上的洼地,至于如何成了洼地,洼地里的泥土去了什么地方,沒人知道,大概也沒有人想知道。草甸子里有無數的池塘,有大的,有小的。夏天時,池塘里積蓄著發黃的水。這些池塘無論大小,都以極圓的形狀存在著,令人猜想不透,猜想不透的結果就是浮想聯翩。前年夏天,我帶一位朋友來看這些池塘。剛下了一場大雨,草葉子上的雨水把我們的褲子都打濕了。池水有些混濁,水底下一串串的氣泡冒到水面上破裂,水中洋溢著一股腥甜的氣味。有的池塘里生長著厚厚的浮萍,看不到水面。有的池塘里生長著睡蓮,油亮的葉片緊貼著水面,中間高挑起一枝兩枝的花苞或是花朵,帶著十分人工的痕跡,但我知道它們絕對是自生自滅的,是野的不是家的。朦朧的月夜里,站在這樣的池塘邊,望著那些閃爍著奇光異彩的玉雕般的花朵,象征和暗示就油然而生了。四周寂靜,月光如水,蟲聲唧唧,格外深刻。使人想起日本的俳句:“蟬聲滲到巖石中。”聲音是一種力呢還是一種物質?它既然能“滲透”到磁盤上,也必定能“滲透”到巖石里。原野里的聲音滲透到我的腦海里,時時地想起來,響起來。
我站在池塘邊傾聽著唧唧蟲鳴,美人的頭發閃爍著迷人的光澤,美人的身上散發著蜂蜜的氣味。突然,一陣濕漉漉的蛙鳴從不遠處的一個池塘傳來,月亮的光彩紛紛揚揚,青蛙的氣味涼森森地粘在我們的皮膚上。仿佛高密東北鄉的全體青蛙都集中在這個約有半畝大的池塘里了,看不到一點點水面,只能看到層層疊疊地在月亮中蠕動鳴叫的青蛙和青蛙們腮邊那些白色的氣囊。月亮和青蛙們混在一起,聲音原本就是一體——自然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天安門集會,青蛙在池塘里開會。
還是回到路上來吧,那條黃沙的大道早就被我們留在了身后,這條黑色的膠泥小路旁生了若干的枝杈,一條條小徑像無數條大蛇盲目爬動時留下的痕跡,復雜地臥在原野上。你沒有必要去選擇,因為每一條小徑都與其他的小徑相連,因為每一條小路都通向奇異的風景。池塘是風景。青蛙的池塘。蛇的池塘。螃蟹的池塘。翠鳥的池塘。浮萍的池塘。睡蓮的池塘。蘆葦的池塘。水葒的池塘。冒泡的池塘和不冒泡的池塘。沒有傳說的池塘和有傳說的池塘。
(選自《莫言散文精品集·會唱歌的墻》)
【沈老師點讀】
故鄉是每個人抹不去的根的記憶,她自帶獨特的光環。莫言以他獨特的審美視角,用冷峻的目光審視著自己的故鄉,文中不乏對故鄉畸形、貧弱、不和諧的描寫。這種冷峻的視角不虛美、不隱惡,正是一種“審丑”。如東南邊隅、土墻草頂,雜亂無章生長的槐、柳、柏、楸樹,還有池塘中野生睡蓮奇異的花朵,那滿池塘的青蛙等景物。這樣的描寫無不讓人聯想到《聊齋》的孤墳、野景。莫言正是以這樣的筆墨寫出對故鄉最原始的記憶,這是一種來自最底層生活的底色,而在這樣清醒的認知里又無不透露著莫言對家鄉的熱愛。“如果挖一塊這樣的黑泥,用力一攥,你就會明白了這泥土是多么的珍貴。”是啊,哪怕故鄉再普通,再古老,再充滿苦難,也是我們的鄉土,我們心靈的港灣。在風雨的低吟中,故鄉卻永遠屹立在心中。正如他文字中苦心經營的高密東北鄉,離不開故鄉的一草一木,離不開故鄉的子民,更離不開那滲透到巖石中的高密東北鄉精神。這種獨特的文化已經融進莫言的血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