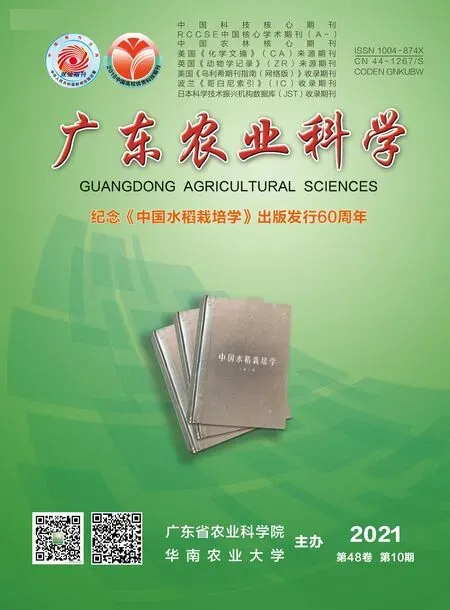水稻耐熱相關功能基因的克隆及其分子機理研究進展
丁杰榮,孫炳蕊,王慶林,范芝蘭,潘大建,陳文豐,李 晨,劉 清
(1.廣東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廣東省水稻育種新技術重點實驗室/廣東省水稻工程實驗室,廣東 廣州 510640;2.廣州國家現代農業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廣東 廣州 510520)
水稻起源于低緯度的熱帶地區,形成了適應高溫和短日照生態環境的生長習性。但水稻生長發育受溫度影響較大,以孕穗至抽穗揚花期對溫度最敏感,此階段水稻的最適溫度為25~30℃,如遇日均溫度高于32℃或日最高溫度高于35℃,水稻會出現花器官發育不全、花粉發育不良且活力下降,同時開花散粉和花粉管伸長也會受阻,導致大量空秕粒形成,從而造成嚴重的產量損失和品質下降[1-6]。
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全球溫室效應日益加劇。自1880—2012 年,全球氣溫上升了0.85 ℃,預計到21 世紀末將增加1.5~4.5 ℃,極端高溫出現頻率將大幅提高[7]。Peng 等[8]20 多年跟蹤研究發現,全球氣溫每升高1 ℃,水稻產量將下降10%。異常高溫已對我國的水稻生產造成了嚴重影響。2010 年和2013 年,我國 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生了大范圍的持續高溫,2013 年江蘇省許多地區甚至出現長達45 d 的持續高溫天氣,導致該地區水稻嚴重減產[9-10]。高溫熱害天氣越來越頻繁,已成為水稻生產的主要災害性氣候之一[6,11-12],解決水稻熱害問題刻不容緩。
目前,培育耐熱水稻品種被認為是解決熱害問題最經濟、最有效的途徑。然而,利用常規方法開展水稻耐熱性育種非常困難,一是水稻熱害研究的條件(尤其是自然條件下的環境溫度)難以控制;二是水稻的耐熱性是由多個基因控制的數量性狀,遺傳機理較為復雜[13]。深入了解水稻耐熱的分子機理,開展高效準確的分子育種,水稻耐熱問題將有望解決。近年來,隨著測序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功能基因組學研究的不斷進步,水稻耐熱性的相關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定位了一些與水稻耐熱性相關的QTL,部分相關功能基因被成功克隆。此外,水稻耐熱分子機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進展。本文就水稻耐熱性相關QTL的鑒定、功能基因的克隆及分子機理研究等方面進行綜述,以期為水稻耐熱分子育種的開展提供理論參考。
1 水稻耐熱相關QTL 的鑒定
近年來,隨著分子標記技術的發展以及對水稻熱害的高度重視,水稻耐熱性分子機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進展。國內外迄今已定位80 個以上水稻耐熱QTL,這些QTL 分布于12 條染色體上[13-27]。
1.1 耐熱QTL 的定位
水稻在孕穗和抽穗灌漿期對高溫比較敏感,目前定位的耐熱QTL 大部分是孕穗、抽穗開花和灌漿結實期相關的QTL,只有少數是苗期相關的QTL。耐熱和熱敏感親本雜交后代的重組自交系是定位耐熱QTL 的重要材料。陳慶全等[14]利用T219 和T226 構建的重組自交系,兩年間共定位了6 個抽穗開花期耐熱性主效應QTL,分別位于第2、3、8、9、12 號染色體上,qHt2、qHt3、qHt8和qHt12來 自T226,qHt9a和qHt9b來 自T219,其中qHt3在兩年實驗中都被定位到,有潛在的分子育種應用價值[14]。Jagadish 等[15]利用Bala 和Azucena 構建的重組自交系定位了分布在第1、2、3、8、10、11 號染色體上的8 個耐熱QTL,其中1 個QTL 對表型貢獻率高達18%。Tazib 等[16]利用 Nipponbare 和Kasalath 構建的回交重組自交系,以花藥長度等作為性狀指標,共定位了12 個耐熱QTL。盤毅等[17]利用996 和4628 構建的重組自交系,定位了2 個花粉育性相關的耐熱 QTL,其中qPF4可使水稻在高溫下花粉可育率提高7.15%,qPF6同樣能提高水稻在高溫下的花粉可育率。Ps 等[18]利用N22 和IR64 構建的重組自交系也定位了5 個耐熱QTL,分別位于第3、5、9、12 染色體上,其中一個主效QTL與前期定位的QTL 重疊(qSTIY5.1/qSSIY5.2),另一個主效QTL(qSTIPSS9.1)為新定位的耐熱QTL。
除重組自交系外,研究人員構建的近等基因系、染色體片段代換系和滲入系也是定位水稻耐熱QTL 的重要材料。曹志斌等[19]利用元江普通野生稻荷花塘3 號為供體、秈稻恢復系蜀恢527為輪回親本構建的種間近等基因系成功定位到qHTH5,其在F2和F3代的表型貢獻率分別為8.6%和19.4%。Li 等[20]利用Liaoyan241 和IAPAR-9構建的近等基因系,以水稻結實率為性狀指標,定位了11 個耐熱QTL,其中qNS1、qNS4、qNS6和qRRS4等4 個主效QTL 能穩定地在不同年份或環境中被定位到。張昌全等[21]利用以日本晴和9311 構建的染色體片段代換系定位了3 個耐熱性QTL。奎麗梅等[22]利用遺傳背景為特青的云南元江野生稻滲入系材料,在第1、3、8、10 號染色體上各定位了1 個抽穗開花期耐熱相關QTL。
上述是孕穗、抽穗開花和灌漿結實期的水稻耐熱QTL,而有關苗期耐熱QTL 報道較少。Kilasi 等[23]利用N22 和IR64 構建的近等基因系對水稻幼苗進行熱害處理,以根長和株高為性狀指標,共定位到10 個耐熱QTL,其中rlht5.1、slht6.1/slpc6.1、slpc2.1、slpc10.2和slpc10.3的 表型貢獻率都超過10%。而Lei 等[24]利用與奎麗梅相同的材料[22],也定位到5 個苗期耐熱性相關QTL,其中位于3 號染色體的耐熱性QTL 與奎麗梅等[22]定位的qHT3位置相近,說明苗期耐熱性與抽穗開花期耐熱性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1.2 耐熱QTL 間的互作
水稻耐熱性是由多基因控制的數量性狀,單個耐熱QTL 起作用的同時,不同耐熱QTL間的互作也對水稻耐熱性起重要作用。趙志剛等[25]定位的7 個耐熱QTL 分布在4 條染色體上,它們的表型貢獻率為6.4%~19.7%,加性效應為-21.3%~20.9%。曹立勇等[26]利用IR64 和Azucena 花藥培養的DH 群體定位到6 個開花結實相關的具有加性效應的耐熱QTL,這6 個QTL能提高結實率4.33%~10.37%;此外,在第 1、2、3、4、5、7、8、11 等8 條染色體間還檢測到 8 對加性×加性上位性效應,其貢獻率為2.27%~8.13%。陳慶全等[14]在定位水稻耐熱QTL時也檢測到7 對上位性QTL,位于第1、2、4、11、12 染色體上的4 對QTL 間,以及位于第2、3、4、7、8、9 染色體上的3 對QTL 間分別存在互作效應。朱昌蘭等[27]定位到3 個灌漿期耐熱性主效QTL,并檢測到8 對上位性互作QTL 位點,它們對粒重變化的貢獻率為2.45%~5.29%。不同耐熱QTL 表型貢獻率差異較大,主效QTL 的定位及對應基因的克隆對水稻耐熱品種的選育意義重大。但不同QTL 之間錯綜復雜的互作使水稻耐熱QTL 的定位困難重重,水稻耐熱基因的克隆難度很大。
2 水稻耐熱相關功能基因的克隆
水稻耐熱性是由多基因控制的復雜性狀,且難以準確進行表型鑒定,因此水稻耐熱功能基因的克隆鑒定顯得尤為困難。目前,僅有不到30 個水稻耐熱相關基因被克隆鑒定,其中多數基因是通過反向遺傳學方式克隆鑒定得到,僅有少數幾個基因由正向遺傳學手段克隆鑒定得到。克隆鑒定所得的水稻耐熱相關基因多數編碼蛋白質,其中11 個基因編碼蛋白酶類,10 個基因編碼熱激蛋白等其他蛋白質,3 個基因是轉錄因子(表1)。
2.1 通過正向遺傳學方式克隆功能基因
通過正向遺傳學手段克隆的水稻耐熱基因對水稻耐熱性均起正向調控作用。Li 等[28]以生長于熱帶的非洲稻為材料,通過與亞洲栽培稻雜交構建遺傳群體,并進一步進行遺傳分析和定位克隆,成功分離克隆了控制非洲稻的一個耐高溫主效QTL 的功能基因OgTT1(Oryza glaberrimaThermo-tolerance 1)。OgTT1編碼一個26S 蛋白酶體的α2 亞基,在泛素化介導的蛋白降解通路中發揮重要作用。過表達OgTT1能夠顯著增強水稻在苗期、開花期和灌漿期的耐熱性[28]。Wei 等[30]以耐熱水稻品系HT54(源自廣陸矮4號)與熱敏感品系HT13(源自秈稻05-占)構建遺傳群體,定位了調控水稻苗期耐熱的主效位點OsHTAS(Oryza sativaHeat Tolerance at Seeding Stage)。進一步研究表明,OsHTAS編碼一個泛素連接酶,過表達OsHTAS能顯著增強水稻的苗期耐熱性[23]。Wang 等[31]從秈稻品種中秈3037 自然突變體中克隆到耐熱功能基因TOGR1(Thermotolerant Growth Required 1),該基因編碼一個DEAD-Box RNA 解旋酶,其表達同時受到溫度和晝夜節律的調控,且與日常溫度的波動緊密相關,溫度升高會直接增強其解旋酶活性,TOGR1轉錄水平的變化還與株高呈正相關,過表達TOGR1會使水稻在高溫條件下生長更好。此外,Shen 等[32]從擬南芥中分離得到了1 個富含亮氨酸重復序列的類受體激酶基因ER(Receptor-like Kinase ERECTA),在水稻中過表達ER基因能顯著增強水稻的耐熱性。“高ER水稻”與野生型植株相比,在高溫條件下的結實率顯著增加;反之,在水稻中功能性突變ER的同源基因會顯著降低植株的耐熱性[32]。
2.2 通過反向遺傳學方式克隆功能基因
目前通過反向遺傳學手段克隆鑒定的水稻耐熱基因有20 多個,其中多數基因起正向調控作用,僅有幾個基因起負向調控作用(表1)。
2.2.1發揮正向調控作用的功能基因 熱激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是植物熱信號傳導通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酵母細胞中過表達水稻OsHSP90基因能顯著增強細胞在42、50、70 ℃下的耐熱能力[33]。此外,Lin 等[34]研究發現,HSP101 通過與熱相關蛋白HSA32(Heat Stressassociated 32-kd Protein)的互作,在水稻苗期的基礎耐熱性和后天長期的耐熱性馴化中發揮了重要的調控作用。OsANN1是水稻膜聯蛋白家族中的一個成員,其表達受高溫處理顯著誘導[35]。過表達OsANN1能顯著改善水稻在高溫條件下的生長,而OsANN1的基因敲除株對高溫熱害更加敏感[29]。OsHCI1(Oryza sativaHeat and Cold Induced 1)編碼一個環finger E3 連接酶,也受高溫誘導[36]。在正常生長條件下,該基因定位于高爾基體中,且能夠沿著細胞骨架快速移動,但是在受到高溫處理后,OsHCI1可能累積在細胞核中[36]。在擬南芥中過表達OsHCI1能顯著增加植株在高溫下的存活率[36]。與OsHCI1基因相似,OsHIRP1(Oryza sativaHeat-induced RING Finger Protein 1)也編碼一個環finger E3 連接酶,經45 ℃高溫處理后,OsHIRP1主要在細胞核中富集,在擬南芥中過表達OsHIRP1能顯著提高種子的發芽率[37]。此外,OsMYB55、SNAC3和OsNTL3基因的表達也受到高溫熱害的顯著誘導。過表達OsMYB55顯著改善水稻在高溫條件下的生長,同時減小高溫對產量的影響[38]。過表達SNAC3和OsNTL3的水稻植株耐熱性顯著增強,反之,SNAC3的基因沉默植株和OsNTL3的基因編輯植株對熱害更加敏感[39-40]。
SUMO(Small Ubiquitin-related Modifier)化修飾是一個類泛素化的過程,在高等植物的生命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匍匐翦股穎(Agrostis stoloniferaL.)中過表達編碼SUMO E3 連接酶的OsSIZ1基因會使植株在高溫條件下的耐熱性顯著增強[41]。轉錄后RNA 修飾也廣泛存在于活體生物中,其中一種豐富的mRNA 轉錄后修飾方式就是胞嘧啶的5'端甲基化(m5C)修飾。編碼m5C甲基轉移酶的OsNSUN2基因在水稻耐熱性中也發揮了重要調控作用,osnsun2突變植株的苗期耐熱性顯著降低[42]。Shiraya 等[43]研究表明,高爾基體/質體類型的錳超氧化物歧化酶(Manganese SOD 1,MSD1)在耐熱水稻品種中的表達量顯著高于耐熱性較低的水稻品種,持續高表達MSD1的植株在高溫條件下的籽粒品質顯著優于野生型植株的籽粒品質,反之,msd1敲除的水稻植株對熱脅迫的反應更加敏感。此外,過表達編碼水稻異三聚體G 蛋白β 亞基的OsRGB1顯著增強轉基因植株的發芽期和苗期耐熱性[44]。過表達編碼小GTP 結合蛋白的OsRab7也使轉基因水稻植株的苗期耐熱性顯著增強[45]。此外,已有研究表明鈣信號在植物響應非生物脅迫過程中也發揮重要作用。Cui 等[46]研究發現,OsCNGC14(Oryza sativaCyclic Nucleotide-gated Ion Channel 14)和OsCNGC16(Oryza sativaCyclic Nucleotide-gated Ion Channel 16)這兩個環核苷酸門控離子通道蛋白正向調控水稻植株的耐熱性。oscngc14/16雙突變植株的苗期耐熱性顯著降低,且突變這兩個蛋白的任何一個都可降低或者消除熱脅迫誘導的胞質鈣信號[46]。
2.2.2發揮負向調控的功能基因OsHSBP1(Oryza sativaHeat Shock Factor Binding Protein 1)、OsHSBP2(Oryza sativaHeat Shock Factor Binding Protein 2)、OsMDHAR4(Oryza sativaMonodehydroascorbate Reductase 4)、OsFBN1(Oryza sativaFibrillin 1)和OsUBP21(Oryza sativaUbiquitin-Specific Protease 21)在水稻耐熱性中起負向調控作用。OsHSBP1和OsHSBP2編碼HSF(Heat Shock Factor)結合蛋白,正常生長條件下它們廣泛表達于各個組織,且在高溫處理后的恢復期表達水平急劇上調[47]。過表達OsHSBP1或OsHSBP2的水稻植株對高溫熱害更加敏感,而OsHSBP1或OsHSBP2的基因沉默株系在高溫條件下幼苗的存活率顯著增加[47]。過表達編碼一個單脫水抗壞血酸還原酶的OsMDHAR4會顯著降低水稻植株在苗期的耐熱性,而osmdhar4突變體植株的苗期耐熱性顯著增強[48]。此外,過表達編碼質體-脂質相關蛋白的OsFBN1顯著降低水稻植株在苗期以及生殖生長期的耐熱性[49],而基因敲除或者降低編碼泛素特異性蛋白酶的OsUBP21的表達,可明顯增強轉基因植株的苗期耐熱性[50]。
3 水稻耐熱分子機制研究
目前水稻耐熱基因介導的耐熱分子機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維持植物體內蛋白及rRNA的正常水平及穩定性、維持細胞膜的完整性和維持細胞內正常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水平(圖1)[27-28,31-32,35,39,41,43,45]。

圖1 水稻耐熱相關基因介導的分子機制Fig.1 Molecular mechanism mediated by heat tolerance related genes in rice
3.1 維持植物體內蛋白及rRNA 的正常水平及穩定性
植物細胞在高溫逆境下積累大量的變性蛋白,這些錯誤折疊的蛋白會對細胞產生毒性[51]。OsHSP90介導的耐熱性與在高溫條件下預防蛋白變性密切相關,而且溫度越高,這種預防蛋白變性能力越強[27]。與熱激蛋白預防蛋白變性不同,對OgTT1控制水稻高溫抗性的機理研究表明,OgTT1在轉錄水平上對高溫的響應更有效,而且其編碼的蛋白使細胞中的蛋白酶體在高溫下對泛素化底物的降解速率更快,促使水稻細胞中積累的有毒變性蛋白的種類和數量均顯著降低,進而保護水稻細胞。該研究也揭示了植物細胞響應高溫的新機制,即及時有效清除變性蛋白,對維持高溫下胞內蛋白平衡至關重要;尤其在極端高溫時,清除變性蛋白比復性變性蛋白的效率更高[28]。除了高溫條件下維持蛋白的平衡外,水稻的耐熱性與rRNA 穩定性也密切相關。TOGR1作用于小亞基(SSU)rRNA 前體的加工,即使在高溫熱害的條件下也能保證rRNA 前體的正常剪切,因而能保持植物體內正常的rRNA 水平[31]。
3.2 維持細胞膜的完整性
非生物脅迫條件下,細胞膜的完整性與植物耐熱性密切相關。對ER基因介導的耐熱性機理研究表明,ER基因表達水平提高后,植物細胞膜在逆境下更完整,細胞不易死亡。細胞增多變大,組織器官與生物量也隨之變大,使植株總體壯實得以增產[32]。高溫脅迫下,過表達OsSIZ1的轉基因匍匐翦股穎植株比無OsSIZ1的對照植物表現出更完整的細胞膜、更強的保水性,所受的熱害也更輕微[41]。在番茄中的研究也發現,SlSIZ1的干擾株系比其野生型株系對熱更敏感,SlSIZ1的過表達株系則更耐熱[52]。進一步研究發現,熱脅迫下SlSIZ1過表達株系中的HSP70、HSP90和HsfA2的表達量顯著增加,而SlSIZ1 可與SlHsfA1 互作并介導SlHsfA1 的SUMO 化[52]。由此可見,SlSIZ1可能是通過調控HSP70和HsfA2等下游基因的表達對某些蛋白起保護作用或介導其SUMO 化以保護細胞膜結構。
3.3 維持細胞內正常的ROS 水平
ROS 的積累影響耐熱性,而植物細胞在遭受高溫熱害后,體內會富集過多的ROS,從而危害細胞內的膜脂、蛋白和核酸等生物分子,造成植物細胞死亡[53]。已有研究表明,OsANN1、SNAC3、OsRab7和MSD1介導的耐熱性是通過降低熱害產生的ROS 水平來實現的[35,39,43,45]。過表達SNAC3基因,顯著降低了植株體內的H2O2水平,表現出更好的耐熱性[39]。與SNAC3基因相反,OsHSBP1或OsHSBP2介導的熱敏性是由體內過多的ROS 導致的[47]。OsNSUN2突變導致的耐熱性降低也與植株體內積累了過多的ROS 密切相關[41]。
4 展望
目前盡管水稻育種學家已鑒定出眾多水稻耐熱相關QTL,但是水稻耐熱功能基因的分離克隆還較少,應用分子標記輔助選擇培育耐熱水稻品種也暫未見成功報道[28-29]。這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水稻耐熱性為多基因控制的數量性狀,且一般單個QTL 的表型貢獻率較低,不同QTL 之間經常會有互作;二是水稻耐熱性的表型鑒定較為困難,難以控制田間實驗處理的環境和溫度;三是水稻耐熱性相關基因表達受環境影響較大,有些基因只在特定時期才表達發揮功能,因此難以準確鑒定。
目前已克隆鑒定的水稻耐熱相關功能基因還較少,所開展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水稻苗期進行,目前對苗期外的水稻耐熱性相關功能基因克隆鑒定僅有個別報道。但是水稻從孕穗期開始,對熱害的敏感度明顯高于苗期,遇熱害時產量受損更嚴重,而且不同生育期可能有不同的耐熱分子機制。因此,克隆鑒定水稻生殖生長期耐熱性相關的功能基因將是水稻耐熱性研究的側重點。克隆鑒定目標功能基因的同時,還需要深入研究它們所介導的水稻耐熱性相關分子機制,以期為培育耐熱且高產優質的水稻品種奠定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