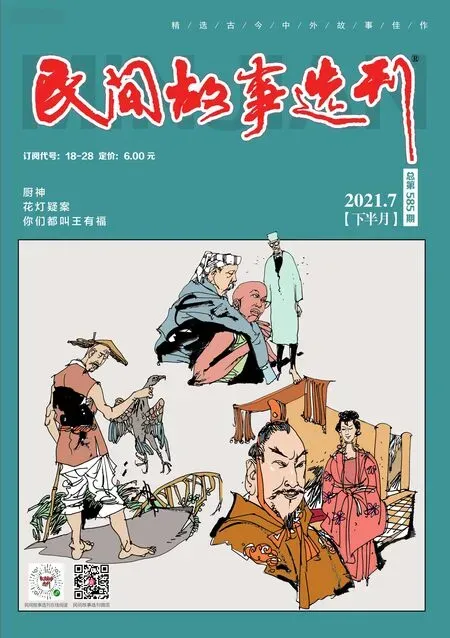鑒家的擇賞選
◇文/ 張東興
宋朝慶歷年間,東京汴梁有家書畫苑叫聽石齋。聽石齋的老板聽石先生是個書畫鑒賞權威,書畫在他面前一過,優劣真偽登時顯現。所以能夠在聽石齋立足的書畫,立時聲名鵲起,身價百倍。
書畫是給人看的,可是聽石先生卻是個盲人,盲人如何鑒賞字畫呢?
靠用鼻子嗅!聽石先生有種獨特的嗅覺,好書畫聞起來清香撲鼻,使人心曠神怡;差的書畫聞起來惡臭刺鼻。聽石先生每天白開水一杯,憑鼻子買進賣出,生意很是興隆。
這天,聽石先生剛開門,一個書生夾了個卷軸進來。此人叫周潤碧,在書畫界小有名氣,平日里,富人借他裝點門面,他借富人裝點腰包。
伙計見是熟人,趕緊招呼道:“周先生,又有大作?”
周潤碧笑笑說:“有,卻不是我的。我受朋友相托,請先生鑒賞一幅畫。”說著展開卷軸。
聽石先生坐定,他剛想用鼻鑒賞,忽聞一股奇臭,趕忙捂著鼻子擺手不迭。周潤碧的臉立刻紅了,知趣地把畫卷起來,放在門外,同時,伙計把窗戶都打開了。
聽石先生好半天才緩過氣來,埋怨道:“潤碧先生怎么開這種玩笑?”
周潤碧趕緊解釋道:“對不住,我也不得已呀。汴梁巨富錢家三公子,是個書法愛好者,成名心切,想請先生美言幾句。”
聽石先生連忙作揖:“您饒了我吧,別把我的牌子給砸了。”
周潤碧從袖子里取出一包銀子,朝柜臺上一放,苦苦哀求道:“那么借寶店一隅,掛這幅畫總可以吧?錢公子愿多出些錢。”
聽石先生見對方糾纏不清,就來了氣,干脆地說:“行!但錢要足夠多——要足夠我搬家的。留這畫在這兒,我走人!”
周潤碧求了半天,一無所得,只得夾起卷軸走了。
第二天周潤碧又來了。這回沒拿卷軸,捎來了錢公子的話:“三年后,我再拿畫來請你鑒賞!”
聽石先生心想:這種富家公子,一時興至玩起書畫,但未必真肯下苦功,過些時候就忘了,所以也沒把這句話當回事。
誰知三年后的這天,還沒開門呢,就聽到外面“哐哐”鑼響,接著就有人砸門。伙計開門一看,街心停著一乘八抬大轎,兩旁站立著兩班衙役。衙役見伙計出來,遞過一張大紅拜帖,神氣地吩咐道:“叫你們掌柜的出來!”
伙計不敢怠慢,趕緊跑到后堂,一看:一壺白開水還冒著熱氣,聽石先生人卻不見了,只是壺底壓著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交來人”。伙計只得拿了茶壺出去稟報。
壺遞進轎子,半晌沒有聲響。伙計那個緊張啊,就聽見自己的心跳得山響。終于,壺又遞出來,衙役還傳下話來:“我們老爺說了,三年后還來!”
一個“還”字,伙計猛地想起了三年前的錢公子。
到了晚上,聽石先生回來了,伙計忙問:“您怎么知道是他?”
聽石先生點點頭,說:“三年前的臭味,現在三里外都聞得到了。嗬!當了五品大員,就了不起了?看來他功夫是沒少下,只是沒下在學書畫上,而是下在買官上了。”
伙計還是覺得奇怪,不解地問:“他怎么見了您的茶壺就走了?”
聽石先生捋捋胡子,微笑著解釋說:“茶尚溫,人遠遁,足見他的書畫臭味遠揚。五品大員還要顧及面子,所以沒敢用武力強迫我說他好。”
轉眼三年,又到這一天。這回伙計沒忘,心說上回是兩班衙役,這回不知是什么排場。萬一聽石先生仍不接他的畫,他惱羞成怒,不定怎么收拾咱呢。伙計一想到這兒,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不得安寧。
誰知一個上午過去了,沒有動靜;下午過去了,仍沒有動靜。眼看太陽落山,要關門了,還是沒見人影兒。伙計向外看看,不由松了口氣,今兒是沒人來了!
正在這時,一個青衣仆人抱著個卷軸走進門來。聽石先生眼睛好像忽然復明了,他徑直走過去接過卷軸,然后遞給那青衣仆人一千兩銀子,又指指自己的鼻孔,最后是擺擺手。
青衣仆人似乎是看懂了,他一言未發,接過銀子轉身離去。
伙計在一旁看得一頭霧水,問:“這是誰呀?”聽石先生緊閉著嘴,只是不住地示意伙計趕快把卷軸拿到后面的庫房去。
伙計回來,只見聽石先生正從鼻子里取出兩粒藥丸,長長出了口氣,說:“就這么兩粒防臭丸,花去我一百兩銀子!時隔六年,想不到這幅畫更臭了。”
見這就是六年前周潤碧拿來的那幅畫,伙計更是驚得張大了嘴:“既是劣質卷軸,那您怎么還花一千兩銀子買下呢?”
聽石先生搖搖頭,說:“惹不起啊,那錢公子現在是吏部天官啦!但我仍讓他的仆人看看我鼻子里的防臭丸,讓錢公子知道:我瞎子眼瞎了,鼻子并沒失去嗅覺,所以買下他的畫,不過賣給他個面子,省得一趟一趟來熏我。再說還有一筆不小的賺頭。明兒你把那幅畫掛起來,非二萬兩不賣!我出去避避,這臭味兒就是帶著防臭丸都受不了。”
“這臭畫您不愿聞,難道就有人愿買嗎?二萬兩啊!”伙計還是不明白。
聽石先生說:“這你就不明白了。畫是不值這么多錢,但吏部天官的名可值兩萬,也許更多呢!”
第二天伙計剛把那幅畫掛上,周潤碧就領著一群閑文人進來了。他們搖頭晃腦地對那幅畫大捧一通。一些巨商聽到消息競相前來搶購,最后竟以十六萬兩出手。錢尚書遂成京都著名書畫家。
聽石先生自覺遺禍不淺,終身不再品畫,只做防臭丸廣為布施,以減輕自己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