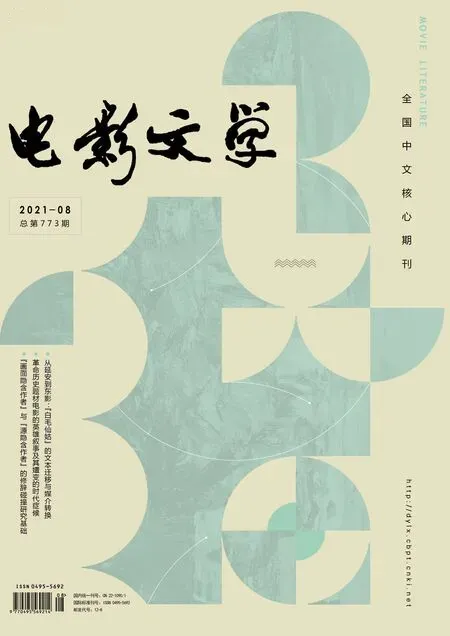電影敘事中的“蒙騙體系”
2021-11-14 08:22:20王彬
電影文學
2021年8期
王 彬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4)
法國《電影手冊》編輯部在撰寫的文章《約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中指出,《少年林肯》“通過電影的直觀和電影的知覺,隱瞞了事物的真實結構”,設置了一種“蒙騙體系”。亞當和馬特兩兄弟在與懷特扭打的混亂過程中,懷特躺倒在地,經卡斯查看后,宣布后者的死亡。兩兄弟誤以為對方是兇手,為了保護對方想獨攬罪行。兩兄弟的母親、見證人、旁觀者、觀眾等相繼陷入敘事騙局。實際上,影片“通過鏡頭的連接和延續、突然的角度變換和有一定距離的表演、參與者的反應和舉動、接踵而來的見證人——一系列使人頭暈目眩的場面”,導致人物與觀眾都墜入了兩兄弟中誰殺死了懷特的敘事圈套。人物與觀眾遭到雙重欺騙與愚弄,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信息的遮蔽與有意誤導。直到最后林肯戳穿了卡斯殺死朋友懷特的騙局,敘事得以通過麥基所言的“閉合神秘”的方式結束。
“蒙騙體系”在于隱瞞、誤導、遮蔽觀眾的視線,進而引起驚奇與懸念的審美體驗。驚奇與懸念是互補而非對立的一對概念,驚奇由“突轉”造成,常與“發現”共時發生。在觀眾從不知到知的轉變中,事件突然轉向相反的方向,自驚奇而滑向懸念,致使觀眾期望與事件結果之間裂開鴻溝。因此,“蒙騙體系”最終導向的是懸念的建構與敘事吸引力的生成。然而,“蒙騙體系”所構建的懸念并非希區柯克式的“炸彈式”懸念——事先有意識地將謎底透漏給觀眾,使得知悉一切的觀眾與一無所知的人物之間形成強大的敘事張力——而是通過信息的扣押、延宕、誤導,形構一種蒙蔽機制,進而在揭開懸念之時,引起觀眾的期待受挫與“原來如此”的了然之感。……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民間文化論壇(2023年6期)2024-01-17 07:28:56
阿來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 07:38:26
課程教育研究(2021年15期)2021-04-13 23:21:23
新世紀智能(高一語文)(2020年9期)2021-01-04 00:42:46
甘肅教育(2020年8期)2020-06-11 06:10:02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新課程研究(2016年21期)2016-02-28 19:28:33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人間(2015年20期)2016-01-04 12:4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