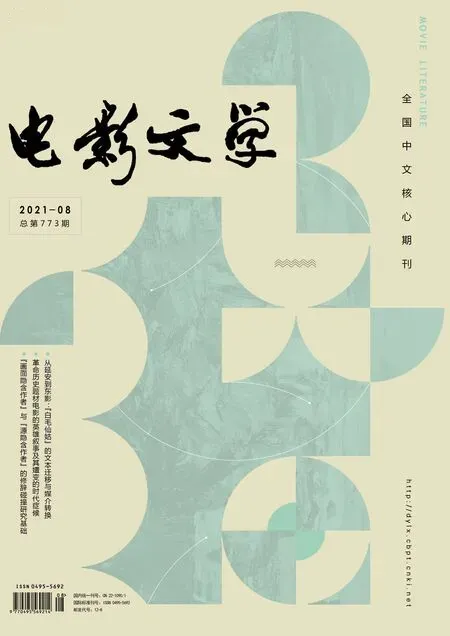《野馬分鬃》的反類型化敘事
2021-11-14 08:22:20魏成穎
電影文學
2021年8期
關鍵詞:規則
魏成穎
(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通識教育學院,重慶 401331)
《野馬分鬃》是由青年導演魏書鈞執導的劇情片,由周游、鄭英辰等主演。影片講述了一個即將從電影學院畢業的少年阿坤,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對自我的審視和對那似乎唾手可及的理想生活的追求,影片充滿了青春反叛的氣息,青春的迷茫和熱血在即將走向社會的人生節點被無限放大。阿坤像所有急于馳騁的少年一樣,迫不及待地想要闖出一番天地。在拿到了駕照后,阿坤邂逅了自己的二手吉普車,并把它看作是走向新生活的可能,想要駕駛著它在內蒙古的草原上馳騁,不曾想它卻將自己帶入了人生的另一個路口。在這段籠罩著荒誕氣息的日子里,阿坤逐漸意識到了成長的代價和生命的無常。影片的整體敘事風格是反類型化的,敘事的重心不在于講述一個單純的故事,而著重在描寫人物的生活細節和生存狀態——既粗糲野性,又飄忽迷離。影片既有對當下電影行業創作氛圍與生存現狀的諷刺,也有對所謂的社會規則的揶揄,使影片整體有一種成長的虛無之感,使人很容易聯想到以楊德昌導演為代表的、平靜寫實之下包含荒涼之感的電影風格。
楊德昌導演是臺灣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其電影以一種冷靜的視角去直面物質化社會下個體精神的變異,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其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更是將少年在社會異化下的隕落表現得淋漓盡致。……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22年28期)2022-05-30 10:48:04
小獼猴智力畫刊(2022年3期)2022-03-29 01:09:42
數學小靈通(1-2年級)(2021年4期)2021-06-09 06:26:14
法律方法(2019年3期)2019-09-11 06:26:16
中國外匯(2019年7期)2019-07-13 05:44:52
幸福(2018年33期)2018-12-05 05:22:42
環球飛行(2018年7期)2018-06-27 07:26:14
Coco薇(2017年11期)2018-01-03 20:59:57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9期)2017-01-15 13:52:02
運動(2016年6期)2016-12-01 06:3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