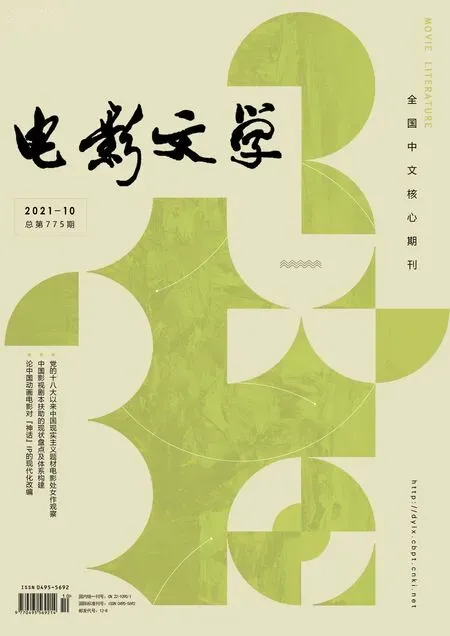檔案、空間與身體:奉俊昊電影中的記憶
王 燦
(武漢輕工大學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23)
電影是一種共時與歷時的集體創作,觀眾在觀影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導演所設置的鏡頭,也隨著導演對劇情的走向而框限在一個被建構的文本里。然而,觀眾要如何在觀看影像的同時喚起自身的記憶,或對一種不曾經歷過的事件產生共鳴?韓國著名導演奉俊昊利用了空間、檔案喚回過往熟悉的記憶,使其成為某種可見、可形塑的存在,通過影像的再現,重新展現一段新的記憶。電影的語言建立在電影創作者與觀眾共享的符碼上,電影文本不再只是一種影像生產與解讀的記憶,在一定程度上是觀眾和作者自身解讀與共同合作的作品,因此影片成為一種開放性文本。
一、記憶圖騰:檔案與媒體
歷史記憶如何被重塑?集體記憶要如何被喚醒?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論集體記憶》中認為,人類的記憶在集體情景中才能發揮,其情景可以由重大的社會性紀念日喚起,也可以由家庭或一群人對過去重大事件的述說喚起。《漢江怪物》片頭在太平間傾倒化學物料的場景,是映射2000年韓國環境監視團體所揭露的一個真實事件。雖然奉俊昊利用這一事件去創造一個虛構、玩笑式的故事,但它的存在在這里也是作為一個提醒過去的事件如何用一個不可預知的方式重返并影響到現在。在電影前段,怪物爬上陸地造成一場大規模的傷害,在之后集體葬禮的大廳現場里,我們看到一片混亂場景:主角們哭喊、打架、摔倒,在這些嘈雜聲的背面,廣播聲呼叫著違停車輛的車牌,請車主將車移開。針對這一段混亂、喜劇與悲傷交錯的畫面,奉俊昊說道:“我想做一組連續鏡頭,包含悲傷、幽默、古怪以及一種超現實的怪異感。我認為這就是韓國的現實,韓國已經發生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超現實災難。”奉俊昊對這一場景的安排,無非是想喚起許多過往韓國人所熟悉的創傷記憶。如:1994 年圣水大橋的倒塌、1995 年三豐百貨倒塌事故、2002年兩名韓國女學生遭美國坦克車輾斃等。而《殺人回憶》則是通過警察調查無果的故事,將悲痛的對象指向死亡的受害女性,同時也指向其時代本身,使華城這個地區成為一個韓國人民的記憶之場。
韓國影評人全鐘鉉在評析《殺人回憶》里提及:華城連環殺人事件的“回憶”作為一段眾所周知的歷史,影片試圖通過歷史事件的再現,重構與重探一個歷史性檔案、一段當代歷史的可能。影片為記憶建立檔案,其中包含了回憶的排斥與遺忘的運作,然而,歷史的記憶要如何重現或再現于影像中?奉俊昊的影片里,利用了“檔案物品”的建構重現歷史的當下,并在劇情中成為對同時代政治、社會的反思,物品成為回溯記憶的媒介,也成了韓國意象的表征。
(一)檔案文件:歷史記憶與再現
集體記憶指向時間維度,聚焦于集體層面上的過去,重視記憶的傳承延續與發展變化,關注群體記憶如何被選擇與建構。《殺人回憶》以特定的歷史時期作為背景設置,隨著案件的調查發展可能涉及某種歷史研究。影片中偵探故事的過程成了一個失敗的歷史研究模式,而警察也就成了失敗的歷史學家。因此,雖然影片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案件,但它同時也打破了歷史記憶的可能性。盡管影片提供了類型的骨架,并融入真實故事,隨著調查的失敗,類型框架正逐漸被拆解,而遵循偵探敘事的動力也逐漸消散。全鐘鉉提到,影片的最后,暴力犯罪不再作為創傷的替代品,而是作為懷舊的對象,不僅因為謀殺本身以某種方式回溯,并因為它們標志著過去的調查發現和歷史記憶似乎是可能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檔案熱》(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
,1996)一書中指出,雖然檔案無法讓我們回到真實過去的當下,卻能給予我們 “碰觸過去當下記憶的可能性”。在《殺人回憶》里,充斥著檔案、成堆的文件、照片以及在調查過程中所尋找出的各種證據,奉俊昊將各種“檔案”加入劇情中,以“歷史證據”去重構“新的記憶”。在《殺人回憶》電影的開頭,主人公樸斗滿在排水溝下發現第一位受害者時,畫面所浮現出的日期是1986 年10月23日。電影最后,警察曹探員在執行截肢手術之前,樸斗滿代替他的家人簽署手術同意書,鏡頭捕捉了同意書內容,其日期是1987年10月20日。在這一年的時間里,奉俊昊在電影中利用案件調查的時間順序,將各種文件、報紙用特寫來取代時代的寫實性,以景框來成為觀眾的閱讀文本。在一連串的調查與失敗的循環中,文件日期的顯現也提醒了觀眾一個事實:從第一個案件開始到結束,顯示出調查案件的證據缺乏與破案失敗。
雖然在電影里不能完整地提供可靠的調查事實,但在影片中的日期通過新聞、媒體等影像的呈現提供了時代的規律性,將過去已經不可挽回的記憶重新存檔。在警察局長第一次出現的畫面中,鏡頭拍攝了局長手上的《朝鮮日報》大篇幅報道了華城的殺人案件,凸顯出這一偏遠鄉村的事件已成為全國所關注的焦點,而報紙上方也顯示出日期,是在案件發生近一年之后,案件陷入膠著,而警察的調查似乎沒有任何進展,此時的時間呈現似乎更凸顯了警察的無能。本內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從共同的語言與民族的建立的關系,進一步解釋了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是促成了民族這個“想象的共同體”,特別是報紙,因為當原本尚無關聯的人,由于閱讀了同一份報紙、看見了相同的內容,便開始關注其所提供的資訊,開始產生同樣閱讀的彼此是共同體的想象。他指稱報紙創造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群眾儀式,也就是說閱讀報紙就如同儀式般,在不同地點被同時的閱讀、消費進行著,產生一種“共時性”的認同。觀眾通過鏡頭看著影片中局長看報紙的模樣,當鏡頭切換至報紙內容時,觀眾成了最直接的閱讀者,報紙的出現提供了“想象共同體”一種再現的技術,使得觀看影片/報紙的當下,觀眾會認為自己身處在同樣的時空背景里。
此外,錄音也成為另一種媒介、一段口述歷史的物品,錄音帶成了一件被記錄下來的歷史檔案。女警前往詢問案件受害幸存者并使用錄音器材將此對話過程記錄下來,鏡頭特寫到錄音機,緩緩轉動的錄音機成了兇手的象征,幸存者用顫抖、惶恐的聲音緩緩敘說案發的過程,直到錄音機停止,案件敘說結束,幸存者如解脫般轉頭看向窗外。錄音機與角色話語的交織形構成存在于影片的檔案,記錄了口述的歷史當下,而角色所說的“我故意不去看”“如果我看到他,他一定會殺我”兩句話,不僅是陳述回憶過往當下對兇手的恐懼,對應于歷史背景,“他”也成了被投射到20世紀80年代肅穆社會的氛圍下韓國人民的恐懼樣態。在此,錄音帶不僅成了新建立的檔案,而通過鏡頭的特寫、角色的述說配合著錄音機轉動的畫面,如同歷史檔案播放的當下,輔助了過去記憶的重返。當鏡頭切換到錄音機錄制結束停止的當下,我們回到了影片敘事的當下時間,這段聲音檔案成了影片所記錄的檔案。
奉俊昊利用檔案記錄呈現的方式,以反向思考批判了歷史的真實性,尤其是案件的20世紀80年代背景,時代的歷史是通過口述與文字所記載而得知并流傳,對于歷史記錄抱以“真實”而客觀的想法。然而,“歷史總是通過記錄者的想法被折射”。也就是說,檔案或是歷史性影像在影片中成為導演詮釋下的物品,比起觀眾、角色本身的主體記憶,只是某種事物遺留下的物質性痕跡,雖然容易引起觀看對象的詮釋再現,但又因為其物質性的痕跡與歷史的聯結,反而讓觀眾感受到被意識形態建構的痕跡,在接收的同時也可能存在不同時空背景下被無限翻轉、再解釋的可能。
(二)再現的記憶:媒體與相片
媒體作為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發展的一環,在數碼技術的進步下,社會充斥了手機、監視器、相機等可攝影的機械,而被記錄的影像成了一種歷史的檔案。有趣的是,奉俊昊的影片里看不見韓國近年來的社會高度發展景象,而存在影片中的現代化科技產物,在電影里最終卻也未能破案。在《殺人回憶》里,最重要的DNA證據,韓國當時并沒有相關的檢測儀器,必須送往美國,但最終卻也未能成為破案關鍵;《漢江怪物》中,主人公弟弟樸南日通過GPS定位系統找到侄女賢書所在地,但最終賢書仍死于怪物之手;《母親》中母親找尋破案關鍵證物的科技產物(手機),然而,卻也無法成為辯證的佐證;而以現代社會作為背景的《綁架門口狗》,卻也因為人性的貪婪,最終“現代人”褪去其外衣,回到如動物般的野蠻、原始本性;在《潮流自殺》短片中,奉俊昊以監視器的畫面構成一個故事,將現代社會下的潛在問題顯露出來。通過監視器影像我們可以看到一名原先努力工作的男子,面臨挫折而導致他走向搶劫、殺人一途。監視影像的呈現如現場直播般,我們觀看著一個人的遭遇,這是存在于現實社會中,亦是我們周遭的人。
在奉俊昊的影片中,“肖像照片”成了重要的物品,而這些攝影相片也都成了敘事附加的重要影像。攝影的真實性各有其時代意義,對于攝影肖像的呈現,透過物質性的留存,檔案才能成為建立集體記憶的根本。中國臺灣學者林志明指出:“攝影在社會體制及社會用途中的變化,攝影肖像作為一個形式類型,其變化軌跡主要是由公眾性領域朝向私人領域的過程……攝影肖像的歷史從一個指認功能(identifying)走向認同功能(identification)。”“攝影肖像最早是被用于警察拍攝犯人的肖像照片。其大量的犯人照片變成一個巨大的檔案……在指認功能的過渡中,它代表的是社會身份控制過程中視覺成分的整合。”檔案作為一種歷史再現的科學證理,而照片在影片中成為一段捕捉攝影當下的時間殘存。
假設在《殺人回憶》中的肖像是一種傳統的指認工具,到了現代發達的攝影技術,照片被數字化,可以更精確地看到細致的細節,可以被放大、修復,照片的真實性引發了質疑。在《母親》里,伴隨數字技術的進步,照片可以再制、再修飾,將丑陋的細節遮蔽。當照相館老板娘回想起被謀殺的女孩想將她手機的照片沖印時,劇情開始另一個敘事轉折與傷痛的循環。
回到初始的肖像功能,歷經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指認功能依然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作用。然而,借由數碼的修復,指認功能的真實性產生矛盾,更能扭轉成造假的工具。《母親》中被殺害的女孩手機的照片,成為潛在的報復和勒索的工具,在女孩生前,這些照片是她的傷痛的回憶記錄。死后,替代成母親調查兇手的指認證據,更是母子成為共犯的工具。在影片中,手機成了一個有趣的物品。相對《殺人回憶》的案件調查方式,《母親》展現了一種科技進步時代,使得調查方式多元甚至更容易處理,而象征現代產物的手機更是人手一個,一般民眾也能當起偵探或創造一則新聞話題。進步的時代使得社會結構被改變,也就凸顯出其中所隱含的罪惡愈趨增多。因此,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科技如何變成暴力物品或共謀的一部分。
二、隱喻的場域:景觀與空間
電影中的許多物品,包含場景、角色與物質性的物品等,在影像中不僅作為敘事的一環,亦是作為時代產物下的變革痕跡,尤以場所、景觀作為塑造時代氛圍的主要要素,場景不僅作為記錄的物品,同時代表了社會與文化空間轉變。特定的空間和地理形勢都與文化的維持關系密切。這些文化還不只牽涉明顯可見的象征,也涉及了人群生活的方式。電影空間場域的建構對于電影敘事的構成在于敘事的表達方式,依照敘事的結構安排情節、人物特性、組織對白、建構沖突等,而空間性的視覺結構將影像、劇情等要素之間的關系重新調整,成為敘事背后的邏輯與寓意。
在奉俊昊的影片里,景觀的鏡頭有一定分量的存在,這些景觀都是已被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倉促進度所重創:韓國迅速萎縮的自然景觀,如山嶺、河流、農地、藍天、森林等,這些經常占據了奉俊昊電影的想象,構成了他電影敘事中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殺人回憶》與《母親》中的非都市場景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殺人回憶》更是奉俊昊努力去重現20世紀80年代韓國尚未現代化、發展相對落后的鄉村景觀的結果。在現代化背景的偏遠地區,奉俊昊采用廣角鏡頭去描繪整個城鎮或鄉村的景觀。為能使時代的氛圍呈現于鏡頭前,并與敘事內容相融合,奉俊昊采取了時代場域與現代化空間作為記憶再現的空間,他試圖通過這些景觀與空間的呈現,從中顯露其背后的象征寓意。
(一)現代化的工業景觀
以20世紀80年代作為敘事背景的《殺人回憶》,除了揭示軍人政府獨裁期間的韓國社會暴力,同時通過場景的呈現,巧妙地暗示韓國邁向經濟成長與現代化付出高昂社會成本的代價。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雖然呈現出一個先進的現代化進程,然而社會不公與專制現象蔓延、惡化。這時期的電影開始出現反現代、反西化的民眾群體與意識,不見現代化光明的一面,更多凸顯出現代化背后的不堪樣態,電影成了創作者意識形態斗爭的宣泄。如樸光洙的《黑色共和國》,凸顯20世紀90年代前后韓國勞動市場的現實狀況;《美麗青年全泰一》,則通過處在狹小工廠空間的女工情景,利用過去和現在互動的結構,反省了勞工的境況。
廣義來說,現代化在實質上是西化的進程,是18世紀西歐的資本主義工業背景下建立理性、共和的文化,創造一個“進步的世界”。但比起西方人民而言,非西方的人民對現代化產生的矛盾感在于“現代化等同于西化”這一事實帶來復雜的影響,比起表面的現代化發展更令人困惑。而對韓國人來說,可能更相信現代化即是認同“西化”。在種種尚未適應的變革環境下,出現了資本家與勞工、統治和反抗、東方和西方、傳統和現代、過去與現在的矛盾對立。
1988年漢城奧運之前,國家把當地社區夷為平地的“美化活動”后,政府對居民的唯一補償就是漢江攤販的經營權,從《漢江怪物》主人公樸氏一家的生活與工作中就可見到歷史痕跡。背景為現代城市的《漢江怪物》,鏡頭卻集中在主人公樸江斗一家的狹小店鋪以及漢江下的下水道,現代化的城市景觀幾乎沒有出現在影片內,唯一出現的城市景象,是在樸氏一家各自逃離分散后,我們看到站在馬路邊的民眾,各個戴著口罩抬頭看著電視墻上的新聞,接著隨著公車的經過鏡頭轉換到坐在公車上的樸南日,隨著他的視線我們看到了窗外聳立在夜晚的大樓,接著在別有目的的友人“幫助”下進入大樓內。奉俊昊說道:“在拯救賢書未果、樸江斗的父親死去后,我想我們得到了無助的感覺。當他們分散后每個人都受到考驗。這是我們第一次從漢江脫逃,我們突然看到市中心,南日的出現像個犯人似的在奔跑。當他戴著口罩走到城市后街,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和氛圍展開,仿佛剛剛發生的事件是不存在的。”奉俊昊短暫地將城市景觀呈現,但樸南日最終只能靠自己,并狼狽地逃離大樓,再度回到漢江下水道。在此,漢江就如一個“收容”無法適應現代城市的人的場所,令人聯想起“漢江奇跡”,雖然帶動了韓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卻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如漢江的環境被破壞,其代價是造成了一只怪物的誕生;首爾雖然從廢墟中發展成為現代大都會,但漢江也成了現代化的犧牲品。
將時間拉回到20世紀80年代,《殺人回憶》的背景正是韓國社會轉型的時代,我們看到影片中的鄉村地區逐漸有了工業化的痕跡,如廣大的采石場與嫌疑犯樸賢奎所工作的工廠。農業村落與工業建物構成了對比強烈的地景。這些地區本身與其時代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在地居民開始脫下農裝、穿上工作服進入工廠工作,從農民變成勞工。這樣的工作轉向意味著整個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改變:現代化的進程,使韓國步入轉型而有越來越多人成為勞工。在資本勝利的傳說底下,是以勞動來支撐現代的工業都市。
在一場三位警察追逐自慰男子到采石場的場景,一個長鏡頭將夜間寬廣、巨大的采石場呈現:粗糙、灰白的空間,數以百計的工人穿著同樣的黑色衣服在采石場穿梭、勞動,這些勞工成了無特征的無名個體,如無身份的群像展示。冷漠、機械式的動作氛圍充斥于工地,大量的燈光照射群體、灰白的石壁將工人包圍。這幕場景以群體景象的勞動來凸顯社會轉型所形成的氛圍,進而與悠緩的農村印象形成對比。在經典論述中,馬克思提出人的身體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中,被異化成機器,失去了人的主體性、控制權;而在精神分析的探討中,經常將人對身體的認同看作是人建構自我的關鍵要素。人物身體是構筑電影中角色主體特性與不同背景下所產生的相異形體,這種空間與人物的隱喻關系,就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所描述的,當越來越多人被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越來越多令人厭惡和攻擊變得越加野蠻、冷漠,每個人變得極度無情,或是變得歇斯底里。如《漢江怪物》中與怪物曾經接觸的人們,被認為是具有高度傳染性疾病,而被強迫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甚至進行“消毒”。
由于現代化,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人們在工業化的環境中工作,使用先進的技術,居住在城市或郊區,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巨大變化愈趨復雜。但在現代性的轉型過程中,必然存在各種事物的矛盾與沖突,奉俊昊以現代化的工業景象,將案件、時代氛圍做一個巧妙的聯結,同時也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消極影響,如對政府的不信任、重視利益與發展所帶來的階級界限、環境被破壞的危機、人性因環境變遷所產生的影響等,伴隨因其產生的各種矛盾,在某些部分上可能否定了現代化所帶來的成果。
(二)光明背后:地下的黑色空間
對奉俊昊來說,20世紀80年代的華城,在《殺人回憶》里揭露了現代化發展的不足與警察部門的束手無策,在這種時空空間的架構下,人們的死亡成為一種無可避免的狀態,悲傷的歷史敘事只能以失敗告終。在《殺人回憶》中的謀殺和死亡的發生,不僅是因為一個未知的兇手,更廣泛地說是由于空間和時間的影響。因此,隱喻的影像在片中展現出一個國家的失敗,更借由一個“黑色空間”呈現出20世紀80年代荒廢、破舊的排水道與隧道的黑色形態。在電影的第一個場景中,一具女性尸體被丟棄在稻田筑堤旁的排水道中,借由鏡面反射光線才看出身體已腐爛并被無數的螞蟻覆蓋。這樣的影像在電影后半段再次出現:時間來到2003年,當樸斗滿已卸下警察身份而再次回到電影第一個案發現場,當他再次往排水道中望去,里面沒有尸體,鏡頭緩緩推進、往排水道另一端前進,如火車隧道中,望向過往,重新找尋那段無法抹去的挫敗記憶。
情節告知故事行為者相關的環境、所處位置和行動路徑,將有利于我們對故事空間的建構。這些影像賦予了空間新的寓意,透過敘事情境與角色的反面行為來構成強烈的對比性,讓敘事情境塑造成一股不安定感,成為潛在的破壞與威脅。在形塑歷史劇變中的現代世界,存有許多清晰可見的景象,包括原野、農村、郊區、工業城市。而電影中所描繪出都市對自然的依賴性以及生態的破壞(森林、河流),運用剪接與鏡頭的連接,構成多層次的空間意義,如工廠、巨大采石場成了國家權力的權威象征,現代化的痕跡在場域的隱喻中受到另一面的沖擊和改變。而在現代城市里,怪物的誕生是恐怖的重生,它顯現了人與自然、自然與工業之間不再加以區分,當工業從自然中提取原生物料,然后再將其垃圾投入自然中,這種循環的方式掩蓋了人類、自然和工業各自獨立的存在,怪物的出現揭示了現代化背后的復雜結構,漢江的純粹被轉化成矛盾與曖昧的存在。“黑色空間”調和了奉俊昊對于過去與現代的韓國歷史觀點,這些工業化、城市破敗的景象在犯罪、驚悚、神秘、恐怖、喜劇等元素里,利用類型化的敘事,重新設置出另一面的記憶再現與情感。
三、歷史傷痕:有缺陷的身體
在迎來21世紀后,韓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借由影像來批判現代化、工業化、社會動蕩與民主抗爭的電影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后的科技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矛盾與金錢至上的資本社會。如奉俊昊的奧斯卡獲獎影片《寄生蟲》,表現韓國現代社會變化不定的樣貌,后工業社會的生活是憔悴、繁亂和迷惑,不同階層之間充滿分崩離析的癥候,影片對現代性和不平等階層的抨擊,更準確的是冷嘲熱諷,對現代化強而有力的反話語。
奉俊昊的影片中幾乎都會存在一個“智能障礙”的角色,不管是《殺人回憶》的白光浩、《漢江怪物》的樸江斗、《母親》的泰宇還是《寄生蟲》的基宇和前任女管家丈夫,這些角色缺陷的身體狀態不僅成為易于被頂罪與誣陷的身份,更是劇情中隱藏的靈魂人物。
《殺人回憶》中被當作案件嫌疑犯的白光浩,從其臉面的燒傷痕、唯唯諾諾的說話方式以及總是微微駝背的身體,讓人對他產生同情弱者的心態。在影片里,他是個手無寸鐵、被警察毆打的平民,似乎在權力底下,他只能乖乖地承受。最后,他第一次起身反抗,是拿著木條朝向毆打大學生的曹探員,并使他的毆打結束。在兩位警察拿著樸賢奎的照片要白光浩確認兇手長相時,白光浩睜著眼看似仔細地觀看,卻又像并未聚焦于此,而后將視線移開照片,緩緩地說出:“你知道那有多熱嗎?你知道那火多嚇人嗎?”“在我小的時候,那個人把我丟到火里。”白光浩轉向旁邊,鏡頭隨著視線移轉,白光浩的父親從遠處跑了過來。在這里,我們可以得知其臉部燒傷的來由,而在說話的同時,父親的出現似乎暗示著這場火與他有關。然而,我們無法進一步知道這場火的來龍去脈。白光浩突然吹著哨子跑向了火車,并對著跑向他的樸斗滿用柔弱的語氣叫他離開,下一秒,白光浩遭火車撞上身亡。白光浩的死亡代表了兩件事的終結:奸殺案件與軍事時代。唯一看過兇手面貌的白光浩,對他來說看到犯罪過程或兇手是誰并不重要,因為身處那樣的時代,就像習以為常的事情,是個暴力者與受害者每日共處的情形。當他第一次起身攻擊暴力者(曹探員)的時候,結束了專制的政治,而他也如同對抗軍隊而犧牲的民眾般,與那個時代一同共生、共滅,卻也是一個時代真相的消失。他站在鐵軌上吹著哨子警示樸斗滿不要接近的行為,或也暗示著新一場反抗將起。
與白光浩相似的身體狀態,亦出現在《母親》的角色里。兩部電影皆以“智力障礙”的角色作為劇情中的重要人物,但在《母親》中的泰宇卻與唯唯諾諾的白光浩相反,泰宇是個充滿自信的角色,卻也相對冷血,在犯下殺人案后,仍像是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與白光浩相同的是,泰宇回憶的過去也是被傷害的過往,白光浩選擇埋藏真相,泰宇則直白地揭露事實。在此,泰宇缺陷的身體狀態緣由明朗,以堅定的眼神與話語將這股罪惡嫁接到極力隱瞞事實的母親身上,至此,兩人成了共生、共謀的犯罪者。母親弱小、年邁的身體在電影里幾乎身處一個充斥陰暗的空間,不管是充斥藥材的店鋪還是與泰宇的居住地,這些黑暗空間被塑造成母親的基本生存空間以及他們那些人最后生活的事實。而在電影最后,其遼闊的草原風景與前面狹窄、封閉的空間形成巨大的反差,母親的身形如倒影般虛幻,不復存在。母親為拯救自己的兒子離開罪惡,卻使自己愈趨身陷到如人間地獄的生活。
而《漢江怪物》中的樸江斗,是白光浩與泰宇的綜合體。樸江斗在影片中是一個父親的角色,但與《母親》中的母親形象又不同,其呈現的是一個無能、無知、懶惰的角色,像是韓國一個后工業時代的韓國人物形象,不僅牽錯女兒賢書的手導致賢書被怪物抓走,并錯算子彈數量讓父親死亡,還成為國家實驗團隊研究怪物感染的實驗對象,抽血、解剖、植入,他被當成一個實驗物體而不是一個人類。達西·帕奎特(Darcy Paquet)認為《漢江怪物》中的每一個角色可以被看作是代表過去十年不同的韓國歷史樣貌:樸江斗作為大家長,一個樸實、維護家庭的20世紀60年代的家長,在貧窮的生活中努力地養育自己的家庭;江斗,一個精神上出現創傷的中年男子,在20世紀70年代的政治下被迫害的人;南日,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學生街頭運動丟擲汽油彈的經驗者;南珠,20世紀90年代,缺乏信心而無法展現自己實力的射箭選手;賢書,一個21世紀10年代勤奮、聰明的中學生。這些角色被放到大時代的隱喻下,樸氏三兄妹的表現成了奉俊昊真正的想象實踐,代表韓國真正的草根人民。當三兄妹的父親被怪物殺害后,他們不再如20世紀80年代與20世紀90年代期間,樸光洙和張善宇等老一輩導演所回應的歷史:以嚴肅、審慎的憂郁姿態來面對創傷、歷史浩劫、國家與家族的喪失。
這些有著“缺陷”身體的角色,在影片中是一個時代、社會縮影的象征,在奉俊昊的影像里,缺陷的角色更接近現實的人物,一種在社會背后不易外顯的迫害、創傷。身為新一代導演的奉俊昊,擺脫了身陷痛苦的現實,在電影里刻意避免與現實做直接的對抗,而是借由這些角色,將其身體作為一個重構集體記憶的影像,讓其身體成了人民的行為事件,去回應在現代語境下的歷史記憶。
結 語
依循哈布瓦赫的說法,集體記憶一種是用來重建對過去的意象的工具,來傳承、延續或發展,是建構群體認同、文化凝聚與個人對社會的體驗,與個人相比更為廣大的力量。檔案作為歷史記錄的物品,奉俊昊利用再造的檔案重新喚起過去的記憶;同時,這些因應時代的重顯而被制造的檔案,也成為影片拍攝當下的檔案。這種曖昧的形塑不僅通過時間日期試圖讓檔案重返過往,并使得影片本身成為被記錄的檔案,就如德里達所論述,檔案的建構具有遺忘、解消、摧毀的死亡驅力。奉俊昊借由檔案的創建來召回暫時被大眾遺忘的記憶,再以這種非真實的檔案來銷毀受到過去掌權者所建立的記憶。
在空間的建構模式也是相同的。電影的場景不僅記錄當下的樣態,同時又顯示社會過去與現代之間轉變的痕跡,特定的空間和地理形勢都與文化的維持著密切關系,同時也涉及了當地人的生活方式。通過導演的配置,客觀的空間就成了被詮釋成不同樣態的場域。電影的空間建構對于電影敘事構成的挑戰并不在敘事本身,而在于敘事的表達方式,通過情節的安排、角色人物的塑造、角色對白話語以及建構戲劇沖突來接合電影的完整性。因此,空間就成了視覺建構的重要元素,不同的空間結構將重新調整與解釋其意義,并且企圖去重新將過往記憶納入當下的空間。在追溯某種記憶的空間場域中,人物成了賦予空間解釋的重要角色。前文曾提及,奉俊昊將人民的生活景象來形構成一個時代的顯影,因此空間與人物被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若以個體來論述,人物自身的身體狀態就成了另一種記憶表現。身處韓國時空背景的人物,其不可避免地成為某種歷史的隱喻借代。
奉俊昊讓身體或生理上帶有缺陷的人物出現在他的每一部影片中,成為奉俊昊某種角色形構的特色,這些身體缺陷的人物貫穿了影片的敘事走向與關鍵,體現了屬于韓國歷史的具體化。韓國學者徐南同認為,因為地緣政治與歷史關系,韓國的民族特性建構在“恨”之上:“韓國人從日本殖民統治、毀滅分裂的朝鮮戰爭和戰后嚴重依賴外援的精神狀態中恢復過來后日益覺醒的自我意識和自尊。”這種民族特性被建構在身體缺陷的角色身上,奉俊昊將其納入時代之中,讓人物在過程中回憶,顯露出歷史記憶與時間的關系、遺忘與記憶的關系、現實與記憶的關系等,重構與反思大時代之下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