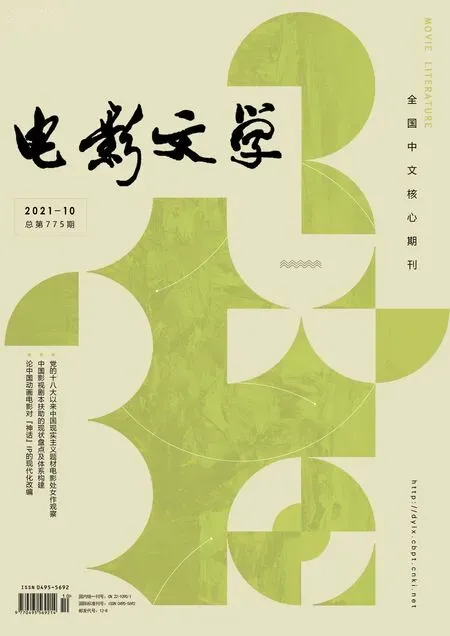作者論視域下的新海誠動畫電影
朱 虹
(南京傳媒學院動畫與數字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0)
在日本動畫新生代中,新海誠無疑是突出的一位。自2002年創作《星之聲》始,新海誠就開始牢牢把握在動畫創作中的主體地位,展現其獨特的電影藝術風格,為電影打下鮮明的個人烙印。同行與觀眾都能夠清晰地從其作品中辨認出他的藝術風格,個體思索、感悟和審美偏好。毫無疑問,新海誠是其電影當之無愧的“作者”。同時,新海誠的個性化表達已不拘囿于“新浪潮”團體為“電影作者”劃下的狹隘范圍。他的藝術堅守和與時俱進,對于中國電影,尤其是中國動畫電影而言,是有借鑒意義的。
一、從“小宮崎駿”到“新海誠”
新海誠的職業生涯,經歷了他人對他的認識從“新津誠”到“小宮崎駿”,再到“新海誠”的過程。新津誠為新海誠的原名,在大學畢業后,他以自己的原名進入日本知名游戲公司Falcom,負責平面設計與宣傳工作,同時也接觸了美工、動畫等工作,在業余時間完成了《被包圍的世界》等三部短片創作,這一段經歷為新海誠成為電影“作者”奠定了基礎。在發現Falcom的工作與自己的愛好無法兼容時,新海誠選擇辭職,并創作了一鳴驚人的《星之聲》,也因為電影的畫面靜美、情感細膩而獲得了“小宮崎駿”的稱號。但人們很快發現,兩人在技術傾向、故事杜撰、審美目的、畫風等方面都大相徑庭,他開始真正以“新海誠”為人們熟知,而到《你的名字》大獲成功之后,世界更是掀起了“新海誠熱”,人們終于注意到了他作為動畫電影“作者”的身份。
作者論(the auteur theory)最早來自1948年由法國電影人阿斯特呂克撰寫的《攝影機——自來水筆,新先鋒派的誕生》。阿斯特呂克認為:攝影機猶如作家的筆,應該體現著電影作者的自由創作意志。這一主張很快得到特呂弗等人的認可和補充。導演對電影的絕對支配地位得到肯定,并且如果一個導演能夠“選擇個人化的元素作為相關的尺度,然后將其持續永恒地貫徹到一個又一個的作品中”,即反復用電影來彰顯自己的思想與藝術個性,那么他就可以被稱為電影“作者”。盡管數十年來,關于作者論這一電影藝術批評方式始終爭論不休,但確有不少導演可被認為是典型的電影“作者”,他們將自己的意念、情緒與思考運用在電影中,劇本僅僅是編劇(或原著作者)提供給他們的題材,在搬上銀幕的過程中,導演會根據個人視野來主導電影的劇情甚至主題。
就日本動畫而言,如宮崎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生,經歷了戰后日本的衰敗與貧瘠,始終以動畫來反映自己對宏觀主題(環保、反戰、女權等)的思考,堅持水彩等手繪,在《千與千尋》等作品中呼吁人類的善良、和平與愛。這些是其他動畫人難以復制的,也是人們在比較宮崎駿與新海誠等人的作品時能輕易識別出來的,宮崎駿就是一名電影“作者”。而同樣,新海誠也在其作品中處處留下了自己作為“作者”的痕跡。
二、新海誠動畫中的作者身份痕跡
綜觀新海誠的幾部作品,不難發現它們在主題的選擇、影視語言的運用、意象的設置等方面都有著屬于新海誠的“個人化的元素”。
(一)主題選擇
在主題選擇上,新海誠幾乎一直選用“距離”為主題,男女主人公的孤獨、愛和成長等,都是與距離息息相關的,他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了自己對距離主題的偏愛。如在《她和她的貓》中,貓和女主人之間存在物種上的距離,貓作為“他”盡管具有豐富的情感,但是無法以人類能理解的方式表達,在女主人絕望地喊出“誰來救救我”的時候,“他”是無能為力的;在《星之聲》中,美加子則因為加入了宇宙軍離開地球而與阿升的距離越來越遠,以至于在自己犧牲多年之后,她發的消息才傳到地球;《秒速5厘米》中,貴樹和明理因為轉學而與對方越來越遠;《言葉之庭》中,秋月孝雄和雪野百香里之間不僅有著十二歲的年齡差距,而且還有著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身份距離;在《追逐繁星的孩子》《你的名字》中,人和人的距離除了時空,還包括生與死。在這一主題下,新海誠得以充分關注當代人的生存處境,對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進行創造性的言說。在新海誠看來,科技的進步并沒有緩解人和人之間的疏離感。在宮崎駿電影中絕少出現的軌道交通、網絡、手機等,在新海誠電影中比比皆是,但它們并不意味著人身心距離的縮短,在新海誠看來,人的生命因距離而充滿沉重。但距離又并非不可逾越的,人強烈的情感是戰勝距離的關鍵。在《言葉之庭》中,雪野主動撲向了孝雄,承認是對方給了自己前行的力量。在《你的名字》中,兩個彼此找尋的人甚至改變了歷史,讓宮水三葉和村里的人活了下來,三葉與立花瀧也終成眷屬。可以說,在新海誠的作品中,盡管題材、世界觀和結局是各有不同的,但距離主題是一以貫之的。
(二)語言運用
就影視語言而言,由于對榮格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原則有著較為深入的理解,新海誠熱衷于運用“同步性事件”這一技巧。例如在《秒速5厘米》中,當花苗終于鼓起勇氣想對貴樹表白時,偏偏遇上衛星發射,使花苗改變了心意;又如成年后的貴樹與明理在擦肩而過時偏偏有一列火車駛來,遮擋了彼此的視線等。在《共時性:非因果性聯系原則》中,榮格指出:“共時性指的是某種心理狀態與一種或者多種外在事件同時發生,這些外在事件顯現為當時的主觀狀態的有意義的巧合,或者主觀狀態是外在事件的有意義的巧合。”即兩件原本并不相干之事,因為人物的心理狀態而具有了某種聯系性,在人腦的強化下,某種客觀事物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含義,人對于“噩兆”“心靈感應”等的迷信正是源自此。人們預先存在的心理狀態導致了外在事件隨后被聚焦與關聯。而新海誠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創作中先設定了外在事件,以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心理狀態,在電影中建立一種微妙、唯美的情感氛圍。如在《星之聲》中,當阿升收到美加子發自遙遠時空的短信時,正好有一片櫻花花瓣落在他的手上。這便是一種“有意義的巧合”。冰冷的現代科技(衛星、火車等)以男女感情阻礙者的身份,介入原本就心志不堅的角色“有緣無分”的感情中,而凄美的櫻花飄落與短信到來本無因果關系,但它暗示了美加子美好卻短暫的一生,能迅速勾起觀眾唯美、婉轉的情思。
(三)意象設置
作者論認為,電影作者應該在電影中設計某種個性化的“簽名”,如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中向垃圾桶投擲空瓶的老婦、吳宇森電影中的白鴿、王家衛電影中的香煙等,都是導演專門設計的、極具辨識度的作者署名。在新海誠動畫電影中,不少意象也因為反復被運用而具有了“簽名”意義,如櫻花。《秒速5厘米》中,以每秒5厘米下落的櫻花是男女主人公悲劇愛情的重要見證者,十三歲時想著“明年要是也能一起看櫻花該多好”的戀人漸漸為各自的成長所束縛,最終在櫻花飄落的鐵道口分道揚鑣。《星之聲》中櫻花飄落,阿升手機亮起,獲得慰藉。
又如天空、星星和彗星等。《秒速5厘米》中花苗對著被分隔成一半明一半暗的天空意識到了自己與貴樹并非佳偶。在《云之彼端,約定的地方》《星之聲》《追逐繁星的孩子》等片中,或高曠清澈、或黯淡無光、或有陽光穿破烏云、或有夕陽燃燒的天空意象更是數不勝數,分別指向人物不同的心境。在夜空中閃爍的星星、劃破天空的彗星等也在新海誠電影中扮演重要角色。如《秒速5厘米》中男女主人公談到升學問題時畫面中出現的星星意味著兩人未來距離的遙遠與愛情的渺茫,《你的名字》中彗星拉著詭異的彩色尾巴穿過云海,墜向大地,導致三葉與瀧的生死相隔,而彗星分開的軌跡,也象征了三葉與瀧所在的兩條處于非穩態的時間線。在對這些意象的充分利用下,新海誠電影的“物哀”“空寂”審美實踐也得以完成。
除此之外,新海誠在形式上,對于真實場景的逼真還原,對空鏡頭的大量運用,絢爛豐富的色彩等,也都是他的作者身份痕跡,在此不再贅述。
三、從“作者”走向“作者表述”
在我們承認新海誠的“作者”身份的同時,我們又必須注意到,新海誠并沒有拘泥于“新浪潮”為電影作者規定的苛刻條件。如“新浪潮”認為,電影作者“一生只拍一部電影”,不同的作品之間應該建立起強互文性,又如“新浪潮”主張一套反好萊塢式的電影語言,如以長鏡頭、獨白、不規則構圖等來完成自己的“簽名”等,這也就導致部分電影人為彰顯不取悅觀眾的立場,而非某種審美必須而刻意運用前述形式。而新海誠在這方面則靈活得多,他在保證藝術主體自覺性與控制力的同時,并沒有為深化個人標簽而放棄更多嘗試,也并未拒絕接受商業化操作。相對于成為作者論規定的“作者”,這種將自己從成規中解放、剝離出來的方式被稱為“作者表述”。
首先,新海誠在保證個人優先地位的同時,亦日益重視分工協作。電影創作本身就是一項集體性藝術創作活動。如早期在創作《她和她的貓》時,新海誠身兼劇本、監督、制作甚至是男聲配音多職的狀況無疑是不符合電影的工業化生產方式的。于是,在后來的創作中,新海誠除導演與編劇外,不再身兼多職,在組建團隊后,也會視情況更換團隊成員,如與宮崎駿堅持與音樂師久石讓合作不同,新海誠便在《你的名字》中舍棄了一直以來的音樂伙伴天門,改為與日本小眾搖滾樂隊RADWIMPS合作。
其次,在世界觀的設定、在對科技的態度、在悲喜劇基調的設定等方面,新海誠不拘一格,愿意進行多種嘗試。如就在觀眾誤以為走世界觀宏大的奇幻、科幻路線是新海誠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征時,他又在《言葉之庭》中選擇了完全基于現實的小品式敘事。
最后,新海誠并不排斥商業邏輯下的電影套路。以《你的名字》為例,這部對于新海誠奠定作者風格有里程碑意義的電影恰恰又是一部商業語言明顯的電影。如電影充滿歡樂氛圍的前半段中,新海誠設計了搞笑的男女主人公在換身體后互摸對方胸部和下體的情節,又如電影根據情緒曲線嚴格地安排了音樂與情節。在電影第三十分鐘,抒情的音樂出現,第六十分鐘,瀧喝下改變彼此命運的口嚼酒,第九十分鐘,三葉看到手中瀧寫下的“喜歡你”字樣,這一幕讓觀眾淚流滿面。觀眾的注意力和情緒始終被公式化地牢牢掌控。而電影皆大歡喜的結局,也顯然是一種對商業的妥協。電影能取得日本電影史上票房收益最高的紀錄,與新海誠這種在市場面前的靈活性是分不開的。
如果說,被譽為“小宮崎駿”意味著人們注意到了新海誠的“作者”身份,那么新海誠在擺脫這個稱號,以“新海誠”之名為人們所熟知時,才意味著人們較為全面、系統地認識到了新海誠藝術魅力的獨特性。在動畫電影的主題選擇、語言運用、意象設置等方面,新海誠都留下了作者痕跡;同時,我們又注意到,新海誠在立足自身經驗、思考與審美偏好進行一部部電影的創作時,并沒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斷探索著更靈活的“作者表述”的路徑。應該說,動畫人要想在世界動畫之林中占據一席之地,構建出屬于自己的藝術風格,并能根據市場需要而對其適當調整,是極有必要的。就這一點而言,新海誠無疑是有借鑒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