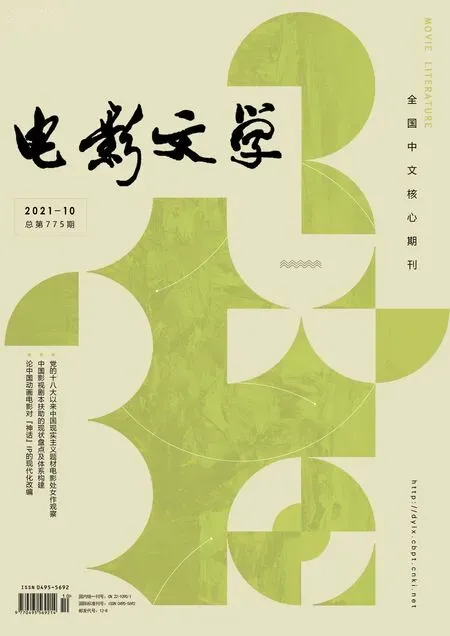閉環、錯位與創傷療愈
——《一秒鐘》元電影敘事探析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重慶 400030)
“‘元’,意味著自體反思,也意味著文本鏈接。”影片《一秒鐘》借電影《英雄兒女》及《新聞簡報》的文本鏈接,進行了多重時代性的元電影建構。在這樣的建構中,主人公張九聲與劉閨女在年齡痕跡抹除的情況下發生了人物關系的錯位,同時于主人公張九聲的人物動作中,得以瞥見斯蒂格勒電影理論中作為“第三持留”的電影制品的“毒性”與“療愈性”。《一秒鐘》中,其元電影屬性從其建構方式進行闡釋,既生成了影片中人物關系的錯位和人物與其所處環境的心境對照,進而衍生出對柏拉圖“理式世界”及元電影閉環建制之下的回環反思。
一、“閉環”與“錯位”之下的元電影
(一)互文、閉合與想象性和解——建構之本
所謂元電影,是在一部影片中折射其他影片或電影特質的電影形式,即“關于電影的電影”。《一秒鐘》借《英雄兒女》,探討了時代中電影抑或膠片在特定社會條件下的文化及社會功用,既是元電影對電影特質的特定折射功用顯現,又塑造出了范電影及群眾這類典型的人物角色形象,完成大環境的擬真構筑;而所謂閉環,又稱“反饋控制系統”,即在物理學意義上,將系統輸出量的測出值與所期望的給定值進行比較,由此產生偏差信號,并通過偏差信號將測出值一步步加以修正的系統。影片中,諸多符合格雷馬斯語義矩陣的人物關系模式構成了這類得以符合元電影建構的閉環“開關”,同時對元電影模式進行了閉合性建構。
“電影互文性是元電影的特征之一, 元電影通過電影互文性實現言說和回憶自身。”影片中元電影屬性與閉環模式的構筑幾乎是通過《英雄兒女》與《一秒鐘》的內在敘事同時進行的。首先,在元電影的物質載體——《英雄兒女》的幾盒膠片尚未被送到“二號場”時,便是通過劉閨女想要為弟弟做燈罩而對膠片盒的竊取聯結了與張九聲的人物關系,格雷馬斯語義矩陣中的“迷影者”與“反迷影者”嶄露頭角。此時既是元電影建構的第一塊“碎片”,也是整個閉環建構的第一步。
其次,在兩人不斷地摩擦沖突之后,二人來到“二號場”,并遇到范電影,將膠片盒交給范電影,而范電影因膠片盒的來源對張九聲產生了懷疑,進而提取出范電影“非迷影者”的角色實質,即與張九聲有矛盾,但并不完全對立。加以群眾對范電影的態度及電影無法播放時的群體反應,元電影的建構幾乎已經完成,而閉合“開關”也即將形成。
最后,在影片《英雄兒女》播放之前,張九聲完成了與劉閨女的想象性和解,同時對范電影坦白自己是“越獄犯”,故植入了“保衛科”這一“非反迷影者”。在張九聲不斷觀看自己女兒影像的“大循環”時,“保衛科”的抓捕行動使得真正的閉環得以完成,同時在張九聲與劉閨女一同被“保衛科”綁在大廳觀看影像時,影像對二人的影響產生了完整的共情——張九聲女兒的影像及劉閨女弟弟的燈罩。自此,元電影的建構宣告完成,而閉環成為元電影的一種補足與修正,同時也迫使元電影的建制宣告結束。
(二)內在現實、身份認同與時代的錯落——元電影建構的反身性
《一秒鐘》與《英雄兒女》在文本意義上是對張九聲及其女兒父女關系的一次錯位展示,也是對劉閨女平等關系的善意編織。元電影及其閉環建構的完成進而對影片的精神世界進行了一次多重意義的錯位表述。
首先,是作為元電影內在現實的錯位。在《英雄兒女》中,王政委和女兒王芳最終相認,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而于元電影之外的張九聲,卻和自己的親骨肉經歷了“生離”,以及最終的“死別”。謳歌革命英雄的《英雄兒女》完成了一次影像意義上的團圓,而這樣鼓舞人心的革命事跡卻凸顯了張九聲和劉閨女的悲情之景。在觥籌交錯的“大循環”時光剪影中,張九聲獨自一人坐在大廳中,虛幻與虛幻、現實與現實不斷交織,繪制了一幅時代洪流沖擊下的個體哀景。錯位的不僅是《新聞簡報》中女兒與王芳的身影,也是無端成為“壞分子”的張九聲與革命英雄王成的想象性體認。
其次,是張九聲與劉閨女人物身份與關系的錯位。生理年齡,作為個體的直接外現屬性,自始至終都是意識形態對主體規訓或詢喚的重要部分。年齡通常是對個體身份、地位、職業的指認,同時也是區分生理層級的一類適當標準。在《一秒鐘》中,年齡除了在展現“荒漠”般的大環境之時有一定程度的“擬定父女關系”的討論之外,在元電影開始建構之后,作為張九聲與劉閨女主要人物的主要特征被象征性抹除,進而二者的關系必然也變得純粹。介入“迷影者”與“非迷影者”的對立關系后,影片圍繞二者建構了元電影的閉環設計,而只有當元電影及其閉環完成,甚至在張九聲“釋放”后,二者的年齡指認才有所改變。影片結尾不僅是兩位主角生理年齡的回歸,亦是大時代下社會生活回歸的一種集體式寫照。正是于這樣的集體背景之下,年齡體認被歸還給張、劉二人,才有了關系上的錯位與突圍。洗凈面孔的劉閨女和張九聲既像是《英雄兒女》中相認的王政委與王芳,又有著情愫暗生的畫面隱喻,在元電影及其閉環建構之下,錯位就此生成。
最后,人物于閉環下的錯位與元電影的閉環建構使得影片的敘事中漸次拼貼出時代的錯位。《英雄兒女》主要內容是歌頌革命英雄,因此屬于戰爭年代;《一秒鐘》的故事背景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屬于和平年代。但對張九聲與劉閨女來說,在二人合力擊打“保衛科”以及后來被“保衛科”背對捆綁之時,這兩個時間點無疑分別對應時代錯位的開始與終結。身份、年齡、時代的三重錯位因而回應了元電影的閉環建制。
二、幻象毒性與同質化——壁壘的消融
相比數字時代之下的影像及其創作形式,《一秒鐘》敘事文本中對電影膠片的留戀毋庸置疑地指向一種關注物質及其技術痕跡的“迷影文化”。影片主人公張九聲將其對女兒的留戀移情于膠片上,膠片成為敘事的主線索,同時也成為人物內心情感的主要承載物。
“當某一客體的時間流與以該客體為對象的意識流相互重合(例如音樂旋律),那么該客體即為‘時間客體’。”影片中,《英雄兒女》的放映成為無數意識——即觀影群眾意識與集體無意識的這一時間客體的新結構與新形式,這也即是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下稱斯氏)所稱之為“超工業化”的文化現實。共時性與歷時性是一對不斷磨合的組合,而時間客體的“超工業化”制造的恰恰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普遍對立,制造出意識上的去個體化。
意識上的霸權和代具化過程會使得“我”被完全納入“我們”的范疇,進而使得個性化過程發生障礙,因為意識即是個性化過程。“在胡塞爾現象學劃分的第一、第二記憶基礎上,他特別提出還存在具有跨個體化功能的第三記憶(或第三持留),這是人類獨有的能將意識外化的助記憶術,即人工的、技術的器官組織。”跨個體化是法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西蒙棟所提出的術語,意即個性的荒漠,于弗洛伊德理論中便是“超我”的存在。而對于第一、第二、第三持留,簡單來說,以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3》中舉的經典時間客體“音樂旋律”為例,第一記憶是音樂的旋律或前一位音符,第二記憶是對音樂旋律的回憶,即記憶的再回憶與回憶的再記憶,第三記憶(或第三持留)則是技術的痕跡、物質性的保留,即唱片。因此,張九聲對膠片的執著追求亦可納入對第三持留的探討范圍。
斯氏電影理論指出,作為第三持留的電影制品便是技術痕跡的最佳證明和觀者意識的最佳載體,即“意識猶如電影”。第三持留雖然不可與第一、第二持留的性質完全等同,但是具有人類藥理學意義,即“亦毒亦藥”性。
“第三持留技術在意識外部從歷時、共時層面對意識內面全面工業化之可能,將造成大眾意識控制的全面升級而出現斯蒂格勒所言的‘存在之痛’,而斯氏第三持留理論的非批判性同樣挾帶著幻象毒性。”“亦毒亦藥”性中的“毒性”首先表現在觀眾沉浸于銀幕及其角色演繹時行動能力的暫時退化。于蒙太奇作用之下,作為“時間客體”的影像會與觀眾的意識流發生交疊,當下的過去化與過去的當下化使得影像擁有高度相似的結構,影像更接近于德勒茲在《電影II:時間—影像》中所描述的“晶體—影像”,進而此類含混性最終會導致現實與影像的混同。
“幻象毒性”主要體現在影片中的兩個敘事鏈條。第一,在《英雄兒女》將要放映時,群眾的反應是“看過很多遍了”,可知觀眾對《英雄兒女》的觀感是“先將來時”的,因此范電影先前對張九聲的態度也是“先將來時”的。在張九聲談到自己女兒的影像在電影中時被范電影反問其女若為革命英雄的女兒王芳,張九聲豈不是革命英雄王成等攻擊性話語,體現出對元電影特性的認同,即含混。因此,第三持留的“先將來時”特質可以被視作是意識制品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
第二,元電影的建構過程也裹挾著動員群眾拯救膠片的原初動力。膠片的“拯救行動”對于范電影、張九聲及余下群眾有著當今時代無可比擬的正向凝結力。“拯救活動”的展開會被群眾的內意識流動視為個體自身的構成、映射甚至成就。在“英雄兒女”四字出現在銀幕方塊之上時,群眾掌聲雷動,似乎對膠片的沖洗、梳理才迎來了《英雄兒女》中革命的開端與勝利,因此,第一、第二持留不斷交互,它們互相滲透。此時,作為時間客體之流的元電影,其“先將來時”的大團圓結局喜悅也由高度同質化的群眾所共享,而張九聲上衣口袋中有著女兒影像的膠片流失于黃沙中,意即指向斯氏所稱的意識的“沙漠化”與“無區別化”。
“斯蒂格勒認為電影代表著可被存儲、篩選、編輯和刪節的‘第三記憶’,電影的工業化讓‘第三記憶’不斷調節人自身具有的‘第一記憶’和‘第二記憶’能力,讓意識不斷物質化,這些物質化的意識成為程序工業的原料,以滿足當代世界正在生成的巨大的全球意識市場。”正因如此,意識的高度同時化以及與現實性的混同使得第三持留的毒性漸次顯現。
三、“解救機制”展示與“理式世界”背反與回歸
集體意識一直以來都是社會所詢喚的主要目標與方向,元電影特性的建構使得群眾意識與社會進行跨個體化連接,即在斯蒂格勒所稱的“刻板印象類型”與社會進行意識凝結;同時,由于張九聲這一特殊個體在影片中的存在,故社會記憶不僅在“刻板印象”中完成對群體的去個體化,也于“創傷類型”之下,完成個體記憶的抒發與解救。
(一)“刻板”的揭示與“創傷”的療愈
元電影能使觀影者清醒意識到自身的觀影行為,或是暴露電影機器,或是映射電影機制,在電影中講述電影。首先,《一秒鐘》中的時代背景極為特殊,群眾意識在經歷了“刻板印象類型”后,意識發生“沙漠化”和“同質化”的變更,時代的去個體化使得作為第三持留的意識制品——電影更具幻象毒性。
其次,除“刻板印象類型”之外,斯氏還提出“創傷類型”以作為“刻板印象”的類比項。“創傷類型”以激發、解放個體記憶的方式使得個體萌發意識同質化與荒漠化之下的希望;同時,“創傷類型”常常“偽裝”成“刻板印象”,以維持主體與社會的跨個體連接的穩定性。張九聲作為被誣陷的“壞分子”,其意識自然與時代下的集體格格不入(群眾觀影時張九聲遮擋銀幕被辱罵)。而影片中群眾意識的去個體化描述也即促成了張九聲“創傷類型”的凸顯:影片中女兒的一秒鐘影像為女兒生前的最后一刻。當張九聲獨自坐在范電影為其準備的“影像大循環”之下時,無數次女兒的活動影像便進行了無數次的“創傷類型”激發,其記憶類型不斷混同,第三持留與第一持留無限次顛倒,直到“保衛科”介入,其“解救機制”強制中斷,得以回歸影片的內在現實。
最后,影片內的“解救機制”未能于張九聲女兒影像自身中生成,但其“解救”卻是從對第三持留的探討中深入胡塞爾現象學難題中完成的。作為現象學創始人的胡塞爾在現象學發展前后過程中設立了一系列對應關系的現象學概念(A與A’),在現象學的“意向性原則”之下,A的意義由A’賦予,因此,A永遠無法等同于A’,故否定性與差異性得以凸顯,變成現象學的自身難題。第三持留制品完成的是對群體或個體意識的超強共時化,故差異性與缺陷性的出現與關注便是現象學視域之下的突破關鍵,亦是對作為“亦毒亦藥”的第三持留制品中被持留者解救方案的自省式生成。
因而從一種現象學本體難題的維度思考,張九聲的主體殘缺性(“壞分子”身份)進入本體殘缺性(父親身份)之時,于范電影釋放的女兒影像的“大循環”之下,此類奇特的“影中影”觀影方式使得電影內外關系發生顛倒和轉變,完成了一種齊澤克式的凝視。后來張九聲“回到”二號場找到劉閨女,實現了“意識猶如電影”:意識的不可同一性與作為幻象毒性的電影猶如光與暗的一體兩面性,因而自身的支點破碎,自身成為他者,張九聲轉換為劉閨女的“父親”甚至情愫對象,“創傷類型”不再借以“刻板印象”掩蓋自身,“解救機制”得以顯現出其真實力量。
(二)物質留戀與反物質追思——一種影像的“回環”
“電影是真實的,而故事卻是個謊言。”讓·愛浦斯坦此番對電影的概述描繪出電影的矛盾寓言,同時也概述出元電影建構過程中的對電影物質性探討的圖景。
柏拉圖對“理式世界”的推崇使得其對現實世界進行了一次唯心主義式的顛覆:人們頭腦中的世界為第一層,肉眼所見的現實世界為第二層,而藝術創造的世界則是第三層。柏拉圖的思想將藝術形式框定為世界的第三性之中,其認識論中的矛盾屬性卻與《一秒鐘》中元電影的建構形成對照:張九聲將位于第三性世界中的女兒的膠片認定為女兒自身的替代品,即“代具性”,其對影像物質的留戀無疑指向一種與柏拉圖思想背反的態度。因此,《英雄兒女》的敘事情節無法與具有“創傷類型”的張九聲產生共情(“范電影”將張九聲命名為“壞分子”),但《新聞簡報》中有著女兒身影的影像參與元電影的建構過程卻透射出“真實”與“謊言”(女兒影像與《英雄兒女》影像)、“物質”與“幻象”(女兒自身及其影像)的多重含混。
影片的結尾,張九聲對有著女兒影像的膠卷的執著,實際上,這既是對柏拉圖的一次質詢,但同樣也是對“理式世界”的一次回歸。因而在元電影的閉環建制之下,亦完成了一種對影像思考的回環建制。
《一秒鐘》是片中張九聲對女兒的一次“挽留”,而這樣的“挽留”卻是通過元電影的成功“搭建”及其對文化社會的一次批判實現的。“毒性”與“療愈性”夾雜于影像之中,物質物質與“理式世界”的多重對照是對元電影的一次特殊生成,同時亦成就了對電影本身的“最后一封情書”。“元電影讓‘電影與現實的關系’這亙古不變的追問懸置起來,與現實的發酵并不是電影的終極目的,思考‘電影還能怎么樣’或許比追問‘電影是什么’更能貼近元電影的精神內核。”張藝謀的《一秒鐘》,既是張九聲人生的漫長而循環的“一秒鐘”,也是獻給整個電影史的“跨越”時代邊際的“一秒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