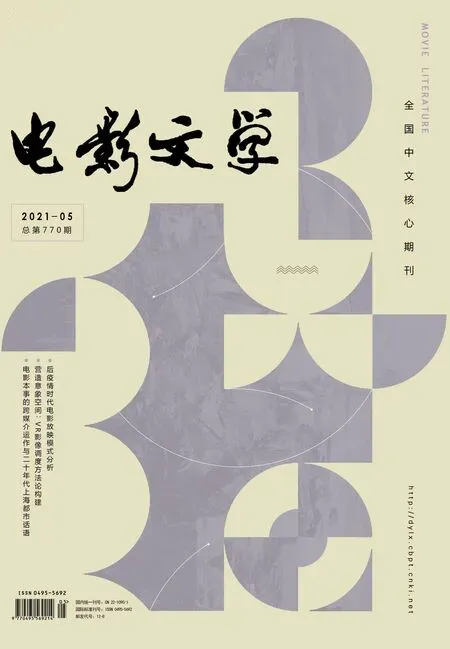20世紀30—40年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價值觀探尋
張 捷 薛晉文(太原師范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社會仍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在文化戰線上,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逐漸成為時代的主潮。在啟蒙與救亡的旋律交織中,影視藝術充分發揮其廣泛的傳播特性,承擔起文化救國的歷史重任。具體來看,中國共產黨對民族電影事業的領導是從1932年的左翼電影運動開始的;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后,電影界人士結成統一戰線,共同為保家衛國奔走呼號;抗戰勝利之后,回顧過往,展望未來,逐步奠定了民族電影事業的根基。
一、左翼電影文化:直面現實揭露民族苦難
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進一步加劇,電影市場上曾經異常火爆的武俠神怪片再也不能吸引觀眾的目光,整個社會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空前高漲,歷史的潮流推動著中國電影事業走向了革命的進步道路。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邀請左翼作家夏衍、鄭伯奇、阿英等加入明星編劇顧問行列,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向民族電影創作陣地進軍的開始。1933年3月,在黨的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下,黨的電影小組正式成立,由夏衍、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五人組成,夏衍任組長。自此,左翼電影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電影文化與國家命運緊密勾連,為20世紀初期的電影文化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左翼電影的進步性主要表現在取材上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它們重視劇本的基礎性作用,在影片創作初期十分注重作品的革命性,具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產階級的特征。1933年,由夏衍編劇,程步高導演,明星公司出品的《狂流》可以視作左翼電影的開山之作。影片以1931年長江流域水災為主要背景,深情講述了教師劉鐵生領導村民奮力搶險,勇斗地主富紳的動人故事,其中穿插著不少珍貴的水災真實影像資料,極大地增強了影片的紀實性和藝術張力,表現出強烈的時代性,借助影視文化的力量為階級斗爭吶喊助威。《春蠶》則改編自著名文學家茅盾的同名小說,同樣由夏衍編劇,程步高導演,是我國銀幕上第一部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電影。影片聚焦帝國主義入侵后,以江浙蠶農為代表的中國底層農民深受多重壓迫,艱難求生的悲劇性故事。影片著力塑造了蠶農老通寶這一典型形象,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同時卻又愚昧無知和軟弱無能,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殘余勢力的多重壓榨之下,風景如畫的江南水鄉也無法治愈主人公內心的痛苦與不堪。在這部作品中,影視藝術將這一時代積貧積弱的文化國情進行了生動記錄,批判了落后文化的破壞性和影響力。除此之外,還有《三個摩登女性》《上海二十四小時》《女性的吶喊》《小玩意》等,都立足于當下中國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多角度展現了國人在奴役和壓迫中奮起反抗的可貴品質。可見,早期電影藝術自覺擔負起了文化強國的重任,這些影片著眼于先進文化對社會文化建設的引領性和建設性,借助典型人物實現了對國民大眾時代文化觀念的改良和再造。
1933年是左翼電影全面爆發的一年,大批進步文人的加入極大充實了左翼電影的創作隊伍,為中國銀幕帶來了濃郁的革命氣息,中國電影真正承擔起了推動新民主主義文化快速發展的歷史重任,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產階級革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是電影推動這一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體現。與此同時,左翼電影迅猛的發展勢頭很快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密切關注,1933年11月12日,國民黨特務組織沖擊搗毀了左翼電影的主要創作陣地之一“藝華影業公司”,企圖恫嚇進步電影工作者,史稱“藝華事件”,這充分表明動蕩年代的電影文化強國之路歷經曲折與坎坷。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為時代發聲、為人民立傳的左翼電影并沒有因為反動勢力的迫害而偃旗息鼓,反而愈加顯示出堅韌的生命力。歷史地看,“作為20世紀30年代新的主流電影形態之一,左翼電影既是歷史客觀存在的市場化產物,也是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生態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左翼電影的發展壯大,對處于民族存亡關口的中國來說,意義非凡。它不僅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平臺,同時在銀幕上開辟了救亡圖存的有力陣地,呼應著啟蒙與救亡的時代主潮,成為文化救國的生動體現。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率先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響應黨的號召,1936年初,蔡楚生、歐陽予倩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電影界救國會,標志著中國電影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為了適應新的運動形勢,“國防文學”的口號應運而生,即旨在發起“一個最大限度地動員文藝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運動”,從文學界出發,迅速形成了一次“國防文藝”運動的高潮,左翼電影由此走向“國防電影”的創作道路,從此電影文化與救亡時代的文化強國使命同呼吸共命運,電影文化的階級性、斗爭性和時代性特征日益凸顯,電影以斗爭武器的形式直接投入文化強國的時代洪流之中。1936年11月,由沈浮、費穆編劇,費穆導演,聯華公司出品的《狼山喋血記》是國防電影的開山之作。影片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暗喻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現狀,野狼肆虐的村莊猶如被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中國,團結打狼的獵戶則代表一致抗日的中國人民。費穆詩意的藝術電影表現手法賦予影片一種回味無窮的魅力,它巧妙規避了此類電影極易出現的口號式、說教式弊端,得到了評論界的熱烈反響。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不朽的經典之作《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相繼問世,代表了20世紀30年代國產電影的最高成就。這兩部影片雖然沒有正面展現中國人民的抗戰歷程,但都通過對底層民眾命運的細膩刻畫,折射出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樸素又堅定的斗爭意志。由沈西苓自編自導的《十字街頭》塑造了四位性格迥異的青年人形象,剛剛大學畢業的他們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種迷茫與困惑猶如處于時代旋渦中的中華民族,在短暫的失意過后,影片結尾四人挽手同行,目光堅定地走向前方,向人民傳達出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唯有反抗才能救中國的有力呼喊。影片傳達出自力更生和自強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光影形式實現了傳統文化為時代文化服務的崇高使命。而由袁牧之編導的《馬路天使》則將目光聚焦在幾位底層青年身上,歌女小紅、吹號手少平、報販老王、妓女小云、剃頭匠、茶樓伙計等,他們備受欺凌,在夾縫中求生,卻沒有自怨自艾,始終對他人善良以待,對美好的事物充滿信心,能夠帶給觀眾一種正面的感召力。影片采用一種舉重若輕的方式針砭時弊并響應時代,以藝術的形式為救亡圖存的時代文化注入了無窮力量。這些載入史冊的經典作品,盡量規避了宏大的敘事視角和嚴肅的政治說教,以小博大,將鏡頭聚焦于最廣大的底層民眾身上,運用國人喜聞樂見的民族傳奇影像觸發群體情感共鳴,有利于廣泛動員社會各個階層共同投身于文化救亡的時代洪流之中。
二、抗戰電影文化:以光影力量實現文化救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火宣告了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巨大危機。面對這一嚴峻形勢,電影界的愛國人士迅速予以反應。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之下,一個具有廣泛統一戰線性質的電影界全國性組織——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于1938年1月29日宣告成立。協會秉持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的政策精神,宣言“要建立一個新的電影的戰場……以集體的行動來服務抗戰宣傳。對準著敵人的無恥說教,我們愿以電影的話語向我們的同胞和我們的國際間的友人陳訴新中國的現實”!此時的電影人在文化強國建設方面不僅具有國內全局意識,試圖建立電影文化的聯盟和陣線,重視加強電影文化的斗爭作用,積極發揮電影文化的協同抗戰力量,而且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將電影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傳播的載體,努力將抗戰形勢和抗戰主張及時傳播出去,盡心竭力地為抗戰勝利爭取有力的國際輿論支持。
全面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創作,主要集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后方。在統一戰線的指引下,電影界的國共合作結出碩果,這主要體現在中國電影制片廠(簡稱“中制”)所拍攝的一系列抗日題材影片中,如《保衛我們的土地》《八百壯士》等。其中,《保衛我們的土地》是全面抗戰爆發后,第一部正面描寫抗日戰爭的電影,由史東山編導,主要講述了農民青年劉山在被日寇摧毀家園后帶領親人逃難,一步步走上革命斗爭之路的故事。影片通過劉山的視角展現出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發動人民參與抵抗運動的重要性,表達出強烈的民族覺醒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影片中穿插剪輯進部分紀錄片場景,真實呈現了日本侵略者在我們的土地上燒殺搶掠的累累罪行,極大增強了電影的真實性,對于號召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非常好的宣傳效果。除此之外,中制還拍攝了數量可觀的紀錄片和新聞片等作品,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戰爭的縱深推進,此時的影視藝術在抗日斗爭中發揮了鼓手和旗手的良好作用。與中制采取公開的國共合作不同,“中央電影攝影場”(簡稱“中電”)隸屬于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被國民黨一手包辦,但在中共地下組織對抗戰電影工作的正確領導和進步電影工作者的團結努力下,中電的抗戰電影創作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先后拍攝出《中華兒女》《長空萬里》等優秀之作。而由軍閥閻錫山投資開辦的西北影業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響應時代號召,創作完成了長紀錄片《華北是我們的》,講述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情況,以及表現西北人民英勇抗戰的故事片《風雪太行山》。應該指出的是,在全面抗戰時期,國統區的電影創作在廣泛的統一戰線影響下,表現出了一定的進步性,為喚起人民的抗戰意志和弘揚愛國主義文化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電影文化為特殊歷史時期的文化強國建設不遺余力。但是,國統區的電影創作同時又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國民黨反共浪潮的干擾和破壞,可以說是在夾縫中求生存,這也使得這一時期電影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有所折損。總體而言,內憂外患之中,電影藝術服務于文化強國的征途絕不是一帆風順的,但在民族矛盾占據絕對主導的危急時刻,不同黨派和階層都深刻地認識到電影之于文化救國的意義和價值,從而奮力突破了政治立場的藩籬,使得電影藝術在文化戰場上的統戰力量得以凸顯。
此外,全面抗戰時期,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逐步建立起了中共自己的電影事業基地,為電影文化強國設立了自己的根據地。“1938年秋天,在八路軍總政治部領導下成立了延安電影團,主要成員有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馬似友等人。‘延安電影團’是中共成立的第一個電影機構,是黨性宣傳與電影的結合,從此之后真正意義上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電影得以誕生。”在艱難的現實境遇下,延安電影團始終圍繞著紀實性、革命性和歷史性的創作原則對拍攝題材進行進一步的創新性嘗試和探索,完成了許多優秀的紀錄電影佳作,如《延安與八路軍》《南泥灣》等,留下了非常寶貴的歷史影像資料,藝術家們不斷探索電影和國家命運的內在聯系,電影文化與民族存亡休戚與共,電影藝術與文化救國密不可分。可以說,這一時代的電影文化強國主要表現在電影文化救國方面,依托電影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為民族解放而不懈努力。抗戰時期的延安電影團,適時地用膠片記錄戰爭生活,理性克制地說明真相,力圖將一個真實的延安和八路軍介紹給外界和人民大眾,開創了反映新意識形態與宣傳策略的政治電影的先河,電影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標簽獲得了空前強化。1942年5月,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了有文藝工作者、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計100多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同時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明確指出,文藝創作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人民大眾服務,“我們的要求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中國電影文化更加鮮明地體現出其階級斗爭的屬性,它成為黨領導下的政治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電影文化配合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的效果愈加突出。歷史地看去,電影對于文化救國發揮了巨大作用,是宣傳陣營中的一名重要成員,成為我們用“筆桿子”瓦解敵人和啟蒙大眾的一員健將,它將光影的力量轉化為動員人民和打敗敵人的有力武器。自此之后,影視藝術服務于文化強國從一種個體自發狀態轉向了群體自覺狀態,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之上開啟了全新的征程。
三、解放區電影文化:多方合力奠定文化強國根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于取得最終勝利,舉國上下一片歡騰。然而,人民期盼中的美好景象卻并沒有出現,國民黨當局不斷妄圖破壞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復雜的國內形勢推動有良知的社會實業家投身電影事業,也為進步電影人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戰后最有影響力的昆侖影業公司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昆侖公司深受“左”傾思想影響,是由幾位思想開明的實業家出資籌建的,主要包括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等人,他們為戰后進步電影的拍攝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支持。可以說,昆侖公司雖然地理位置不在解放區,但是和解放區電影有著共同的文化追求。1947年5月,昆侖影業公司與聯華影藝社合并,沿用“昆侖”這一名稱,相繼拍攝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烏鴉與麻雀》等影史杰作。這些作品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關注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在抗戰前后的命運變遷,同時表現出濃郁的民族審美范式,對后來國產電影的創作影響極其深遠。《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于1947年2月,由史東山編導,影片著力塑造了進步女學生江玲玉一角,她參加救亡演劇隊一路北上,攝影機跟隨她的視角歷盡艱辛,充分表現了抗戰的艱難與人民生活的困苦。然而當戰爭結束她返回上海后,卻連安身之所都沒有,反觀她的表兄周家榮靠給國民黨接收大發橫財,寄人籬下的玲玉內心無比悲愴痛苦,在不同人物命運的對比中,影片的現實批判性、階級斗爭性都鮮明地體現了出來。《一江春水向東流》由蔡楚生、鄭君里聯合編導,分為《八年離亂》《天亮前后》上下兩集,共計210分鐘。全片時間跨度長、空間范圍廣、人物角色多,被譽為中國悲劇性史詩電影的代表作。影片主要敘述了男主人公張忠良如何從一個滿懷斗爭激情的進步青年一步步被資產階級腐蝕,走向墮落淪喪的過程。張忠良也曾大聲疾呼抗日救亡的道理,不惜作別年邁的父母、新婚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投身到革命運動當中去,但抗戰的艱辛與前路的迷茫逐漸消磨了他的意志,因此在偶遇了舊相識王麗珍后,張忠良搖身一變混跡到了官僚資產階級的隊伍中去,而且越來越甘之如飴。與之相對,他的妻子素芬則代表了更多在戰爭中忍辱負重的中國底層人民,備受侵略者奴役與欺凌的素芬從來不曾屈服,但面對丈夫的背叛她崩潰了。影片結尾,素芬投身滔滔江水之中,結束了自己艱辛的一生。《一江春水向東流》具有沉甸甸的歷史厚重感,通過張忠良與素芬不同命運的對比勾勒出抗戰前后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生百態,具有深刻的現實批判意義和強烈的歷史反思精神。這一時期的杰出電影共同的特點是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服務,用電影文化特有的“文權”,努力肢解國民黨政府視為命根子的“政權”“財權”和“軍權”,從側面再次證明了,優質的電影文化資源既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生產力,更是一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戰斗力,這是影視藝術與文化強國戰略關系的最為生動具體的體現。
“昆侖影業公司”作為戰后私營電影創作力量的杰出代表,始終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堅持思想性和藝術性并重,將電影文化作為階級斗爭的有力武器,為民族解放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電影藝術服務文化救國的步伐更加堅定和自覺。與此同時,中共的電影事業也在穩步向前推進,1946年10月,東北電影制片廠在黑龍江興山成立,它的前身是東北電影公司。日本在侵占東北三省期間在長春成立了“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簡稱“滿映”),抗戰勝利之后,中共地下工作者做了大量宣傳和聯絡工作,逐漸掌握了滿映的實際控制權,并改組成立東北電影公司。但由于解放戰爭形勢緊迫,國民黨意圖奪取東北電影公司的主導權,中共指示東北電影公司盡快撤離長春,抵達黑龍江興山。“1947年10月,在延安電影制片廠的基礎上改組成為西北電影工學隊,同時抽調陜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戰斗劇社、七月劇社、西北文工團、綏德文工團等人員,由鐘敬之任隊長,成蔭任支部書記,帶隊出發去東北。1948年6月到達興山,加入了‘東影’,在新的實踐中成為解放區電影發展中歷史的一環。”就這樣,多方進步力量匯聚東北,東北電影制片廠成為日后新中國第一個電影制片基地。由此,自我建設的不斷加強、人才隊伍的逐步充實、創作陣地的日漸鞏固,使得電影藝術在助力文化強國的道路上擁有了更強大的領導力和更具分量的話語權。黨領導“東影”在建立之初便確定了以新聞紀錄片為主導的創作原則,其出品的系列紀錄片《民主東北》意義重大,影片內容不僅涉及戰爭歲月的真實反映,還全方位展現了東北解放區群眾的日常學習、生活風貌,整體風格質樸動人。1949年4月,“東影”遷回長春,同時推出長故事片《橋》,這部電影被譽為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在中國電影史上,《橋》是標志著電影藝術由文化救國使命到文化興國使命的里程碑,電影文化建設從救亡圖存轉入了文化興國的新的歷史階段。影片以工人階級為主要表現對象,講述了東北一家鐵路工廠的工人們努力克服一系列困難,完成搶修松花江大橋的任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突出貢獻。影片時代特色鮮明,一經公映便得到廣泛好評。除此之外,東北電影制片廠還積極投入動畫電影創作領域,為新中國的動畫電影事業打下良好基礎。1949年初,國內政治形勢漸趨明朗,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權還在做最后的掙扎,而現代中國歷史即將沖破這黎明前最后的黑暗迎來重生。中共逐步接管了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制、中電等電影制片基地,奠定了共和國電影的基礎。1949年4月,中央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袁牧之任局長,統籌并領導建立中共新政權之后的中國電影事業,就這樣,中華民族電影事業開啟了新的篇章。
結 語
由此可見,20世紀三四十年代,黨領導下的革命電影運動在艱難的環境中頑強求生,在民族電影資本市場中一步步發展壯大,它強力配合著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偉大事業,表現出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特征,將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一次次沖破。左翼電影和國防電影高潮一改中國電影的落后面貌,為銀幕帶來了現實主義的氣息。抗戰電影在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引下,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對于喚醒民眾、宣傳抗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抗戰勝利以后,進步的民營電影企業致力于在銀幕上再現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命運變遷,以此折射出整個時代的風云變幻,具有明確的現實批判意義和階級斗爭屬性;而解放區則一步步建立起屬于人民的電影文化事業,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奠定根基。總的來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中共領導下的電影事業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的藝術屬性、傳播屬性、意識形態的政治屬性均得到了全面發展,在積極宣傳先進文化、充分喚醒民眾思想,動員基層救亡圖存中發揮突出作用,同時亦成為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為文化救國偉業做出了自己應有的歷史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