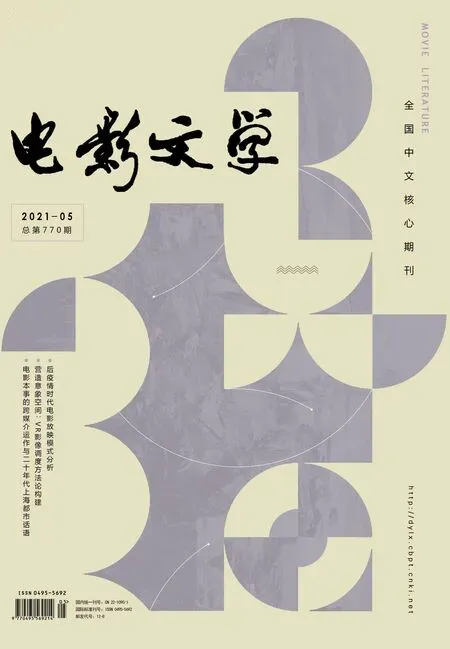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閾下《花木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王 帥/Wang Shuai
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最早的文學版本出現于宋代郭茂倩主編的《樂府詩集》中的《木蘭辭》。經過1000余年的發展演變和多種藝術形式的改編補充,“木蘭形象不斷地改變與刷新,關系人物不斷地增加,故事情節不斷地豐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故事譜系,最終成為國家與民族的集體記憶和傳統文化的精華”。“木蘭故事”流傳深遠,其中所蘊含的忠孝之道、英雄主義、家國情懷以及女性認同等敘事母題和文化想象,為其影視化改編提供了豐富多義的類型元素和拓展議題。
2020年,由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妮基·卡羅執導的真人版劇情電影《花木蘭》登陸國內外院線,作為東方經典傳說與現代電影工業相結合的產物,一經上映便備受關注。然而,放映后很多觀眾對其無新意的翻拍套路、不合時宜的人物裝扮、拖沓晦澀的臺詞設置表示失望。《花木蘭》的口碑雖褒貶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該片在以影像符碼呈現兩位女性(花木蘭與女巫)的主體意識覺醒和身份認同達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探索意義。因此,本文以花木蘭和女巫這兩位女性形象的塑造為立足點,窺探女性主義視域下該片如何實現對父權制度的祛魅,厘清并洞悉其中潛藏的性別詰問和權力關系,建構女性身份認同和性別認同,從而完成對女性主體意識的策略性表達。
一、社會規訓與性別迷失的桎梏
《花木蘭》雖然是以花木蘭(女性)作為“主體”展開敘事的,但運用的第一人稱敘事者卻是木蘭的父親——花周(男性)的口吻,這種復合式敘事,暗示著女性的行動時刻被男性的敘述層層裹挾,被牢牢控制在父權制度的社會規訓議程中。福柯指出:“我們應該承認,權力制造知識(而且,不僅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權力才鼓勵知識,也不僅是因為知識有用,權力才使用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可見,知識和權力的共謀使得傳統社會中的父權制度異常牢固,二元對立的性別表述實施著對女性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規訓,將女性禁錮在性別迷失的“鐵屋子”。
花木蘭從小能文善武,開場“攀上屋頂捉雞”的一出戲便展現出她靈動機敏的身姿和超乎尋常的膽識,也體現出木蘭對父權制度下女性自身角色規范的僭越。她所呈現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不同于以往父權認知中的“賢妻良母型”女性氣質,因此遭到鄉親父老的鄙夷和嘲諷。如米利特所言:“父權制的意識形態夸大了男女之間生物學上的差異,它明確規定了男人永遠擔任統治的或男性氣質的角色,而女人永遠擔任從屬的或女性氣質的角色……如果女人拒絕接受父權制的意識形態,如果她打算拋棄她的女性氣質,即她的恭順/屈從性質,如果她要以此表達對父權制意識形態的懷疑,那么男人將對她采用威脅手段,彌補平時管教不力。”父親勸誡她收斂體內的“氣”(能力),因為這種能力只有戰士需要,認為木蘭應該學習“三從四德”,以此成為一位合格的妻子和母親。出于孝心,木蘭答應了父親的安排,畫上妝容、穿戴整齊去相親。在這里,相親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檢驗女性角色規范的考試,意味著桀驁的女性(木蘭)“在男性的規訓下,或主動或被動地被馴化,由此可見女性身體性別意義上的文化寄寓與父權印記”。媒婆向她灌輸著“文靜、沉著、優雅、賢淑“等一系列禮儀規則,但木蘭卻處處出丑,未能通過考試,印證了木蘭不符合父權制度下傳統女性的刻板印象,也體現出她無力打破“鐵屋子”桎梏的無望感。
在故事肇始的畫外音中,“女孩運‘氣’會蒙羞、受辱甚至被流放”一語便指明了女性的宿命。這種迷思式的宿命如同幽靈一般籠罩著木蘭和女巫的一生,也映射出父權社會對女性能力的貶低和命運的操縱。柔然部落的軍師女巫,是首領步利可汗的得力助手,為其訓練了一支由暗影戰士組成的精銳部隊,輔佐步利可汗不斷攻陷中軍的要塞,屢建軍功卻得不到其認可與肯定。女巫在片中多次幻化為商人、士兵、宰相,這些人物均為男性身份,似乎只有隱藏自身的“女性氣質”,以異質身體才能獲得進入父權社會的“通行證”,可見其性別迷失和身份焦慮。女巫不允許步利可汗叫她“巫婆”,讓其稱自己為“戰士”,盡力輔佐步利可汗是為了能夠得到“認可能力、接納身份”的安家之所。步利可汗卻說:“你如喪家之犬一樣流放在荒山野嶺,只有依靠我,你才能安家。”荒山野嶺是一個含混且模糊的所指,暗示著女巫自身處境的惡劣與艱險,也反映出女性地位的邊緣化和弱勢性。女巫只能無奈地向他臣服:“我明白了,我聽命于你,我是奴隸。”這一舉動恰恰寓意著女性向父權社會的屈從和投降。
個人的身份是被社會建構的需要和欲望所決定的。無論是木蘭,還是女巫,在影片初始都缺乏完整性的自我概念,淪為斷裂、破碎的“失語”木偶。木蘭遮掩“男性氣質”,選擇“自我閹割”,將自身改造為符合父權制度價值標準和期待視野的女性形象;女巫則是隱藏“女性氣質”,如同刀槍不入的“鋼鐵戰士”一樣沖鋒陷陣,以“自我雄化”的方式獲得和男性相對等的談判資格。實質上,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區別是生物性的/自然的,而不應該是文化的/人為的,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男尊女卑、男優女劣的等級排序。然而,在社會規訓和性別議程的設置下,木蘭與女巫都進入性別迷失的迷霧中,成為“菲勒斯中心主義”權力秩序中失去女性主體意識的“他者”。
二、主體重塑與女性意識的覺醒
對父權制度進行祛魅,正視女性的價值和獨立性,完成主體重塑和激發女性意識的覺醒,才能校正父權社會的性別盲點。帕森斯指出:“那些強調女性和男性能夠以共同方式行動的人繼承了二元論,這種二元論將女性的能力定位于物質、身體與情感,而將男性的能力定位于精神、心智與理性。提供這一二元化結構作為獨特人類能力實踐的背景,已經剝奪了女性充分實現自己的權力,同時它卻給予男性的定位以特權。女性是否要變成男性才能行動?”也就是說,完全忽視兩性之間的差異,兩性也不可能共同持有行為主體權力,女性主體的重塑不能依靠模仿、偽裝甚至是同化為男性來完成。這種女性的“花木蘭”困境探討,具有現代性意義,強調著尊重女性性別意識和“差異性”表達的重要性。
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出征,殺伐北虜,既體現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孝道和忠誠),又表現出木蘭“巾幗不讓須眉”的女性英雄氣概,這也是她尋求自我價值、進行主體重塑的冒險和時機。她以男性的“身體”進入軍營,混跡其中,隱匿真我。軍營如同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視監獄”,具有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和檢查等規訓手段和規訓技術,形成了緊密的權力關系網絡。為了不讓別人察覺出自己的“女性”身份,木蘭每日早起、晚睡,以避開他人;說話時故意壓著嗓子,增添“男人氣”;不敢洗澡,以至于渾身發臭。每日與男兵一起練武、射箭、拎水桶登山頂,“身體”日漸成為被操縱、被塑造和被規訓的工具,木蘭的女性主體性被湮沒和消弭,無法以真實的身體示人。女巫雖能力超群,卻將自我建構為男性的“他者”,內化父權制度的等級和價值觀,認為自己低人一等(被拯救者),只能仰仗步利可汗(拯救者)來實現自我主體重塑,經常幻化為他人(男性),不以真實面目出現。木蘭與女巫或被動或主動地自我馴化,身體的“去性別化”折射出女性追求主體重塑和意識覺醒的復雜性和艱難性。
“對許多解放女性而言,首要之務是將身體的意義重新建構為權力和愉悅的來源。”正視自己的身體,才能緩解和治愈主體潛在的焦慮和不安。在與洪輝比武時,木蘭情急之下忘記了父親的勸誡,展現出實力,得到了上級董將軍的認可。董將軍盛贊其是一位優秀的戰士,而贊賞的前提架構在默認木蘭“男性身份”的基礎之上,一旦識破了她的女性身份,后果則是被流放以及家族受辱。戰前宣誓時,木蘭與眾將士大聲齊呼“忠、勇”,卻在念到“真”時猶豫不決,因為木蘭在被規訓的社會空間秩序(軍營)中,無法面對自我真實的女性身份,如她謊報的姓名“花軍”一樣,她的身體和身份已被建構為父權意識形態的耦合物。戰友們聚在一起討論“女性”時,大家的話題都聚焦于女性的“身體美感”和“溫順品質”,女性的形象成為男性欲望狂歡的能指。當問到木蘭時,她說:“我理想中的女子要勇敢、聰明,有幽默感。”表明木蘭對于女性主體重塑的期望和女性意識覺醒的預兆,也透露“在那些限制的范圍內,每個人依然可以在‘虛無’的意義下模塑自己的存在”。承認女性價值和女性氣質的“合法性”與“必要性”,才能重新界定性別權力話語的新界域,松動父權制度堅固的壁壘。
“家庭”與“軍營”實質上都是男性對女性進行規訓和支配的場所,充斥著父權制共生性權力話語的建構。受壓抑的女性只有尋找“間隙”,完成自我“發聲”,將這種權力話語進行拆解、倒置和重構,對男性邏各斯中心主義進行抵抗,才能闡釋自己。與柔然軍交戰時,木蘭只身一人追逐柔然兵時誤入山谷,遇到了女巫。女巫打敗了木蘭,并一語戳穿木蘭偽裝的“男性身份”,告訴她謊言會削弱她,只有面對真實的自己,才可以釋放出真正的能力。在這個單純由女性構成的場所(山谷)中,木蘭與女巫之間基于女性個體生命體驗的對話,直接堅定了木蘭主體重塑和女性意識覺醒的信念。木蘭扯掉發帶,丟掉盔甲,以英姿颯爽的“女性身份”重返戰場,用智勇雙全的聰明睿智扭轉了局勢,木蘭(女性/拯救者)還于危難中拯救了洪輝(男性/被拯救者),這種“倒置話語”顛覆了父權制度中“男性拯救女性”的主流話語,通過反轉完成了女性主體“抵抗”父權社會的策略性表達。
木蘭自始至終都展現出不亞于甚至超越男性的聰明和體能,“換回女裝”標志著她對女性精神力量和生命價值的追求與探索,解構、顛覆了父權話語中的權力結構,對“花木蘭困境”給出了“女性不是非要變成男性才能行動”的答案。作為木蘭“成長”的見證者,女巫依然禁錮在父權社會語言秩序中含糊其詞,作為“他者”被動地等待父權社會的認可。兩位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證實了女性脫離“生理即命運”可能性的存在,但也體現出徹底解放已被階層化兩性關系的復雜性和艱難性。
三、身份認同與自我命名的實現
“認同”一詞,譯自英語名詞“Identity”及其具有動態含義的衍生詞匯“Identification”。在當代的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領域,當“認同”作為名詞時,可用于表征“某個個體或群體據以確認自己在特定社會之地位的某些明確的、具有顯著特征的依據或尺度,如性別、階級、種族等”,含義相當于“身份”;當它作為動詞時,可用于表征某個個體或群體對自我在文化上某種身份的確認和歸屬,強調的是對某一身份的“認同過程”。簡單來說,認同問題就是你認為自己是什么樣的人以及你歸屬于哪個群體的問題。
“家國一體”是中國文化的特征,木蘭替父從軍殺伐北虜,體現出木蘭“家國一致、盡忠盡孝”的道德信念,即使在暴露女性身份、觸犯軍規、遭到驅逐后,她依然堅守身份認同,對女巫說:“我知道自己的位置,為國而戰。”當木蘭得知步利可汗的陰謀后,不顧生命危險沖進軍營請見董將軍,她的勇氣和忠誠贏得了所有將士(男性)的認可,如洪輝所言:“木蘭比任何一名男子都勇敢,她是我們之中最優秀的戰士。”可見,木蘭以女性身份消弭了父權社會性別權力建構的偏見。木蘭帶兵拯救了困于危難之中的皇帝,同時拯救了處于紛飛戰亂中的國家,從一個“逃避自我”的懵懂女孩成長為“面對自我”的英勇戰士,她尋找自我并展現了自我價值,完成了“中國女英雄”故事的敘述。
作為影片中富有意涵的意象,“鳳凰”曾四處出現,每次都象征著木蘭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幼年時木蘭踩壞了祠堂門口供奉的“鳳凰”石像,父親說鳳凰是祖先派來的使者,會浴火重生,保護有勇氣的人。第一次是木蘭替父從軍、日夜兼程騎馬奔赴軍營,在山谷中迷了路,“鳳凰”現身,如“領路者”一樣帶領她走出迷谷,這是對其“孝”的嘉獎。第二次出現的場景是木蘭拒絕了女巫“同流合污”的要求,冒死請見董將軍之時,“鳳凰”如同“守護者”追隨著她,這是對其“忠”的嘉獎。第三次是木蘭與步利可汗交戰,落于下風時,“鳳凰”如同“助力者”一樣,幫助她打敗了步利可汗,這是對其“勇”的嘉獎。第四次是木蘭淡泊名利,拒絕皇帝冊封,返家與親人團聚時,“鳳凰”如“見證者”一樣在天空久久盤旋,這是對其“真”的嘉獎。“鳳凰”的四次出現,分別對應著木蘭身上體現的“孝、忠、勇、真”優秀品質,也完成了木蘭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自我命名。
女巫與木蘭的相同之處,在于兩人都具有強大的能力,都曾困于社會規訓和性別迷失的桎梏中,都曾遭受父權社會的壓迫,并被其無情背棄。兩人的不同之處則在于:木蘭具有清晰的身份認同和自我命名的渴望,她將希望寄托于自身而非他人。而女巫懷有傷痛的記憶,如她所說:“我展現出的力量越大,遭受的壓迫也越重,我終生徙流,無國、無鄉、無家。”這些“記憶的歷史”是一種“對過去的證實”,她的身份認同注定是混亂與無果的,因為“認同是多重的,基于身份的核心是獨一無二的‘自我’或主體,認同就必然是開始于作為個體的自我或主體的,或者是自我對國家、種族或民族等集體的認同,或者是自我對于社會、他人等人際交往及人類關系的認同,或者是自我對于自身的反觀與省察等”。然而,對女巫而言,四海之大卻無處認可其能力、接納其身份,追隨效力步利可汗(侵略者)的行動也不具有“合法性”,最終只能走上與木蘭截然不同的無涯歧途。
對每個個體而言,在由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搭建的人生坐標中追求身份認同和自我命名,都是建構自我同一性的過程。女巫被木蘭展現出的強大信念和力量所折服,迷途知返,棄惡從善,決定幫助木蘭拯救皇帝,步利可汗輕蔑地稱木蘭是個“女孩”,女巫糾正其為“一個女人,戰士”!并用身體擋住了步利可汗射向木蘭的箭,臨死之前讓木蘭去取屬于她的位置,其實寓意著女巫認同了木蘭的選擇,將“為女性正名”的希望寄托于木蘭。而女巫的死,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善惡有報”的道德價值觀,也說明身份認同混亂的人實現自我命名的期許終將破滅。
木蘭從軍的故事,每一次再敘述都應體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社會心理、價值理念和文化特征。相較于動畫版《花木蘭》,真人版《花木蘭》刪減了木蘭與皇帝擁抱、木蘭與父親親吻等不符合中國觀眾審美習慣和期待視野的戲份,但依然存在無新意的翻拍模式、不合時宜的人物裝扮、拖沓晦澀的臺詞設置等不足之處。但值得肯定的是,創作者通過影像聚焦于木蘭和女巫這兩位女性形象的欲望書寫和身份建構,厘清并洞悉父權社會中潛藏的性別詰問和權力關系,探索著女性主體意識的策略性建構,積極尋求著女性自我命名的路徑,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