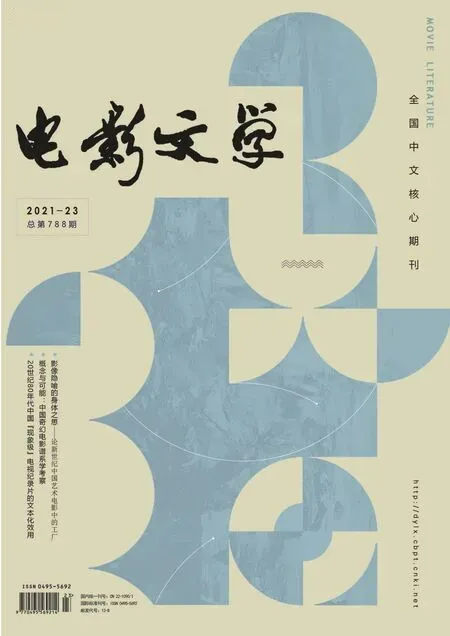國產(chǎn)紀(jì)錄片中“匠人”形象的塑造策略
李 諾
(長春人文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117)
近十年來,隨著群眾觀影水平的提高,觀眾對紀(jì)錄片審美趣味的變化,紀(jì)錄片也逐漸呈現(xiàn)出多種類、多面貌、多層次、多樣態(tài)的特點,特別是一些以呈現(xiàn)我國各行各業(yè)專業(yè)的真實狀態(tài),記錄人們現(xiàn)實生活為主題的紀(jì)錄片躍上屏幕,成為一時焦點,具體如《人間世》以醫(yī)院為拍攝場景,從醫(yī)護、病患、家屬多個向度,縱深地展現(xiàn)了當(dāng)下現(xiàn)實里個體小人物的命運;《人生第一次》旨在通過蹲守拍攝,觀察不同人群在人生重要節(jié)點的“第一次”,串聯(lián)起當(dāng)代中國人一生的圖景;《巡邏現(xiàn)場實錄》則是借由民警巡邏出警的日常,展現(xiàn)當(dāng)代社會中隨處發(fā)生的小摩擦和人與人之間不經(jīng)意間的溫情等。
在這些紀(jì)錄片中,“匠人”是得到較多刻畫的群體。影片中多次出現(xiàn)了普通產(chǎn)業(yè)工人、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人,詳細(xì)展示了他們生活、工作、學(xué)習(xí)的多種面貌,實際上是在旨在借由對這些人物的刻畫,重塑一種對特殊文化形象符號的認(rèn)知。工匠們或展示的不僅僅是工作的內(nèi)容,更多的是在此層面上的個體精神。如《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就展現(xiàn)故宮文物修補過程中,工匠們?nèi)硇耐度氲臓顟B(tài)以及工匠們對文物修復(fù)工作的熱忱,《大國工匠》則將焦點聚焦于為中國的國防科技、民生產(chǎn)業(yè)奮斗的工程師,以及他們在工作中無限探索的精神,并通過這些記錄,向觀眾揭示當(dāng)代中國國富民強的精神依托。在這些以“匠人”為題材的紀(jì)錄片里,始終體現(xiàn)了一種切合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積極價值觀,一種專注的、奉獻的、忘我的時代精神,匠人精神體現(xiàn)出的追求極致、奉獻自我、高度專注的品質(zhì),正是目前消費社會普遍缺乏的精神品質(zhì)。本研究嘗試梳理我國近些年紀(jì)錄片中“匠人”形象的發(fā)展脈絡(luò),以《我在故宮修文物》一片中所呈現(xiàn)的匠人精神與匠人特質(zhì)作為分析基底,并在比較視野下對比中日紀(jì)錄片中匠人精神的差異,試圖探討中國紀(jì)錄片在近年來孜孜不倦描繪“匠人”的意義。
一、匠人精神與期待視野:國產(chǎn)紀(jì)錄片中前匠人階段
近些年出現(xiàn)的中國紀(jì)錄片大體上保持著一種“小人物記錄大時代”的特點。從《舌尖上的中國》開始,“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的紀(jì)錄片敘事特點就已經(jīng)逐步形成,《舌尖上的中國》詳細(xì)描繪了中國飲食文化巍巍幾千年歷史,借由展示在各個地方形成的特色菜肴,見微知著地呈現(xiàn)了美食背后中國各個地區(qū)的風(fēng)俗特色、歷史文化。《舌尖上的中國》章丘鐵鍋一節(jié)中,導(dǎo)演將鏡頭對準(zhǔn)堅持用手工小錘敲擊制作鐵鍋的鐵匠,并且將鐵匠們對工藝傳承的堅守和對職業(yè)身份認(rèn)同的自豪感,作為本章的主旨,《舌尖上的中國》播出后引發(fā)了國內(nèi)消費者購買手工鐵鍋的熱潮,這種熱潮,實質(zhì)上是觀眾們對返璞歸真的匠人精神和“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生活態(tài)度的認(rèn)可。自此以后生活中的平凡人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xiàn)在國產(chǎn)紀(jì)錄片之中。
《舌尖上的中國》之后,國產(chǎn)紀(jì)錄片一改過去宏觀視點下的大格局、大時代、大變遷為拍攝主體的紀(jì)錄片傳統(tǒng),《河西走廊》《話說運河》《唐蕃古道》這一類以自然風(fēng)景、民族風(fēng)情、歷史傳說等題材的紀(jì)錄片明顯地減少了,轉(zhuǎn)而開始將鏡頭對準(zhǔn)普通市民的生活。美食紀(jì)錄片一時間出現(xiàn)了爆炸式發(fā)展,《尋味順德》《味道中山》《人生一串》《一城一味》等就是這一階段誕生的產(chǎn)物。這些紀(jì)錄片都著重于地方飲食文化的刻畫,其展現(xiàn)的方式與《舌尖上的中國》不乏雷同之處,引發(fā)的觀眾討論熱度也不能與《舌尖上的中國》相提并論,形成這樣的差異原因,還是這一類紀(jì)錄片同質(zhì)化過重、只留有對具體事物的記錄,缺乏對現(xiàn)象背后根源因素的探查,缺乏對美食背后人文精神的深層次挖掘。《尋味順德》嘗試將順德的知名小吃與當(dāng)?shù)叵鄬χ牡赇佔鼋Y(jié)合,但卻引發(fā)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形成這樣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影片缺少了對工藝、工匠的背后故事的探索和挖掘,展現(xiàn)的卻是消費社會邏輯下,營銷、網(wǎng)紅、品牌、資本對工藝傳承的傲慢。
《舌尖上的中國》不僅僅引發(fā)了觀眾對中國各地風(fēng)土口味的興趣,更大層面上,《舌尖上的中國》引發(fā)的是中國人對業(yè)已失去的工藝、工匠精神的追憶和探索。在《舌尖上的中國》后,以工匠精神著稱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橫空出世,實際上突破了過去紀(jì)錄片過分注重高知名度、有悠久歷史的大事件,轉(zhuǎn)而開始注重“物品—人—精神”的邏輯鏈條,并根據(jù)人物的特點,人物或器物所傳承的精神力量當(dāng)作重點刻畫的內(nèi)容。《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成功,也反映出中國紀(jì)錄片將“匠人”文化和精神推向社會所收到的關(guān)注和認(rèn)可。
二、時代精神的弘揚:對“匠人”身份視野的確認(rèn)與傳達
《我在故宮修文物》是一部圍繞著故宮文物修繕專家們工作生活展開拍攝的紀(jì)錄片。本片重點記錄故宮書畫、青銅器、宮廷鐘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寶鑲嵌、宮廷織繡等領(lǐng)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復(fù)過程和修復(fù)者的生活。《我在故宮修文物》在展現(xiàn)修復(fù)工藝時,往往是多線并行的,以故宮中館藏的稀世珍寶為經(jīng)緯,以修復(fù)作品中小組成員的配合和對工藝的解說為血肉,以對作品價值的肯定,對修復(fù)后作品效果的展示作為總結(jié),以修復(fù)師在修復(fù)工作中展現(xiàn)的專業(yè)技能、專業(yè)精神、對職業(yè)身份的認(rèn)可作為影片情感升華。四個方面的融合對影片的制作缺一不可。在紀(jì)錄片第一部分中,可以清晰看到形成敘事鏈條的三重故事套疊,第一重是以王津為修復(fù)專家的鐘表修復(fù)工作的進程;第二重則是修復(fù)唐三彩馬的進程;第三重則是以師傅帶徒弟的傳統(tǒng)視野,展現(xiàn)故宮修復(fù)工匠中年青一代狀態(tài)的內(nèi)容,從這三層套疊,基本上呈現(xiàn)了時間、空間、歷史三重的交匯,工匠們技藝的磨礪、對傳統(tǒng)修復(fù)工藝的集成以及對后來修復(fù)者的培養(yǎng)融匯在這三重結(jié)構(gòu)之中,形成了復(fù)雜的、多面的敘事效果。故宮寶物的修復(fù)技術(shù)超越古今,實現(xiàn)了一種微妙的、持續(xù)性的繼承,而故宮中的文物同樣如此,鐘表、字畫、陶器等等寶物以“物”的實際存在,微妙實現(xiàn)了歷史的“虛”的傳承。在故宮國寶的面前,一代一代的故宮修復(fù)工作者又成為與穿越歷史、亙古不變的“物”的參差對照。這種三重套疊的敘事模式,顯然是一種對流媒體與互聯(lián)網(wǎng)的媒介表現(xiàn)方式的改造和利用,而這種頗具古典美和形式美的敘事樣態(tài),又進一步與故宮珍寶修復(fù)的主題烘托,形成了“一唱三嘆”的格局。
《我在故宮修文物》真正的核心并不是故宮的稀世珍寶,而是修復(fù)者們的職業(yè)生涯與職業(yè)背后對修復(fù)工作高度精神認(rèn)同的個人信仰。因此,人又是時間、器物三重敘事中,最為主要、最為核心的對象。在影片展現(xiàn)陶瓷組專家王五勝時,最為完整和具體。王五勝直到影片第一部分中段才出現(xiàn),旁白介紹了他的身份和職業(yè)路徑,他從青銅組轉(zhuǎn)來,幫助陶瓷組修復(fù)。影片詳細(xì)介紹了修復(fù)唐三彩馬的各個過程。馬缺失的馬尾、各個小組對馬尾形狀展開的討論、王五勝借助展覽素材,對唐三彩馬的修復(fù)做出進一步的計劃等,每個片段都展現(xiàn)出王五勝對文物修復(fù)工作的認(rèn)真態(tài)度。《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創(chuàng)設(shè)性在于它并不拘泥于這些工作內(nèi)容,而是嘗試從情感層面喚醒觀眾對王五勝工匠精神的情感認(rèn)同,王五勝在從展覽處往回走時,路過故宮宮殿拍照,記錄故宮變化的行為,同時也感慨著退休后能夠這樣近距離觀看故宮的機會不多了,片段中包含著王五勝對故宮的依戀,也包含著對修復(fù)工作的不舍,深深喚起觀眾對工作價值、乃至于在工作中實現(xiàn)個人抱負(fù)的理想思索。《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素材敘事目的非常明確,它借由王五勝等專家的個人記錄,呈現(xiàn)出一個專注于自身工作的人,全身心地投入這份工作,服從組織人員的調(diào)配、不斷鉆研修復(fù)技術(shù)的各個方面,這種不計代價、不計成本的自我探索,實質(zhì)上就是中國工匠在千年中師徒傳承的對于技藝和職業(yè)的尊重和信仰。
在第一部分的末尾,旁白將修復(fù)師與文物的關(guān)系總結(jié)為“在修復(fù)中與文物對話、交流、感知古今”。實際上這已經(jīng)超越了傳統(tǒng)對工作的定義,而將修復(fù)工作提升到與個人的審美情趣、價值觀念、人生理想相諧的地位。《我在故宮修文物》通過影像化,將承載與特定環(huán)境的匠人狀態(tài),完全展示給觀眾,將這種傳承千年的對技藝的專注,立體化、全方位地呈現(xiàn)。《我在故宮修文物》中蘊含著多組人物、事物的參差對照,既有古今歷史之間的對比,也有國寶與國寶間的對比,同樣還有現(xiàn)代職業(yè)的從業(yè)者與承載古代匠人精神的修復(fù)者們的對比,正是這種對比,升華了影片的格調(diào),弘揚匠人的精神與品格,對當(dāng)前時代所欠缺的精神內(nèi)涵做出了感召。
三、對“工匠”身份的探索:比較視野下本土“匠人”精神的追尋
國產(chǎn)紀(jì)錄片對匠人形象的描繪,日本和歐洲地區(qū)的“匠人”特征做出了區(qū)隔,這一點也是《我在故宮修文物》于目前國產(chǎn)紀(jì)錄片中對匠人形象描繪最為特殊的一點。從“匠人”一詞在網(wǎng)絡(luò)媒介上發(fā)酵的始末,便不難看到,在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上對匠人的推崇最開始來自日本。《美之壺》《壽司之神》《大渡海》等片中,都細(xì)細(xì)刻畫了日本“職人”肩負(fù)責(zé)任,向職業(yè)生涯高峰攀登的全部路徑。一生只做一件事,一定意義上就是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接受者對“匠人”,對工匠精神的個人定義。
《我在故宮修文物》與日本職人紀(jì)錄片有一定的相似性,它們都將鏡頭聚焦于職業(yè)匠人自身,但《我在故宮修文物》敘事和展現(xiàn)的內(nèi)容往往是多維的,并不像日本職人紀(jì)錄片那樣,將職人掌握的技藝神話,《我在故宮修文物》并不注重“造神”,而是旨在重現(xiàn)那些生活中的人,如鐘表修復(fù)組專家王津?qū)︾姳硇迯?fù)事業(yè)的專注和熱愛,源自對故宮鐘表修復(fù)手藝的傳承和對這一份職業(yè)深層次的認(rèn)可,而不是受到某些特定的職業(yè)神話的感召。電影中無數(shù)次提到“故宮擁有的西式鐘表儲量巨大,光憑鐘表組現(xiàn)在的規(guī)模,完成三千多座鐘表的修復(fù)是不可能的”,生而有涯而職業(yè)探索無涯的喟嘆,實質(zhì)上體現(xiàn)的是中國工匠對職業(yè)的專注和對事業(yè)的奉獻,這和講求極致的日本職人是有著巨大差異的。日本的工匠職人,他們的職業(yè)路徑和技藝傳承往往指向歷史和自我兩個向度。傳承家族事業(yè)或繼承瀕臨失傳的絕技是其歷史向度,將技藝不斷磨煉,使自己成為本領(lǐng)域極致、頂尖的專家,成為某某職業(yè)之“神”,則是其自我向度。中國紀(jì)錄片工匠們對技藝的追求則是多向度的展示,傳承技藝的工匠們既承載歷史的責(zé)任,同樣他們對工作所產(chǎn)生的社會價值產(chǎn)生著認(rèn)可;他們既在自我層面上追求技藝的不斷提升,又愿意與其他匠人通力合作,使作品的效果與呈現(xiàn)達到完美。
中國匠人與日本職人的兩重狀態(tài),同樣也是中日兩國文化底蘊的差異。中國紀(jì)錄片對匠人們的如實記錄,往往在不經(jīng)意之間展現(xiàn)了文化底蘊之間的差異。《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后,又推出了《大國工匠》《我在故宮六百年》等影片,中國通過這些群像式的人物展示當(dāng)代中國匠人的精神風(fēng)貌,展示傳承數(shù)千年手藝的匠人們的精神世界和個人風(fēng)骨。國產(chǎn)紀(jì)錄片對匠人的記錄顯然也必將會影響物質(zhì)時代的人們對于“物”、對于“人”在空間尺度、在時間尺度所處的位置的思考,也會從思想層面、精神層面引發(fā)人們對當(dāng)代匠人價值的思索,這或許也就是國產(chǎn)紀(jì)錄片在近年來孜孜不倦描繪“匠人”的現(xiàn)實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