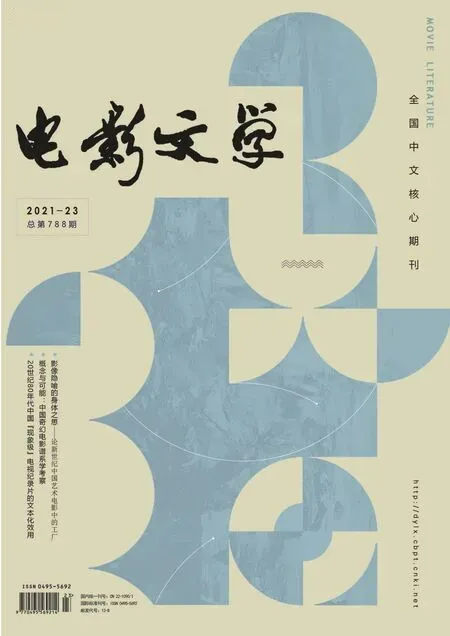發掘·旁觀·重塑:“觀察型紀錄片”的故事化敘事
張澤華
(韓國清州大學,韓國 清州 28503)
作為非虛構的藝術,記錄真實、表達真實固然是紀錄片創作者們竭盡全力所追求的目標,在創作屬性上其實無須刻意進行故事化敘事,但在追求商業成功的大背景下,紀錄片逐漸開始走下少數、精英觀眾的神壇,進入大眾化、平民化發展時期。為滿足受眾與商業需求,創作者在真實的基礎之上,在紀錄片中更多地使用故事化進行創作。所謂紀錄片的故事化,就是在拍攝和制作時突出故事性,借鑒故事片的手法,注重選取包含矛盾沖突和豐富情節的事件,在故事中刻畫人物、展示事件、傳播思想、揭示情感,使得紀錄片在敘述的過程中更具吸引力。
美國紀錄片理論家比爾·尼克爾斯則將歷史上出現過的紀錄作品分為詩意型紀錄片(Poetic Documentary)、闡釋型紀錄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觀察型紀錄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參與型紀錄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反射型紀錄片(Reflexive Documentary)、表述行為型紀錄片(Performative Documentary)等。其中觀察型紀錄片放棄解說詞、搬演等形式,不干預、不參與人物、事件的運作,攝像機如墻上的蒼蠅(Fly on The Wall),僅僅對客觀現實進行觀察。
雖然一部完全反映客觀實在的紀錄片是不存在的,不過,相比其他類型紀錄片的創作模式,觀察型紀錄片對客觀現實的依賴程度最高,對客觀現實的還原程度也最高,也由于創作形式的限制,留給紀錄片創作者進行故事化創作的空間較小。如何既能保持觀察型紀錄片反映客觀實在的創作特征,又能滿足受眾需求,將所記錄的人物、事件通過故事化的敘事方式展現出來成為當下觀察型紀錄片創作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場”(Presence)一詞是指藝術家的出場和現身,即藝術家與作品之間在情感、觀念、生活上的一種共存關系。“場”是時間和空間呈現的領地,“在場”便是人的親臨和精神的參與。紀錄片批評學界常常使用“在場”來確認創作者所記錄影像是否在真實時空下完成的而非被攝者回憶或主觀虛構出來的。觀察型紀錄片所呈現的影像大都是創作者“在場”記錄的;同時,觀察型紀錄片所強調的在場,則在真實時空創作的原則下加入了以觀察為主導的創作規范。將“場”的理論視野引入觀察型紀錄片故事化敘事的問題上,則可以根據創作者“在場”的前后分為“發掘”“旁觀”與“重塑”三個階段,而觀察型紀錄片的故事性創作也由這三階段的合力累積完成。
一、發掘:在對現實的選擇中塑造故事
“在場”之前,創作者無法把握事件的原委,自然無法得知所記錄之事是否存在令人心之所向的故事性。不過,藝術從生活中來,故事片中的故事也是創作者們從生活中進行發掘再經過藝術加工而來的,即使如觀察型紀錄片這種無法進行過多主觀介入的紀錄片類型,創作者們也有在現實世界中發掘人或事的能動性,生活中從不缺乏沖突強烈與懸念豐富的人物、事件,在滿足記錄意義的同時,選擇充滿故事性的人物、事件,哪怕沒有太多的加工,也可以讓影片變得生動好看。
首先是在題材的選擇上,選什么樣的題材,講什么樣的故事,永遠是紀錄片創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謂“選到好的題材作品就成功了一半”,說的正是題材的重要性。選擇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感興趣的題材,并圍繞觀眾的興趣進行塑造當然最利于紀錄片的故事性創作,無論是奇事怪事還是突發事件,這些外在事件本身就充滿了懸念,只要創作者能有機會沖到一線將其過程完整地記錄下來,便少不了觀眾的熱情觀看。紀錄片《76天》的創作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深入武漢醫院的重癥區,記錄下了當時醫院內真實發生的情形,新冠肺炎疫情作為緊急的醫療突發事件,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當時醫院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患者和醫護的關系又是如何?站在后疫情時期的我們,總有回溯過往的想法,帶著種種的疑惑,觀眾自然紛至沓來。
除了躍然于表面能夠把握住觀眾興趣的題材之外,其記錄意義也是紀錄片創作者需要考慮的重要要素,并且,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都能成為創作的對象,因此,在大眾視野之外具有記錄意義的題材中,能否挖掘到其故事性便考驗著創作者的創作能力。根據所選擇具體內容的不同,題材所能展現的故事性也多有區別,有些題材本身便蘊含危機,甚至無須過多地闡明具體內容,創作者便會預想到影片中將會發生的沖突。比如體育、選舉等題材的影片,顯而易見將包含競爭競技方面的內容,在零和博弈的場面中便必然存在勝負之分。即使在現實中看一場真實的比賽,我們也常常為選手們因勝負難分而捏一把汗;為所支持的選手獲得勝利而歡呼雀躍,選擇這樣的題材進行創作,自然更容易突出故事性。
不過,生活中也不乏故事性較弱的題材,這些題材在“發掘”時期很難直接梳理出起承轉合,也很難在創作伊始就看出明顯的矛盾沖突,僅僅從題材角度出發固然不好解決故事性塑造的問題,不過很多的觀察型紀錄片在選取題材時并不僅從單一題材入手,而是將幾種類型題材相互聯系,從而彌補單一題材故事性的不足。電影《棒!少年》講述了一群貧困兒童在愛心棒球隊的成長經歷。貧困兒童與體育是兩個不同的題材類型,貧困兒童以及涉及貧困問題的題材內容若僅僅聚焦貧困本身的話,其切口較小,很難在平凡的貧困生活中找到充滿故事性的記錄點。而體育類題材則是強故事性題材,在愛心棒球基地的這群少年既是實實在在的貧困少年又是在棒球運動賽場上為了榮譽頑強拼搏的選手,棒球運動的出現既彌補了貧困兒童題材敘事單一的不足,亦成為一扇貧困兒童能夠“棒”打命運的窗口。
選對人物、選好人物亦是觀察型紀錄片在“發掘”階段建構影片故事性的關鍵,同題材的選擇類似,選擇名人奇人作為創作的對象使觀眾在觀看之初就產生了懸念性的期待。一般來說,社會大眾與名人之間距離較遠,普通人鮮有接觸到名人的機會,這種距離感便賦予名人神秘的光環,名人與普通人之間的生活有何不同?他們的相關成就是如何產生的?他們工作生活又是怎樣的?圍繞這些疑慮展開創作,將名人的神秘感作為故事性敘事進行塑造,當名人光環被一一打破,觀眾的窺視欲望得到滿足,影片的故事性也就被成功塑造了出來。周浩所創作的紀錄片《大同》就將攝像機對準了當時的大同市市長耿彥波,向觀眾展現了普通人較少接觸到的政治人物的工作日常。
去除掉名人的光環,普通人又該如何選擇,如何去尋找故事性呢?在“發掘”階段,創作者與計劃拍攝對象的溝通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隨著溝通與觀察的深入,創作者對計劃拍攝對象的了解程度也逐步加深,計劃拍攝對象的性格形貌、生活經歷,以及正在或將要發生的事件也有了一個大概的摸底,這些基礎調查也是判斷所選擇的人物是否具有故事性,是否容易塑造故事的關鍵。
首先,選擇表現能力較強,性格外向的被拍攝對象自然比內向孤僻的被拍攝對象更容易塑造出故事來,這類人物敢于且善于表達,即使是“在場”創作者沒有介入的觀察類紀錄片中,幾個事件下來人物也能被觀眾所記憶。
其次,創作者在與計劃拍攝對象溝通的過程中,尋找到人物在此刻或者即將面臨的困難與挑戰,體會人物在面對困難時內心復雜的矛盾點,思考這種矛盾又是否會在未來的問題處理中被放大。選擇面對困難較大、內心矛盾激烈的人物進行創作也可以在“發掘”階段有效地進行故事化創作。2018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徒手攀巖》就將目光對準了攀巖運動員亞歷克斯·霍諾德,他將在沒有任何安全裝備的情況下徒手登上3000英尺高的酋長巖,他將如何挑戰這個困難?如何說服自己又如何說服家人?最終成功了沒有?圍繞這些疑惑,創作者就很容易在其中提取故事性從而展開創作。
二、旁觀:在對現實的記錄內容與形式中塑造故事
長期以來,觀察型紀錄片的創作者們想滿足其記錄目的,得到具有故事性的內容,只能通過“在場”的長時間觀察完成,因此,將觀察型紀錄片的創作比作墻壁上的蒼蠅,作壁上觀也由此而來。不過,拍攝紀錄片的攝影機并非安裝在被攝者家中的監控儀器,所拍攝的內容也不是監控錄像,創作者既有在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中選擇所記錄內容的權利,更有通過鏡頭語言來選擇表達方式的權利,而在記錄內容與記錄形式之間,創作者們在“旁觀”階段依然有故事性創作的空間。
在所記錄的現實內容上,首先,觀察型紀錄片的創作既無法回溯過往更不能穿越未來,想得到故事性的內容就只能老老實實從當下開始,可平常人的生活總是平淡無奇,創作者想從一日三餐中尋出故事并非易事,無論是事件的完整性還是人物經歷的完整性都需要時間的積累才能得到,故事性所需的沖突矛盾也是在有前因后果的前提下才出現的,于是,“等”自然就成了創作者們獲取故事較為重要的手段。歷經長時間等待才拍成的紀錄片不在少數,陸慶屹創作的紀錄片《四個春天》就用了四年的時間。影片伊始,導演也是從生活日常入手,介紹父母及其他家人的日常生活,除了老兩口兒的趣味生活外,也沒有更多故事性的內容,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和諧美滿的家庭卻發生了意外,姐姐慶偉的意外患病離世也使得故事情節直轉急下,電影中人物命運與現實的關系產生了強烈的沖突,觀眾了解人物事件的經過,對人物關心也越發強烈,其影片的故事性也就飽滿地展現了出來。既然并非監控錄像,創作者的攝影機也就很難一直保持開機模式,即便是等,也并非瞎等、干等,也要創作者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存在危急時刻的題材或創作者能預知到關鍵事件即將發生之前,提前架好機位,預想出將要面對的變化,制訂出不同的應對方案,精準又主動地等待故事的發生。
由于觀察型紀錄片不確定性眾多,許多事件的出現是無法預見的,為了抓住被攝者最真實的一面,不錯過極具沖突的事件,創作者也經常伺機拍攝,通過搶拍與抓拍的方式進行創作。在紀錄片《書記》中,導演周浩甚至使用了偷拍的方式記錄下了主人公收受賄賂的內容,而這一信息的出現對塑造人物、補充情節、提升故事性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等、抓、搶之外,適時地補拍也是旁觀階段完善情節信息、補全人物形象的重要方式。觀察型紀錄片中,攝影機實際所拍到的影像是紀錄片進行故事講述最重要的載體,但是在某些關鍵時刻,很多重要信息由于機位限制,不能立即被拍到,而時空經過轉換后又存在失真性與信息丟失等弊端,因此,在場擇機補拍亦是“旁觀”階段捕獲故事性的手段之一。
其次,面對盤根錯節的人物事件關系與變化無序的事態發展,創作者“在場”時很容易沒有頭緒,哪里該拍,哪里不拍很難進行較好的把握。就故事性創作而言,拍全、拍多肯定更有利于故事性的塑造,不過,在眾多信息之下,創作者也應當有果斷擯棄細枝末節的勇氣以及找到最具代表性內容與最能體現人物性格內容的才氣,把握事件、人物的一個或者幾個最典型的側面進行有的放矢的拍攝也能夠讓故事內容更豐富,人物性格更立體,從而提升影片的故事性。紀錄片《初選》中,導演拍攝了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發表演講的畫面,但是創作者一開始卻沒有直接展示人物的面部表情,而是先將鏡頭對準了杰奎琳背后緊攥著的手,接下來鏡頭上搖,與杰奎琳談笑自如的畫面相比,這一信息的出現也更加真實地體現了人物實際的緊張情緒。
在所記錄內容的形式上,作為持攝影機的人,除了拍什么,怎么拍也是由創作者來掌握的。觀眾所看到的畫面,看似是不經意中從廣袤的現實世界截取的,其實,無論是機位、構圖還是攝影機的運動,都是根據拍攝者的主觀意愿決定的。創作者對現實環境中人物與事件的真實狀況有一定把握之后,在不違背真實記錄的原則之下,使用相契合的創作手法同樣也能對觀察型紀錄片的故事性起到塑造作用。周浩的紀錄影片《大同》一開始,便是一段大同市市長耿彥波下車奔跑的場景,鏡頭在市長身后跟隨,抖動的畫面將懸念與緊張感立馬展現了出來,他為什么要奔跑?他要跑向哪里?這種慌張本身便是被拍攝對象在現實中所經歷的,而創作者又通過手持跟拍的方式將這種慌張感加強并傳遞給了觀眾。奧斯卡提名紀錄片《蜂蜜之地》中,整個村子只剩下喀迪絲一家還在居住,面對無垠的荒漠與蕭條的村莊,孤寂之感時常彌漫在喀迪絲的周圍,而影片又主要拍攝了喀迪絲怎樣捕獲野蜜蜂以及如何與蜜蜂和諧共處的經過,為了體現喀迪絲的孤寂感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創作者拍攝了大量只有喀迪絲一人的全景、遠景畫面,當人物不占據畫面的主體,喀迪絲與自然融為一體,其孤寂感也因人物只身一人的渺小被放大。
三、重塑:在對現實的重現與表現中塑造故事
在創作者認為得到了具有完整記錄意義的內容之后,素材從攝像機轉向了剪輯臺,觀察型紀錄片的創作也開始由“旁觀”進入“重塑”階段。觀察型紀錄片的剪輯也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影片創作,創作者雖然拿到了對素材的控制權,但也需要創作者在所得到的素材基礎之上進行取舍,過多使用其他途徑的素材或是過多添加對內容的主觀解讀都是觀察型紀錄片創作所不允許的。因此,當素材拿到手中,創作者不僅要思考向觀眾重現所記錄事實時如何進行故事化塑造,更需要思考當所記錄事實故事性不足時如何通過恰當的表現手法來進行故事化的塑造,而“重塑”,亦是重現與表現的結合體。
觀察型紀錄片在剪輯時的重現,其實就是創作者們將“旁觀”階段所記錄的事實梳理之后進行復述。不過,觀察型紀錄片在前期策劃階段既無法確認準確的拍攝完成時間,也無法制作精細的拍攝腳本,出于防止意外發生、不遺漏重要的內容,促成故事成形等多方面考慮,創作者“在場”階段往往選擇多組對象,使用多個機位同時拍攝,這也致使素材量陡增,其成片的耗片比也常常大得驚人。因此,面對海量的素材,觀察型紀錄片首先要做的就是將素材從雜亂歸至流暢,哪些素材是有意義的,哪些又具備故事性,不僅需要剪輯人員耐心挑選,更需要與“在場”的創作者們進行更多的溝通。同時,廓清所記錄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辨識人物在事件前后的行為變化,建立事件與事件、人物與人物、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系亦是梳理素材過程中塑造影片故事化必不可缺的部分。
當事件、人物脈絡梳理清晰,創作者也就可以將流暢的素材向統一的故事邁進。在較少影響事實的基礎上,舍去不必要的人物、事件,選擇記錄到的較為完整的人物與事件進行重現;同時,確定故事的主要線索與關鍵人物,并盡量圍繞危機事件或對人物有重要變化的事件展開講述,多選擇沖突激烈、懸念性強的內容,最后再按照開端、發展、高潮、結尾等符合故事創作規律的順序進行組合,這樣不僅在內容上由分散走向了統一,也完成了故事化的塑造。紀錄片《張藝謀的2008》的創作就緊緊圍繞著名導演張藝謀2008年的工作日常展開,作為著名的導演,張藝謀往往同時身兼眾多職位,有多個項目同步開展,但是紀錄片對導演的其他項目一帶而過,沒有展開講述,而是牢牢地抓住了張藝謀創作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臺前幕后,并以奧運會開幕式作為全片最大的危機事件營造懸念與沖突進行故事性的創作。
不過,在實際的創作過程中,的確有很多素材即使經過梳理依然存在故事性不足的問題。并且,觀察型紀錄片所記錄的存在大型危機事件的題材也經常由于后期的剪輯發行等造成其時效性較差,很多觀眾早已在新聞媒體上知道了真實事件的最終結果,若是創作者再以此進行故事化塑造,其懸念性勢必大減。
在蒙太奇的理論中,通過對影像的拼接可以對敘事時空進行再造與擴展,甚至可以產生與實際記錄所不同的新的意義,這種拼接自然是純粹的創作者的介入創作,是表現內容的手段。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對紀錄片的故事化塑造無疑是有利的,但在觀察型紀錄片時空統一的真實性塑造上也無疑是危險的。電影理論學家巴贊則認為蒙太奇的創作手法在紀錄片中應該被禁用,不過,在創作者潛意識的影響與當今紀錄片市場化運行的大環境下,要求創作者們符合時空統一的手法重現現實較難實現,而事實上,當下完全符合觀察型紀錄片創作規律進行創作的影片也不多見,學界也早有在當今紀錄片剪輯中是否依然禁用蒙太奇的討論。從故事性塑造的角度而言,規矩并非一成不變,蒙太奇的使用也不應淪為吾之砒霜,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有限度地巧用、妙用蒙太奇也應當符合觀察型紀錄片的創作規范。
敘事蒙太奇在本質上還是以講故事為中心,創作者們將素材重新拼接,打破原本的時空關系并非想要改變、曲解內容,而是期望在原本素材中尋找新的敘事結構與敘事關系,從而增強紀錄片的故事性。敘事蒙太奇中所包括的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重復蒙太奇等多種手法如今也常常在觀察型紀錄片中出現,抗疫紀錄片《76天》中,導演就使用了交叉蒙太奇的方式,將醫院里面的醫生、護士、病人所面臨的不同情形的內容穿插在一起,既向觀眾展現了疫情之下醫院內的全貌,讓觀眾看到了不同身份的處境,還迅速地理清了人物的關系。而《棒!少年》中則以最后一場棒球比賽為中心,將球場上比賽的棒球少年,球場邊的教練與遠在北京看比賽直播的師爺共同分成了三段平行敘事內容,影片通過剪輯在三段平行內容中來回切換,一場甚至都沒有大量觀眾觀看的比賽在不同時空的轉換下緊張感十足,懸念氣氛濃郁。
當然,蒙太奇還有理性蒙太奇與表現蒙太奇等多種手法。理性蒙太奇作為純粹主觀表現創作者思維的手法,在紀錄片的創作中較少使用。不過,當下的很多觀察型紀錄片中一些含有表現蒙太奇內容的作品開始出現。按照客觀性的原則來說,表現蒙太奇中無論是心理蒙太奇、抒情蒙太奇還是隱喻蒙太奇都是創作者對事件的表達或是對人物內心的表現,是創作者主觀的思維體現,客觀存在中的人的內心是復雜的,創作者使用表現蒙太奇的手法其實是對現實的僭越行為,理應禁止。不過,隨著創作的深入,創作者對被攝對象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在素材本身故事性不強,人物扁平且創作者對人物深度理解的情況下,少量地、恰當地使用表意蒙太奇用來幫助觀眾對事件的理解,表現人物的內心實在,也逐漸被大眾所接受。電影《棒!少年》中,棒球隊隊員馬虎由于脾氣暴躁最終與其他室友鬧掰,孤身一人在房間睡覺,但是小孩子一個人睡覺又怕黑。創作者記錄下了馬虎上床用安全帶將自己綁住又將玩偶抱在懷中的場景,接著影片中卻出現了窗外映照的樹影與車燈閃爍的空鏡頭畫面,在燈光照耀之中,這些畫面與前面馬虎一個人睡覺的內容產生了聯系,從而利用心理蒙太奇的手法表現了馬虎此時的害怕與一人睡覺的落寞心情。
結 語
從1997年因為使用交叉蒙太奇初選就被評委淘汰的《春節的故事·回家》,到如今妙用故事化敘事進而拿下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的《蜂蜜之地》、拿下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的《棒!少年》,觀察型紀錄片故事化敘事的尺度與學界、業界的接受度也在發生著變化。如開篇所述,紀錄片本身其實無須刻意像故事片一樣進行敘事,不過,觀察型紀錄片的真實性與故事性也并非完全對立的矛盾,守住“真”底色的同時,在“發掘”“旁觀”與“重塑”階段依然大有故事可講。在市場競爭激烈的當下,觀察型紀錄片的創作者在追求“真”的同時,也更應熟稔故事化敘事的手段與方法,為紀錄片魅力的展現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