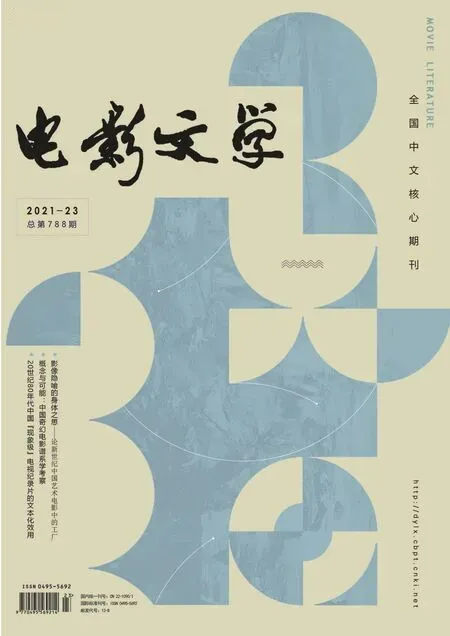作者電影《熱帶往事》的敘事風(fēng)格與審美維度
田小瑞
(新鄉(xiāng)學(xué)院新聞傳播學(xué)院,河南 新鄉(xiāng) 453003)
2016年,寧浩導(dǎo)演的“壞猴子影業(yè)”公布了一項(xiàng)旨在培養(yǎng)國(guó)內(nèi)新人導(dǎo)演,為華語(yǔ)影壇注入新鮮血液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jì)劃”,五年來(lái),陸續(xù)推出了《繡春刀·修羅戰(zhàn)場(chǎng)》《我不是藥神》《甜美生活》《云水》《受益人》等兼具商業(yè)性與藝術(shù)性的優(yōu)秀影片。在新人導(dǎo)演搭檔資深影人的創(chuàng)作模式下,扶植并培育了路陽(yáng)、文牧野、申奧等具有個(gè)性與創(chuàng)造力的新人導(dǎo)演。《熱帶往事》也是在這一過(guò)程中誕生的作品。該片是溫仕培導(dǎo)演的處女作,并于2018年入圍第68屆柏林國(guó)際電影節(jié)天才項(xiàng)目市場(chǎng)單元,獲得VFF創(chuàng)投大獎(jiǎng)。該片由張艾嘉、彭于晏、王硯輝等人主演。
《熱帶往事》的故事背景設(shè)定在1997年廣州的盛夏,講述了由一個(gè)犯罪故事引發(fā)的寡婦、維修工人與警察三人之間的糾纏,以及由此所體現(xiàn)出的亦善亦惡的復(fù)雜人性。影片的地域特征十分明顯,由廣州盛夏的灼熱潮濕之感體現(xiàn)出人性深處的不安躁動(dòng),極具導(dǎo)演的個(gè)人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了一種類(lèi)型片模式下的獨(dú)特氛圍感,同時(shí)在類(lèi)型化之外做出了新的嘗試。作為一部懸疑犯罪片,《熱帶往事》采用了嫌疑人的敘事視角,由此去窺見(jiàn)受害人以及破案者的行為軌跡,為影片增添了新鮮感與神秘感。
一、“作者電影”中的氛圍敘事
1948年,法國(guó)電影理論家亞歷山大·阿斯圖在《新先鋒派的誕生:攝影機(jī)筆》中提出,“攝影機(jī)應(yīng)像文學(xué)家的筆一樣,去自由自在地描寫(xiě)事物,必須具有作者自己的個(gè)性,即要確認(rèn)電影作者的地位”。在法國(guó)電影新浪潮中,導(dǎo)演的地位被進(jìn)一步提升,電影被認(rèn)為是表達(dá)導(dǎo)演個(gè)人生活經(jīng)驗(yàn)和情感訴求的藝術(shù)載體。法國(guó)電影理論宗師安德烈·巴贊更從導(dǎo)演監(jiān)管電影的視聽(tīng)與文字等基本元素的角度說(shuō)明,“現(xiàn)在都要以電影‘作者’,而不是編劇或文本作者等來(lái)衡量”,我們可以認(rèn)為,“作者電影”的概念由此確立。毫無(wú)疑問(wèn),在此類(lèi)電影中,導(dǎo)演處于創(chuàng)作的中心位置,決定著影片的整體風(fēng)格與敘事模式。中國(guó)電影從第五代導(dǎo)演開(kāi)始走向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導(dǎo)演的個(gè)人風(fēng)格也愈加明顯。但當(dāng)我們?nèi)ヌ骄侩娪氨澈蟮纳鐣?huì)與歷史背景時(shí)總能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黃土地》還是《紅高粱》,其實(shí)都根植于中國(guó)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huì)中的歷史文化根基與社會(huì)語(yǔ)境中,以一種集體記憶的形式呈現(xiàn);到了第六代導(dǎo)演,如婁燁、賈樟柯、王小帥、寧浩等人,已經(jīng)具有了各不相同的、獨(dú)立的、專(zhuān)注于不同社會(huì)文化角度的敘事風(fēng)格。《熱帶往事》便是這樣一部作品,而其最明顯的敘事風(fēng)格,就是建立在出色的視聽(tīng)語(yǔ)言上的氛圍感營(yíng)造。
《熱帶往事》的故事內(nèi)容非常簡(jiǎn)單,作為一部懸疑犯罪片,其人物關(guān)系構(gòu)成甚至可以說(shuō)是極簡(jiǎn)的:被害人妻子梁媽?zhuān)厥抡咄鯇W(xué)明,警察陳耳,重要角色僅此三人而已。被害人老梁和幕后兇手甚至沒(méi)有以正面的鏡頭出現(xiàn)過(guò),成為隱匿在影片黑暗環(huán)境中的影子。盡管劇本薄弱成為影片讓人詬病的原因之一,但這也正為我們證實(shí)了一種拍攝方式的可行性——當(dāng)視聽(tīng)語(yǔ)言從故事中獨(dú)立出來(lái)單獨(dú)進(jìn)行敘事,故事內(nèi)容是可以進(jìn)行讓步的,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jié)金棕櫚獎(jiǎng)提名的刁亦男導(dǎo)演的《南方車(chē)站的聚會(huì)》也是這類(lèi)影片,可以被歸類(lèi)為華語(yǔ)“新黑色電影”的序列中。不過(guò)《熱帶往事》在風(fēng)格化上更加大膽。
首先,影片在時(shí)空結(jié)構(gòu)的設(shè)置上,采用了時(shí)空交錯(cuò)重組的倒敘式結(jié)構(gòu),影片以王學(xué)明在獄中的自敘開(kāi)始講述,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已經(jīng)向觀眾交代了影片的結(jié)果,弱化了類(lèi)型片的懸疑性。換言之,影片從一開(kāi)場(chǎng)便表明了敘事重心與態(tài)度——并不在故事內(nèi)容上。影片不斷以現(xiàn)實(shí)和夢(mèng)境、回憶相疊的剪輯方式,在現(xiàn)實(shí)、過(guò)去、夢(mèng)境間游移,打造出一種曖昧迷離的時(shí)空感。影片從王學(xué)明的視角出發(fā),在他出獄前一天,開(kāi)始回憶入獄的經(jīng)過(guò)。整個(gè)回憶又分為車(chē)禍前與車(chē)禍后兩個(gè)部分,以及在此過(guò)程中王學(xué)明由內(nèi)疚茫然,到墮落,再到自省的內(nèi)心情感轉(zhuǎn)變。這個(gè)敘事亦虛亦實(shí),現(xiàn)實(shí)與夢(mèng)境、現(xiàn)實(shí)與回憶、回憶與夢(mèng)境不斷交錯(cuò),時(shí)空像拼圖一樣被不斷拆分重組,帶給觀眾如身處云霧中的觀影體驗(yàn)。同時(shí),為了避免在此過(guò)程中觀眾產(chǎn)生時(shí)空的錯(cuò)亂感以影響對(duì)內(nèi)容的理解,影片巧妙地以幾個(gè)具有象征意義的標(biāo)志性意象來(lái)進(jìn)行標(biāo)簽式的提醒:第一個(gè)是“牛”的意象。牛在片頭首次出現(xiàn),在王學(xué)明對(duì)車(chē)禍現(xiàn)場(chǎng)的回憶中再次出現(xiàn):當(dāng)天王學(xué)明開(kāi)車(chē)上路,因?yàn)榈缆飞贤V活^牛而變道,發(fā)生車(chē)禍。牛有著老實(shí)軟弱的性格,正如王學(xué)明一開(kāi)始的人物特征,被莫名卷入一場(chǎng)謀殺案中,背負(fù)著內(nèi)心的譴責(zé)。第二個(gè)意象是反復(fù)出現(xiàn)的車(chē)內(nèi)搖獎(jiǎng)廣播。在影片以王學(xué)明的視角和上帝視角兩次對(duì)車(chē)禍現(xiàn)場(chǎng)進(jìn)行敘事時(shí),車(chē)內(nèi)都播放著兌獎(jiǎng)號(hào)碼。略顯刺耳的女聲在對(duì)數(shù)字進(jìn)行逐一播報(bào),烘托緊張氣氛的同時(shí),也起到了一種時(shí)空標(biāo)記的刻度性作用。影片在“兩個(gè)號(hào)碼”中又插入了另一段敘事,因?yàn)樘?hào)碼的連續(xù)性,使得敘事被切斷沒(méi)有了那么強(qiáng)的割裂感,也更易于觀眾理解影片的時(shí)空調(diào)度,自覺(jué)地將同一個(gè)時(shí)空的敘事連貫起來(lái),在腦內(nèi)構(gòu)建故事拼圖。
其次,影片的敘事視角在不斷地變換,對(duì)于一個(gè)事件往往會(huì)以多個(gè)人物視角進(jìn)行敘事與信息補(bǔ)充,同樣呈現(xiàn)出一種拼圖式的拼湊感。例如,對(duì)車(chē)禍現(xiàn)場(chǎng)的敘事,分別采用了王學(xué)明的主觀視角、王學(xué)明的夢(mèng)境視角和客觀的“上帝視角”進(jìn)行講述。在王學(xué)明的主觀視角上,是他撞死了老梁并將其埋尸。在夢(mèng)境中,老梁被人打了兩槍?zhuān)鴣?lái)自第三方的“上帝視角”讓夢(mèng)境的內(nèi)容由虛轉(zhuǎn)實(shí),當(dāng)天老梁被人追殺,身中兩槍?zhuān)趥}(cāng)皇逃竄中被王學(xué)明撞到。這樣的表達(dá)方式在道德評(píng)價(jià)的角度上也出現(xiàn)了一種曖昧性:老梁到底是否因王學(xué)明而死,是一個(gè)得不到答案的謎團(tuán),王學(xué)明這個(gè)人物形象也由此呈現(xiàn)出善惡之中的曖昧性。再如,在王學(xué)明與神秘兇手巷中追逐的一場(chǎng)戲中,影片分別以王學(xué)明和警察陳耳兩個(gè)角度進(jìn)行敘事。盡管某些情節(jié)出現(xiàn)重復(fù),但無(wú)疑使影片的風(fēng)格性更強(qiáng)。導(dǎo)演溫仕培以將時(shí)空片段拆分重組的方式,建構(gòu)起整部影片迷離、曖昧、復(fù)雜,代入感極強(qiáng)的個(gè)性化敘事,讓觀眾得以深入王學(xué)明的內(nèi)心情感世界,深切地感受到人物情緒的變化。在一些追逐與打斗場(chǎng)景中,影片所呈現(xiàn)出的也是與常規(guī)犯罪類(lèi)型片所不同的敘事風(fēng)格,更加注重對(duì)整體氛圍感的營(yíng)造。
二、“罪與罰”中的審美維度
《熱帶往事》的鏡頭風(fēng)格是非常突出的,正如上文所說(shuō),畫(huà)面構(gòu)圖、鏡頭調(diào)度、色彩營(yíng)造、配樂(lè)等都是為影片的敘事風(fēng)格服務(wù)的。在20世紀(jì)90年代的廣州狹窄逼仄的居民區(qū)中,潮濕汗膩的天氣,以及生活在其中不安躁動(dòng)的人們——影片運(yùn)用了大量的細(xì)節(jié)描寫(xiě)去刻畫(huà)街頭巷尾的市井地域性特征。同時(shí),運(yùn)用了大面積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色,如紅綠對(duì)比,以顏色的不協(xié)調(diào)感體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的躁動(dòng)。王學(xué)明與梁媽是影片的主要人物,一個(gè)是肇事逃逸的空調(diào)維修工,一個(gè)是風(fēng)韻猶存的寡婦。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是影片前半段主要表現(xiàn)的對(duì)象。王學(xué)明在得知自己撞死的是梁媽的丈夫后,有意地接近她、幫助她,尋找一個(gè)自我救贖的機(jī)會(huì)。當(dāng)嫌疑人走進(jìn)了受害者家屬的家庭時(shí),一明一暗兩種視角構(gòu)建出了一個(gè)充滿(mǎn)張力的敘事空間。
梁媽在經(jīng)歷了中年喪子又喪偶的悲痛后,嘗試從孤獨(dú)中拯救自我,潮濕都市中,兩個(gè)漂泊、孤獨(dú)的靈魂之間產(chǎn)生了羈絆。按照這種劇情發(fā)展,觀眾自然地以為兩人之間會(huì)產(chǎn)生更加深刻的情感糾葛,甚至是犯罪片中并不少見(jiàn)的禁忌之戀。但影片卻沒(méi)有按照這種思路發(fā)展下去,當(dāng)王學(xué)明向梁媽坦白“是我撞死了你丈夫后”,卻意外地得知他是被槍打死的,至此,梁媽這個(gè)女性形象的張力大幅減弱,在后半段甚至逐漸隱去。影片開(kāi)始轉(zhuǎn)向王學(xué)明自身在金錢(qián)與暴力的誘惑面前走向墮落的過(guò)程。在王學(xué)明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清晰的人物狀態(tài)轉(zhuǎn)變過(guò)程:由負(fù)罪后坦白,到徹底墮入暴力,顯露出人性的復(fù)雜之處。
俄國(guó)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著作《罪與罰》中刻畫(huà)了制造了震驚全俄的謀殺案后又懺悔自首的大學(xué)生拉斯科爾尼科夫這一人物形象,在其復(fù)雜波動(dòng)的心理變化中,我們可以瞥見(jiàn)俄國(guó)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犯罪之后,時(shí)常做噩夢(mèng),巨大的精神壓力使他時(shí)刻處于崩潰的邊緣:“這樣的怪聲、哀號(hào)、切齒、流淚、拳打和咒罵,他從來(lái)沒(méi)有聽(tīng)見(jiàn)過(guò),他絕想不到有這樣的殘忍、這樣的瘋狂。他恐怖地在床上坐了起來(lái),忽然發(fā)抖起來(lái)……”在小說(shuō)中有這樣的描寫(xiě),可以類(lèi)比于《熱帶往事》中王學(xué)明的夢(mèng)境場(chǎng)景,都體現(xiàn)出了人物內(nèi)心狀態(tài)之混亂,在尋求救贖的路上,走上了狂歡化的犯罪道路。在此之前,王學(xué)明曾嘗試過(guò)懺悔,他把老梁的遺孀當(dāng)作懺悔的對(duì)象,用打跑前來(lái)要賬的黑社會(huì)、制止梁媽投湖等行為來(lái)減輕內(nèi)心的罪惡感,當(dāng)他詢(xún)問(wèn)梁媽“如果兇手說(shuō)對(duì)不起,你會(huì)原諒他嗎”時(shí),便是在期望她能拯救自己墮入罪惡的心靈。但梁媽說(shuō)“不會(huì)”,并告訴了他一個(gè)更加黑暗的真相。由此,影片彰顯出“新黑色電影”的審美特征,即更加內(nèi)化于個(gè)體生命的暴力性。
王學(xué)明的暴力性逐漸呈現(xiàn)出狂歡化的趨勢(shì)。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shuō)(并不局限于《罪與罰》)對(duì)于人物精神困境的關(guān)注,“關(guān)注人的道德、精神和靈魂深處的掙扎”,在對(duì)人物內(nèi)心細(xì)幽之處的刻畫(huà)中,我們得以感受其狂歡化的精神世界。在梁媽處尋求救贖無(wú)果后,王學(xué)明在街頭隨機(jī)沖入斗毆的人群,以肢體暴力與疼痛維系瀕臨崩潰的精神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一種迷幻的精神世界。而隨著他對(duì)案件的深入調(diào)查,他在火車(chē)站拿到了老梁的致命錢(qián)財(cái),并遭到了冷血?dú)⑹值淖窔ⅰM鯇W(xué)明帶著錢(qián)財(cái)疲于奔命,在小巷追逐的一場(chǎng)戲中,影片在一些動(dòng)作的設(shè)計(jì)上刻意呈現(xiàn)出一種時(shí)間的停滯感,讓人物身處窒息般的緊張感中,以激發(fā)人物內(nèi)心的暴力性。在緊繃的精神壓力之下,王學(xué)明似已“成魔”,當(dāng)他拿起磚頭對(duì)著躺在地上早已動(dòng)彈不得的兇手不停地毆打時(shí),人物的自我意識(shí)已經(jīng)喪失,從而完成了狂歡化的犯罪。縱觀王學(xué)明這個(gè)人物形象,他在偶然間背負(fù)上一條人命的罪責(zé),又在尋求心靈救贖的路上墮入更深的黑暗。影片以他在獄中回憶的視角展開(kāi)敘事時(shí)就提出了這個(gè)問(wèn)題:出獄之后,一切會(huì)更好嗎?所犯的罪過(guò)會(huì)得到原諒嗎?在影片的最后,王學(xué)明出獄時(shí),盡管梁媽并沒(méi)有出現(xiàn),但他奔跑在陽(yáng)光中輕快的身影,似乎是影片給出的一個(gè)善意的答案。
作為新人導(dǎo)演的處女作品,《熱帶往事》呈現(xiàn)了許多讓人驚艷的“作者電影”風(fēng)格特征,讓人們看到了華語(yǔ)“新黑色電影”對(duì)于類(lèi)型化的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作者風(fēng)格的凸顯。影片以極為出色的視聽(tīng)語(yǔ)言重構(gòu)時(shí)空線(xiàn)索,以色彩的沖突體現(xiàn)環(huán)境的悶熱壓抑,環(huán)境特征又為人物的情緒服務(wù),從而人物所處的邊緣性生存場(chǎng)域被凸顯。在夢(mèng)境與真實(shí)的交織中,個(gè)體的個(gè)性與心理活動(dòng)更加豐富,最終指向了影片對(duì)于人性復(fù)雜曖昧處與孤獨(dú)生存狀態(tài)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