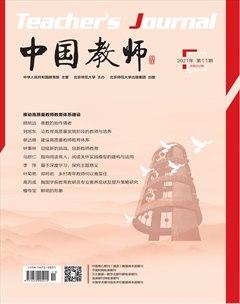魯潔先生二三事

讀書一定要仔細
1990年7月12日,我33歲生日當天收到南京師范大學(以下簡稱“南師大”)研究生部發(fā)來的錄取通知書,我被錄取為1990級教育學原理博士研究生,導師是魯潔教授。9月初,赴南師大報到。
開學不久,校研究生會改選,校團委和研究生部的意見是請一位博士研究生出任校研究生會主席,選中我為候選人。能在南師大這所百年老校當研究生會主席,內(nèi)心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和滿足,這是多么大的榮譽啊!這里可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陳鶴琴、吳貽芳等一眾教育巨星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我如愿以償?shù)禺斶x了。上任伊始,我以滿腔熱忱投入了研究生會的工作之中。對外,和各高校新任研究生會主席聯(lián)絡籌措舉行江蘇高校研究生會代表大會,推出在寧高校研究生志愿者行動方案。對內(nèi),調整研究生會所屬各部的人選和職務,籌備新年晚會的節(jié)目。整天忙于事務性工作,像個沒頭蒼蠅似的跑來跑去,根本沒有時間閱讀導師布置的專業(yè)書目。
次月,首個周一下午是跟導師見面談學習的時間。魯老師問道:“上次布置的《兒童的道德判斷》讀了嗎?”師兄和師弟回答讀了,我也隨口“嗯”了一聲。“那就老趙(報到后第一次見面先生就以“老趙”稱呼我,而稱呼師兄和師弟都是直呼其名,我權且認為是老師的詼諧和幽默)先來吧,說說讀后感。”既然點名讓我先來,便自不量力地侃侃而談。沒幾分鐘,先生皺著眉頭說了一句:“好像讀得不仔細嘛!”我一下子愣住了。真實的情況是由于忙于研會的工作,魯老師布置的書根本就沒讀。那種尷尬的場面使我無地自容,非常慚愧:沒讀就沒讀,為什么不誠實?為什么要騙先生呢?見我一時語塞、神情窘迫,先生叫師兄接著談。那是我們1990級博士生首次讀書報告會,先生看似輕描淡寫實則一語中的的批評深深地刺疼了我,思想上受到極大的震撼。思前想后,我下定決心向校團委、研究生部遞交了辭呈,辭去學校研究生會主席職務。后經(jīng)有關領導談話協(xié)調,我改任副主席分管學術部和文藝部,重訂學習規(guī)劃,將研究生會的工作和自己的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在工作的同時專心讀書做學問,在學術雜志上發(fā)表了論文《創(chuàng)建中國特色的民族德育學》。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魯老師當年的詰問,我就沒有今天專業(yè)方面的成就了。
幼教觀念現(xiàn)代化
1995年新學期開學不久,魯老師給了我一份《學前教育研究》編輯部的約稿函,主編邀請魯老師寫一篇幼兒教育現(xiàn)代化方面的文章,我覺得魯老師的意思是讓我做點查閱資料,寫點文獻綜述,想著我一個學教育學原理的,為什么魯老師讓我去弄學前教育的事呢?既然任務已經(jīng)下達,也沒多想就動手做了起來。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曾經(jīng)讀過皮亞杰的《發(fā)生認識論原理》等學前教育的書籍,所以這任務并不費事。記得是在華夏教育圖書館的邵玉娟老師的幫助下,十來天工夫就把稿子交給了先生。
半個月后,魯老師把“作業(yè)”退了回來,上面布滿密密麻麻的鉛筆修改的文字,有的段落直接重寫過,后面附了五六條修改意見和需要進一步閱讀的文獻。這使我很受震撼。雖然讀博之前就在《教育研究》上發(fā)表了《思想品德三環(huán)結構理論初探》的論文,但是看到學前教育的論文原來是這樣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的,深受啟發(fā)和鼓舞。當我按照魯老師的意見修改之后,魯老師給我當面批改,斟字酌句、推敲琢磨,那一幕成為后來我指導研究生的“方法論開篇”。
之后,成稿寄到編輯部主任處,編輯很快便將排版后的終校稿回發(fā)給我勘校,第一眼就發(fā)現(xiàn)魯老師的名字竟然排在后面,我立即致電編輯部主任,他說這是魯老師的意思,我頓感胸膛中暖流涌動,有一種鼻酸淚目的感覺。我明確表示,文章的第一作者理所應當是,也必須是魯潔先生。全文的主題立意、框架設計、邏輯結構、段落層次皆出自先生之手,如此排名,我情愿退出。主任也認為我的話有道理,問我是不是再向魯老師報告一下,我講不必了,請主任按照我們商量的意見去做。這是我第一次“拂”先生的意思,這才有了《學前教育研究》1995年第6期首篇文章《幼兒教育現(xiàn)代化的關鍵─觀念現(xiàn)代化》(魯潔,趙志毅)一文的誕生。文章指出:“隨著我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全面推進,教育現(xiàn)代化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這是因為沒有現(xiàn)代化教育所提供的現(xiàn)代化人才資源,現(xiàn)代化社會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作為教育的基礎之基礎的幼兒教育,由于它的突出的‘面向未來性,它所培養(yǎng)的對象都將成才、工作于下一世紀,為此,怎樣在各種幼教機構中實施符合現(xiàn)代化要求的教育,為培養(yǎng)21世紀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新人打下良好基礎,這不能不成為人們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些26年前的見解在政府提倡“雙減”的今天讀起來亦不乏深刻的洞見。浙江師范大學幼兒師范學院的王春燕教授說,這篇文章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學前教育學術刊物上較早明確提出幼兒教育觀念現(xiàn)代化的理論文獻,對中國學前教育影響深遠。
后來,我才明白了先生在博士生課堂上諄諄告誡我們的一段話的深刻含義:“教育工作者,無論是理論研究者還是一線的教師,皆應關注幼兒意識和行為的發(fā)生學研究,只有搞清楚兒童思想意識、語言表達、行為表現(xiàn)的發(fā)生機制,才會因勢利導地提出正確的教育對策,采用正確的教育方法。”這話深深地在我腦海里扎根,對我的學術生涯起到了指引航向的重要作用。是啊,國家辦教育的目的是要改造我們的社會,教師改造社會的目標是通過改造學生而實現(xiàn)的。教師要改造學生,必須弄清楚學生言行的發(fā)生機制,而對學生的思想意識、語言行為的發(fā)生機制的理解與把握的最好時機莫過于兒童的早年,即個體的童年時期。從那以后,我開始關注學前教育領域的內(nèi)容和學術動態(tài),深入幼兒園實施系統(tǒng)的教育實驗,在魯老師支持下申報了幼兒教育國家級課題,帶領幼兒園課題組的老師在學前教育領域努力耕耘、發(fā)表系列論文,專業(yè)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難忘西湖中秋夜
記得是1996年的秋天,南師大教育科學研究所利用中秋節(jié)組織老師到杭州游覽。大早出發(fā),中午到達,下午是自由活動時間。先生說想去西湖孤山西泠橋畔的秋瑾墓看一看。在這之前我只知秋瑾是在紹興被殺,卻不知杭州有座秋瑾墓。我和女兒苗苗與先生同行,在秋瑾雕像前鞠躬致敬,聽先生講秋瑾之所以稱鑒湖女俠的故事:秋瑾家鄉(xiāng)紹興有個鑒湖,所以她自稱鑒湖女俠。秋瑾為了尋求救國真理,離開家鄉(xiāng)東渡日本加入了光復會、同盟會,積極投入反清革命的偉大斗爭,后因起義失敗被俘,英勇就義。秋瑾其實是有機會逃掉的,但是她沒跑,與譚嗣同一樣,她抱定了犧牲的決心,犧牲時才32歲。因其生前有“埋骨西泠”的愿望,好友吳芝瑛與徐自華將其遺體安葬在西泠橋畔。先生說,秋瑾不僅是一位尋求真理的革命先驅,而且還是一位近代文學史上的杰出女詩人,她的臨終絕筆引用清代詩人陶宗亮的詩句“籬前黃菊未開花,寂寞清樽冷懷抱。秋風秋雨愁煞人,寒宵獨坐心如搗”中的“秋風秋雨愁煞人”一句作為遺言而被后人傳誦。我問先生,秋瑾被殺是在1907年7月中旬,正值炎炎夏日,她為什么書寫秋天的景象?先生說:“秋天多帶有悲涼肅殺色彩,自古逢秋悲寂寥,蕭索秋天,綿綿秋雨,瑟瑟秋風,肅殺的冬季即將來臨,大地上沒有了勃勃生機,正是萬物凋零的時節(jié),在秋風秋雨之中,心情更是惆悵哀涼。這一詩句表達了秋瑾對封建黑暗統(tǒng)治的反抗、對國家和民族的深情,也表達了女革命家憂國憂民、壯志未酬、面對死亡的悲憤心情。辛亥革命時期,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徐錫麟等人于1905年為培養(yǎng)訓練革命武裝起義軍事干部在紹興創(chuàng)辦大通學堂。1907年,秋瑾曾接替陶成章、徐錫麟,被推薦為大通學堂督辦。大通學堂勇開中國師范教育體育專修科和女子校長之先河。”之前,我只知道她是一位慷慨赴死的巾幗英雄,那一刻我才知道秋瑾原來還是教師、校長出身的革命者,是我們教師的先驅和楷模。
之后,魯老師想下湖轉轉,在晚霞中我們一起乘坐手劃船游覽西湖。艄公悄悄地問我:“老哥,是帶著老母親和孩子出來玩的吧?”我隨口“嗯”了一聲,沒有說什么,我對這種“誤解”很是受用。船上備有暖壺和龍井茶,平素里先生喜歡用她自己的保溫杯,女兒苗苗用船上的開水新沏了一杯龍井茶遞給魯奶奶,先生微笑著接了過去,擰開蓋子輕輕地吹開浮在上層的茶葉呷了一口,靜靜地望著遠處燦爛的晚霞。我不敢打攪,生怕擾亂了她的心境。她是在思念仙逝于香港的父親,還是在想念正在為香港回歸祖國而殫精竭慮的哥哥魯平(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我不知道,也不便多問,聯(lián)想到下午的參拜秋瑾雕像,我覺得先生心中有一團熾熱的理想的火焰在燃燒,而這正是年輕教師所缺少的。三潭印月附近的小瀛洲本可以下船走走的,但天色已晚,我們沒有下去。一輪新月爬上天空,滿天繁星眨巴著眼睛,小船靠了岸,我們離船上岸,與船公告別。
中秋夜,那個香港回歸祖國前的最后一個中秋夜,那個充滿著回憶與念想、思緒與期待的中秋之夜永遠地定格在我的心扉上。謹以白居易的《憶江南三首》中的名句告慰魯潔先生的在天之靈: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
山寺月中尋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頭。
何日更重游?
(作者系宿遷學院文理學院教育系教授)
責任編輯: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