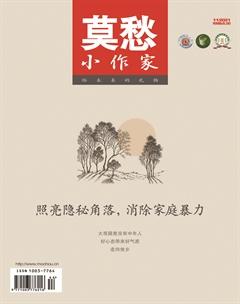用文字照亮隱秘的角落
“國際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稱作“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這一紀念日確立的初衷是消除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在2015年8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國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采用去性別化的用詞“家庭成員”,來定義家庭暴力行為的受害者。隨著時代的發展,“家庭暴力”一詞也包含了更多的含義。當家暴的受害者不再只是婦女,形式也不再只是普遍認知的身體虐待,還包括情感冷遇、言語辱罵等更多形式,我們也更關注定義背后的問題:怎樣才是對待親人的合適方式?怎樣識別、幫助遭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怎樣從整個社會的層面,減少家庭暴力,促進更和諧的交流和溝通?
有人把家庭暴力稱為來自最隱秘的角落里最無力反抗的惡。對于這種惡,每個時代都有作家用文字來描寫、揭露、批駁。閱讀這些作品,我們或許可以增強些許抵御的能力。直視它——深切地理解它意味著什么,再識別出它所有的形態。
有人用文字照亮隱秘的角落,有人從文字中捕獲成長的勇氣。
以愛之名:來自親密關系的暴力
“蕭紅鼻青臉腫地出現在他們面前時,朋友們的心里就都了然了。”這是電影《黃金時代》中的片段,蕭軍和蕭紅參加聚會,朋友發現蕭紅眼角有傷,問她,她說“我自己不小心撞到硬東西上了”。結果蕭軍冷冷地說:“干嗎替我隱瞞,是我打的。”
蕭紅挨過蕭軍的打,這一情節并非虛構,作家靳以在回憶蕭紅的散文里提到了這段往事:
從前那個叫做S的人,是不斷地給她身體上的折磨,像那些沒有知識的人一樣,要捶打妻子的。有一次我記得,大家都看到蕭紅眼睛的青腫,她就掩飾地說:“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傷了!” “什么跌傷的,別不要臉了!”這時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說:“我昨天喝了酒,借點酒氣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說著還揮著他那緊握的拳頭作勢,我們都不說話,覺得這恥辱該由我們男子分擔的。幸好他并沒有說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話來,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蘊滿盈盈的淚水了。(靳以《悼蕭紅和滿紅》)
蕭軍為什么要打蕭紅,有人認為是愛,一種顯示占有欲的愛。
1931年7月,蕭軍收到了女作者蕭紅的求助信,說自己懷孕但被男方拋棄了,現在被困在旅店里,如果付不出房費,會被賣去妓院。當時松花江決堤,哈爾濱市區一片汪洋,蕭軍劃著船來到蕭紅窗下,將她救出。從那之后,她愛上了他,而他稱她為“我的人”。從一開始,蕭軍就是以一種救世主的姿態占有著蕭紅這美麗而可憐的靈魂。他帶她流浪,給她治病,鼓勵她寫作,直到她頻頻發表作品,驚艷文壇,被魯迅夸為“最有潛力的作家”,他才發現,自己的羽翼已經擋不住她了。他先是貶低蕭紅的作品,說她的作品是“碎碎叨叨女人寫的東西”,后來就直接說蕭紅沒有盡到妻子的本分,“我也并不喜歡她那樣多愁善感、心高氣傲、孤芳自賞、力薄體弱的人,這是歷史的錯誤!”精神打擊還不夠,他開始明目張膽地出軌,甚至向蕭紅揮起拳頭,給予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暴力。
蕭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溫順女性,她性情剛烈,反叛了家庭,逃離過包辦婚姻,但在面對愛人的家庭暴力時,她的選擇卻是一再忍讓。她并非不知道男子為什么會使用暴力,在《生死場》中,她就以極殘酷的筆調寫過女性在婚姻中可能會遇到的家暴:
等你娶過來,她會變樣,她不和原來一樣,她的臉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會打罵她呀!
在《呼蘭河傳》中,她還諷刺過男人家暴的原因:可見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應該,神鬼齊一。怪不得那娘娘廟里的娘娘特別溫順,原來是常常挨打的緣故。可見溫順也不是怎么優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結果,甚或是招打的緣由。
也許,這也是蕭軍打她的邏輯:“我能打你,罵你,傷害你,證明了你是我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蕭紅賦予了他這種權力。她和蕭軍幾度分手,但她從未恨過他,從未放棄過對他的幻想,甚至在彌留之際,她還幻想著蕭軍的搭救:“如果三郎知道我困在這里,一定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的吧?”
奧地利詩人艾利希·傅立特曾這樣形容親密關系之間的暴力:“暴力不是開始于一個人卡住另一個人的脖子,它開始于當一個人說:我愛你,你屬于我。”
失控的權力欲:來自親子關系的暴力
家庭之中除了夫妻關系,親子關系也值得關注。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等中國傳統觀念中,孩子像是父母的私有財產,“受之于我”就要聽我處置,以至于諸多家庭打孩子的事情屢見不鮮。
打孩子算不算家暴?要看打的頻率和程度。根據2016年3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暴力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如一次性暴力毆打行為致人輕傷;多次(法律中一般將三次及三次以上視為多次)實施暴力;暴力維持了一段時間;或暴力導致家庭成員罹患了較為嚴重的身體、心理疾病等,都是界定暴力是否達到嚴重程度的判斷標準。
打孩子也不是家務事。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中第五十三條明確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在家庭教育過程中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其實,無論是對孩子實行熱暴力還是冷暴力,違法還是不違法,本質都是父母的無能,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說過:“如果家庭生活制度從一開始就得到合理的發展,處罰就不再需要了。在良好的家庭里,永遠不會有處罰的情形,這就是最正確的家庭教育道路。”仔細分析大部分家庭施于孩子的暴力,動機往往很可疑。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對準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腳,喊道:“起來,你專門給家里闖禍!”他躺在地上不肯動,哥哥很有力地連續踢著他的屁股,說:“滾起來,你作了孽還有功啦是不?”
他奇跡般站起來(在小說中,他此時已被村支部書記打了個半死),一步步倒退到墻角,站定后驚恐地看著瘦長的哥哥。哥哥憤怒地對母親說:“砸死他算了,留著也是個禍害。本來今年我還有希望去當個兵,這下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著母親。母親從來沒有打過他。母親流著眼淚走過來。他委屈地叫了一聲娘。
這段文字來自莫言的小說《枯河》,小說中那個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終是被自己的親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實的情況是:
當父親用沾了鹽水的繩子打我時,爺爺趕來解救了我。爺爺當時憤憤地說:“不就是拔了個蘿卜嘛!還用得著這樣打?”父親是好父親,母親是好母親,促使他們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為我傷了他們的自尊心,二是因為我家出身上中農,必須老老實實,才能茍且偷安。
莫言說,這段經歷來自他的故鄉、他的童年:“由于我相貌奇丑、喜歡尿床、嘴饞手懶,在家庭中是最不討人喜歡的一員,再加上生活貧困、政治壓迫使長輩們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饑餓伴隨我成長。”
盡管莫言說:“這樣的童年也許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原因吧。”但即使多年之后莫言功成名就,他對童年的傷痛依然耿耿于懷。
微博上曾有這樣一個話題調查:“你會與家暴過你的父母和解嗎?”1.8萬人參與了這個話題,1.3萬人表示不會和家暴過自己的父母和解。作家蔡康永接受采訪時被問到:“如果父母的語言暴力對自己造成了很深的傷害,可以不原諒父母嗎?”蔡康永的回答是:“我的建議不是原諒,而是算了。”也許很多人都可以像莫言那樣,把童年的家暴創傷用其他方式療愈,把缺失的父愛或母愛,寄托在其他親密關系上,然而這并不算與父母和解,頂多是算了。
心理學家阿德勒說:幸運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不要讓你的孩子,終生都困在童年里。
沈麗莎:文學愛好者
編輯??? 肖玉??? mcxiaozuoji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