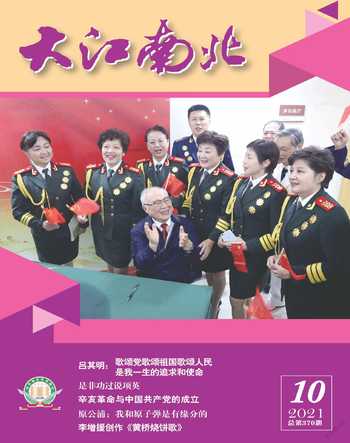紅十字人湯蠡舟與新四軍
湯章城
在孩童時,我就聽說抗日戰爭初期(1938年),父親湯蠡舟在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第三大隊大隊長、駐守江西期間,曾去過新四軍在皖南的軍部。我還見到過新四軍首長送父親的紀念品,一面繳獲的日本旗,旗上有新四軍首長的諸多簽名。
父親生前沒有與我們子女詳談自己的經歷,也沒有留下日記或自傳類的文字記錄。隨著父親的過世,他去新四軍總部的具體情況就無從知曉了。非常幸運的是,2019年上半年,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遷駐貴陽圖云關80周年之際,貴州省檔案館工作人員在3000余份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的檔案中,找到了湯蠡舟于1939年9月寫給救護總隊部林可勝總隊長的一份長達2400余字、請“代為密存”的報告,匯報自己所了解的新四軍一般狀況和衛生勤務。80年后的今天,這份報告讓我們知道了湯蠡舟這樣一位戰地醫生在新四軍中的感受。這份報告涉及三方面的內容,現摘要如下。
第一方面是新四軍的概況,涵蓋新四軍的建立和結構、作戰地區和方式、經費來源和狀況、政治工作和效果等。
“新四軍為共產黨軍之一部分,經二萬五千里長征者為八路軍,未經長征者為新四軍,於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間,由中央改編為新四軍,至二十七年一月間集中巖寺,由中央點驗即行開赴蘇浙皖之長江南岸專任游擊戰,惟該地帶,人多平原,河流交叉,深入敵后不易隱蔽不易活動,苦戰經年相當痛苦,自今春起復劃蘇皖之長江北岸歸該軍作戰,適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中,然已打成相當根基,北與八路軍互通聲氣,南與該軍密切聯絡,隨時過江并無阻礙。
該軍原分二支隊現增為六支隊,支隊下有團、營、連、排、為正規編制,每支隊少者有一團,多者有五團不等,隨活動地帶而增減,軍有軍長、副軍長,支隊有司令,團、營、連、排各有團長營長等,每月中央撥費拾叁萬捌千元不及正規軍一師之經費,人員已由萬人增至二萬七千余人,故經費非常拮據,然該軍有特殊辦法,官長士兵均吃軍米,菜錢每人每日八分,因有合作社飼養豬雞鴨及種植蔬菜等,故八分之給養較普遍隊伍為好,此外有月餉自一元五角至五元,即葉挺軍長項英副軍長亦月餉五元而已,然有正當開支,如經主管長官核準可有公費報銷,故未見如何困難,如以士兵而論其待遇實不劣于正規軍,蓋正規軍之士兵餉除伙食外,亦所得無幾也……
軍部之組織亦有政治部、參謀長、參謀處、副官處、軍醫處等等,如一般之編制外尚有敵軍工作部,專對敵軍做政治工作,全部俘虜參加該項工作,對于俘虜并不監視,反而獎勵歸營返國,惟均不愿回去而隨軍服務,俘虜常自編小品印發敵陣,并教士兵喚日語口號等,工作相當努力。”
第二方面主要反映了新四軍內和諧的官兵關系,軍中的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艱苦環境下的自力更生精神等。
“全軍之官長士兵如同家人,即名稱亦有不同如通訊兵為通訊員,飼養兵(馬夫)為飼養員,炊事兵為炊事員等等,除副官而外,無官一例統稱同志,同志原無大小也,據稱最初成立時,士兵對官長并無立正舉手之敬禮,現在積極正規化已有相當成效。
新四軍之口號為一面抗戰,一面建軍,故于教育特別注意在中村(原在中村鎮因被炸已散在附近村落)設有教導隊,大隊長馮某為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攻惠州后升任連長即派赴德法學習步炮兵有十年之久,歸國后即在八路軍身經數十戰,現掌該軍教育……
文化課中包(含)自然科學及歷史、地理、生理、衛生等,政治課程不限于共產主義包涵一切社會科學及其它之政治問題,軍事則側重于步兵作戰,教育方法為啟發式除授課外有小組討論會及壁報等提倡自動的研究。
該軍經費如此拮據而尚能設立修械廠一所,不特能修理更能自造步槍,全用手工,每月能制數十枝,外表較粗而能連射八十發,甚耐用而射擊亦正確,不惡于機器制品,印刷所一所能鉛印、石印更能鑄字,造紙版,所缺者銅板而已,該軍宣傳品周刊、月刊及各種教本等均自行排印,紙張則將該地所出之宣紙改良,仿造,白報紙,亦能兩面印字價廉合用……
湯蠡舟作為一名醫生,他當然更加關注新四軍的醫療衛生情況。因而,在報告的第三方面,用了較多的筆墨描述了新四軍的軍醫結構、醫護訓練、醫療設備、官兵健康和實際困難等等。
“軍醫處處長沈其震、醫務科科長崔院長(后方醫院)兼材料科科長胡醫師(后方醫院醫師)兼衛生科長,每一支隊有醫師一人,等於師部軍醫處處長兼野戰醫院院長(在新四軍稱前方醫院)。現在前方醫院只有一所在云嶺,新設一所擬推進至江北,每一醫院只有醫師一人女護士數人其他均為該軍訓練之衛生員與小鬼(下面說明)而已,軍隊中以連為單位,連有連衛生員,營有營衛生員,掌理各該單位醫務及衛生事宜。
軍醫處內有衛生員訓練班,由軍醫處之醫師護士為教官,學員由各部隊選送及招考而來,訓練六個月,三個月專授解剖、生理、病理、藥物、細菌、內科、外科、護病、環境衛生等,后三個月分發各醫院半工半讀,畢業后派至各部隊為衛生員。
軍醫院中之看護及衛生員之助手均為小鬼,所謂小鬼者收養十三四歲之男孩分發各處半工半讀,授以文化、衛生、政治三課,其教育方法與教導隊同,一二年后均有相當知識,并有特殊之認識,工作非常努力,并且各事均是自動,毫無勉強之處,各人對于小鬼并不以小鬼目之呼為小鬼,而實以小同志目之,實為共產黨軍特有之制度。
對于游擊戰之衛生勤務,該軍亦無特殊研究特殊辦法不過隨時隨地之應付而已,某種應付并不適用於一般之軍隊,總之該軍之醫師極度缺乏,雖能在如此環境之下自己訓練衛生員專為該軍所用,已屬難能可貴者也。”
這份報告通篇留下了湯蠡舟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的真實寫照,充滿了贊許之詞。實際上,還有一些史料證明,在此以前,湯蠡舟已經與共產黨有所接觸。
1936年6月,紅十字會(上海)救護委員會成立,湯蠡舟是執行委員之一。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上海成立了各類抗日救亡團體40多個,其中設有共產黨地下黨支部的煤業救護隊人數最多、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為便于開展救護活動,煤業救護隊與紅十字會取得聯系,并改稱“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從紅十字會登記領取所需汽油和汽車修理經費。當年底,為加速從已成為“孤島”的上海租界中外運傷兵,紅十字會和煤業公會決定將煤業救護隊和紅十字會的接運站合并,仍沿用“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交通股”的名稱。救護車輛統一刷印“紅十字會交通股”字樣及紅十字徽記。

此時,湯蠡舟已經從上海帶領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重傷醫院醫護人員西撤至武漢,并擔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委員會中路西線第十四隊隊長。1938年初,先后在寧波龍華寺和翰香小學,參與建立“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交通股傷兵接收站”。由于上海四周陸路已經被日軍封鎖,留在上海租界內的數千名傷兵只得通過水路,用外輪全部順利遣送內地。后來,由共產黨員帶領的上海煤業救護隊100多人,帶著20多輛救護汽車,在南昌集體參加了新四軍。交通股第一組組長,共產黨員樂時鳴回憶道:“駐南昌的紅十字會醫療大隊長湯蠡舟,原是上海東南醫學院醫務長,也從上海來,我們的關系處得很好。”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第15醫療隊、第61醫務隊的趙興讓先生回憶:1938年下半年,日寇九路圍攻晉東南八路軍抗日根據地,朱德總司令電告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長林可勝博士,請求派醫療隊前去為傷病員做醫療防疫工作。醫務人員紛紛報名,共批準36人,我是其中的一員。總隊部在啟程前,由湯蠡舟教授召集全體成員講話,他對這支醫療隊的組成作了說明,勉勵大家不辭勞苦去完成這一光榮使命。他指著一幅中國地圖說,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軍根據地,生活上艱苦,路途上還要闖過“三關”,那就是“夜闖潼關”“偷渡黃河”“翻越中條”,才能勝利地到達目的地——晉東南八路軍總部,大家都是中華兒女、不甘做亡國奴的青年醫務工作者,這正是報效祖國的大好機會,愿與諸位共勉之。大家都表示一定完成偉大的使命。
1939年秋,湯蠡舟從新四軍總部回到第三大隊部后,繼續支持新四軍的戰地救護工作。1939年底或1940年初,就有三大隊第6中隊第67醫療隊醫護人員在安徽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醫院工作。2月,該組又增加人數,并隨同該院推進至繁昌。4月,第67隊有一支人員隨新四軍醫院進抵銅陵三條沖附近工作,忽于24日在何家灣被敵包圍,經三日夜苦斗,始得隨軍沖出重圍,復經三日夜急行軍,才得以返回繁昌。
后來,湯蠡舟又分別擔任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醫務處長、救護總隊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總隊長及第三任總隊長。解放戰爭初,他辭去了國民政府衛生部司長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秘書長等職務,拒絕隨遷臺灣,回到他參與創建的上海私立東南醫學院,繼續從事醫學教育和醫務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12月28日,《解放日報》的醒目標題“走向內地面對農村 東南醫學院遷懷遠 今晨全體師生員工專車離滬”的消息。文中寫道“本市私立東南醫學院響應六大任務號召,在人民政府鼓勵和協助下,內遷安徽懷遠。全校師生員工教職員眷屬及附屬醫院醫師職工五百余人,已在今晨零時四十五分搭乘專車離滬”。文中還提及“附屬醫院湯蠡舟院長在暑期中與華東衛生當局負責人談及今后醫學教育及事業的方針,認為面向廣大農村去發展是一條新的康莊大道”。
1957年10月,父親去世,在“安徽各界集會追悼湯蠡舟先生”的會上,安徽省副省長陸學斌在悼詞中指出,湯蠡舟這種追求進步的精神,這種靠攏黨,接受黨的領導的精神,這種認真進行自我改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獻出更多力量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學習的。
(編輯 易 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