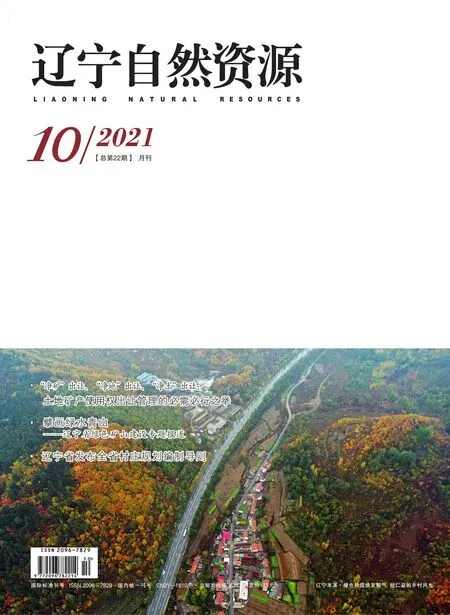國家公園,來了!
2021年10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宣布,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保護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涵蓋近30%的陸域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這標志著我國在推進自然生態保護、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自2013年11月黨中央首次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8年來,中國的國家公園逐漸有了清晰的樣貌。
為什么建?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并將其作為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
為什么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提出建立國家公園?在清華大學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楊銳看來,需要從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兩方面追根溯源。
1956年,我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建立,半個多世紀以來,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濕地公園等各級各類保護地已有近萬處,占陸域國土面積的18%,在保護自然資源和野生動植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績不小,問題卻也不少。“九龍治水”是最典型也是最具有共性的一個難題:常常在同一區域內,存在著環保、建設、林業、國土、旅游等多個主管部門。
“因為多頭管理,有的地方出現了保護地上又建保護地的情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管理目標的不一致又導致了管理不夠系統、科學,區域割裂嚴重,自然保護地有數量、缺質量,保護成效低下。”楊銳表示,進入生態文明時代,設立國家公園既能補償中國長期在生態保護上面的歷史欠賬,更從根本上扭轉了自然保護的被動局面。
黨的十九大將“美麗”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一起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目標體系中。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加優美、健康的生態環境,建立國家公園是一種理想的模式。
“此時建立國家公園是黨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作出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楊銳表示。
中國實行國家公園體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安全屏障,給子孫后代留下珍貴的自然資產。對此,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調查規劃設計院副院長唐小平感受頗深:“國家公園的理念,是將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突出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嚴格保護、整體保護、系統保護。比如建立東北虎豹國家公園,是為了保護東北虎豹傘護的整個生態系統,而這種頂級物種群落的生態保護,靠以前小范圍的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等是無法完成的。”
自1872年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公園誕生,國家公園已經走過了上百年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那能直接抄“國際作業”嗎?
“我們提出建設國家公園才不到1 0年時間,肯定是要向國際取經,但是學到一定程度,基于不同的國情,更多的還是要靠自己去探索。”唐小平告訴記者,我國人口眾多、土地權屬復雜的國情,生態保護的緊迫性,都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之路。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先后7次專題研究國家公園,相繼出臺了《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關于統一規范國家公園管理機構設置的指導意見》等8份重要改革文件。2018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組建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加掛國家公園管理局牌子,負責統一監督管理國家公園等各類自然保護地。黨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這一系列重大安排部署,構建了我國國家公園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從2015年開始,我國啟動了三江源、東北虎豹、大熊貓等10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作,從高寒草原草甸、溫帶針闊葉混交林、中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到熱帶雨林,從西北內陸的冰川雪山到東南沿海的丹霞地貌,從冰天雪地的東北到海南的熱帶雨林,試點覆蓋了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保護著豐富多樣的野生動植物。
唐小平表示,通過體制試點,總結一些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上升為頂層設計,為下一步建設更多的國家公園做了準備。
怎么管理?
中央的改革從加強頂層設計開始。而地方的創新,則在摸著石頭過河中產生。
理順管理體制,解決“九龍治水”,是改革試點的首要任務。
以前,一個三江源地區,頭上就戴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際重要濕地、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黃河源水利風景區以及自然遺產等多個“帽子”,不同的“帽子”歸不同的主管部門。
作為最早試點的三江源國家公園,將原來分散在15個管理機構的生態保護管理職責集中整合,建立了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總攬全局的管理機構,實現統一規范高效的保護管理。管理局的設立,使得三江源有了清晰、明確和統一的管理目標,改變了過去“山一家、水一家、草一家、林一家”的碎片化管理,為國家公園范圍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類自然資源的“兩統一”職責行使,奠定了基礎。
“對公園所在的瑪多、雜多、治多和曲麻萊4個縣進行大部門制改革,是三江源管理體制創新的一大亮點。”青海省林草局黨組書記、局長,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首任局長李曉南介紹,青海整合了4縣林業、國土、環保、水利、農牧等部門的生態保護管理和執法職責,設立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管理局、資源環境執法局。“
縱向,壓縮管理層級;橫向,減少管理部門,從兩個尺度上改革管理體制,實現管理效率的最大化、最優化。”李曉南表示,徹底打破“九龍治水”,是三江源國家體制試點成果的關鍵。
在距三江源2000多公里之外的武夷山,除了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牌子之外,還擁有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地、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AAAAA級旅游景區、國家水利風景區等諸多“頭銜”。
為避免政出多門,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局由福建省政府垂直管理,同時在試點區涉及的6個主要鄉鎮(街道)分別設立國家公園管理站和執法大隊,構建了縱向到底的“管理局——管理站”兩級管理體制。
在理順管理體制上,武夷山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林雅秋介紹:“管理站站長由所在地6個鄉鎮長兼任,既節省行政資源,又落實屬地責任,還能形成工作合力。”
其他的試點區也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實現了一個公園、一套機構、一塊牌子,管理體制由分散、多頭、低效向統一、垂直、高效轉變。
唐小平介紹,試點過程中各地各部門堅持將創新體制和完善機制放到優先位置,結合實際情況,分別探索了以東北虎豹試點區為代表的中央直管模式,以大熊貓和祁連山試點區為代表的中央和省級政府共同管理模式,以三江源和海南熱帶雨林試點區為代表的中央委托省級政府管理模式。
改革于法有據,保護有法可依,建設有章可循。林雅秋介紹,武夷山國家公園頒布實施了《武夷山國家公園條例(試行)》,出臺了特許經營管理暫行辦法,編制了總體規劃,以及保護、科研監測、科普教育、生態游憩、社區發展5個專項規劃,制定了11項制度12條標準,為日常管理的規范高效提供了制度支撐。
唐小平認為,試點期間,各個國家公園進行的一系列法規制度創新,都為今后制定國家公園法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怎么保護?
“過去在一些自然保護地內,自然保護常常讓位于開發利用,或者將保護與發展置于對立面。而在國家公園內,自然才是絕對的主角,生態保護必須放在第一位。”在楊銳看來,國家公園生態價值最高,保護也必須最嚴。
《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明確,國家公園是我國自然保護地最重要類型之一,屬于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的禁止開發區域,納入全國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管控范圍,實行最嚴格的保護。
“現在來到三江源,見到野生動物的概率是100%,這在十幾年前是不可能的。”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三江源國家公園研究院學術院長趙新全介紹,8.6萬多平方公里的草地,是三江源國家公園最主要的生態系統類型。只有草好了,食草動物得以快速恢復,整個草原生態鏈才能接起來。
正是在趙新全這樣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多年研究的基礎上,三江源國家公園統籌實施了生態保護工程,科學修復退化草原,三江源的草地退化趨勢得到逆轉,草地覆蓋率、產草量分別比十年前提高了11%、30%以上。作為草原生態系統的指示物種,“高原精靈”藏羚羊從建園之初的2萬多只增加到現在的7萬多只。
其他國家公園同樣收獲滿滿。
東北虎豹國家公園通過退耕退參還林,實施生態修復,恢復虎豹棲息空間,試點以來,園內東北虎豹種群穩定增長,野生東北虎新增幼虎10只,東北豹新增幼豹7只;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啟動海南長臂猿生態廊道試點建設,加強海南長臂猿棲息地保護,建設核心保護區電子圍欄和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體系,海南長臂猿從發現時的不到10只增加到5群35只;大熊貓試點區野生大熊貓適宜生境面積增加了1.6%,保存了全國野生大熊貓總數量的71.89%,受威脅程度等級從“瀕危”降為“易危”……
一個一個不斷增長的數字,一個一個紛紛“降級”的物種,證明了國家公園的成效。除了旗艦物種、指示物種的增加,一些昔日銷聲匿跡的野生動物也再度現身,還有許多植物新種不斷被發現。
如何共生?
既要實行最嚴格的保護,又要讓國家公園內的百姓得到更好發展,實現人地和諧,這也是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的探索重點之一。
保護第一,并不等于保護唯一。中國的國家公園邊界內外人口不少,試點地區又多在老少邊窮地區。楊銳認為,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才是考驗管理者智慧的真正難題。
在實地走訪三江源之后,楊銳增強了信心。國家公園不僅肩負了保護生態的重任,還統籌考慮了原住居民的生計需求,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玉樹州雜多縣昂賽鄉被譽為“雪豹之鄉”,這里是瀾滄江園區,也是雪豹最重要的棲息地之一,是眾多國內外專家、專業攝影師的向往之地。2018年,三江源國家公園率先在玉樹州昂賽鄉開展了基于社區的生態旅游特許經營試點探索,22戶牧民作為接待家庭,為自然體驗者提供食宿,并擔任向導。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社區保護顧問劉馨濃是昂賽自然體驗試點項目負責人,她告訴記者,試點第一年22戶牧民共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61個體驗團隊,總收益42萬元,最終這些收入將按照接待家庭45%、社區45%、保護基金10%的比例進行合理分配。“自然體驗雖然目前只是小范圍探索,但也顯著改善了接待家庭的生活條件。”劉馨濃表示,后續將不斷改進完善生態旅游特許經營,以促進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和地區的經濟發展。

目前,生態旅游特許經營已經在三江源、武夷山、大熊貓等國家公園邁出了嘗試性的腳步。而更多地惠及原住居民的措施,則已經普及開來。
三江源創新生態管護公益崗位,實現園區內17211戶牧民“一戶一崗”,家家有生態管護員,戶均年增收2.16萬元,實現了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的“雙贏”;武夷山國家公園除了吸納居民成為生態管護員,還通過建設生態茶園,打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道,有效拓寬村民收入;大熊貓公園設立生態公益崗位約3萬個,為當地居民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從貧困戶到護林員,從森林伐木工到巡護監測員,從草原牧民到生態管護員……曾經世代居住在此的人們,在生態保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從生態利用者到生態守護者的身份轉變,是各個國家公園探索實現人地和諧的好辦法。早在2700多年前,管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如今的國家公園,正是那個人與天調、天地大美的地方。
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展示的是國家形象,體現的是國家軟實力,是我們從祖先手中繼承下來,要真實完整地傳遞給中華民族子孫后代的。國家公園不僅是每一個國人的公園,更是每一代國人的公園。我們期待著國家公園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續載體。(i自然全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