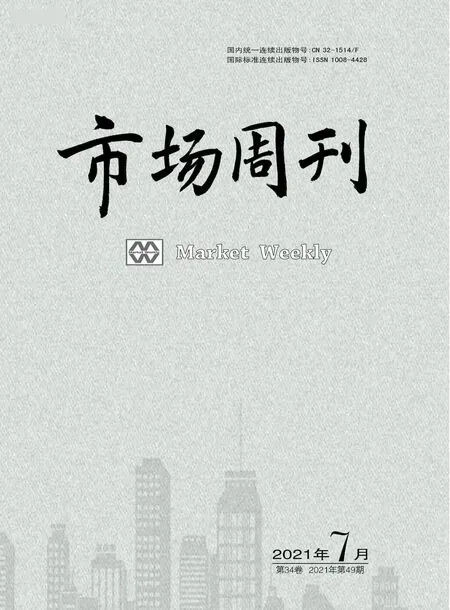淺析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適用考量
馬永剛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學院,北京100038)
一、正當防衛必要限度概述
(一)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含義
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就是指為保障合法權益不受損害,維護防衛行為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的一個量的規定。根據刑法規定①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即為超過必要限度構成防衛過當。可見,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與 “明顯超過” 和 “重大損害” 二者之間有直接關系,但是,刑法學界并沒有對其含義給出一個清晰準確的界定。
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的含義從內涵和外延的角度考慮更為恰當。首先,必要限度的內涵應是保證防衛行為合理性和正當性的核心,即阻卻不法行為,維護合法權益,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般重要,更是區分防衛行為是否有責的關鍵之鑰。其次,必要限度的外延是一個區間長度、一個最大量的規定。也就是說在整個制止不法侵害的過程中,必要限度就是既能有效阻卻不法侵害,防衛行為造成的損害又可以被接受的一個量的規定。
(二)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相關學說
關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基本標準的觀點,我國刑法學界對它的理解大致上有以下四種觀點:
1.必要說
“必要說” 主張防衛行為的必要限度是由防衛過程的客觀實際需要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只要不法侵害行為在客觀上仍有現實危險性,在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力量強弱的對比中,防衛行為的強度就不需要受限制,即超過、等于或弱于侵害行為的強度均可。
2.基本相適應說
“基本相適應說” 強調,在分析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時,主要是將防衛行為和加害行為二者的破壞力量進行權衡。這種破壞力量是指給對方造成損害或者是保護自己不被對方傷害,而這種破壞力量的參考系數就是指二者的性質、強度以及手段等。如果二者的破壞力量沒有相差很大,或者基本上相適應,那么防衛行為就是適度的、無責的。反之,就有可能屬于防衛過當。
3.折中說
“折中說” ,實際上是 “必要說” 和 “基本適應說” 二者觀點的主要思想內容的折中之意。該觀點主張在解釋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時更好地貼近了正當防衛制度的立法目的,吸收了前面兩種學說各自的優勢,即統籌考慮客觀現實需要和防衛雙方的力量對比,既能保護合法權益和制止不法加害行為,防衛行為造成的損害結果又能被法律和社會所認可,并且強調綜合全案進行分析判斷。
4.社會倫理許可的必需說
這種學說是目前關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的最新觀點。該學說實質是個人權利的保護原則和社會權利的法確證原則的融合,其主張在防衛過程中,防衛者出于正當的防衛意圖實施的防衛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能夠被社會倫理所認可,足以制止違法行為并且不違背確證法秩序,那么該行為就沒有超過必要限度。而社會倫理許可的必需說則主要是為了緩解在司法實務中涉及防衛限度的認定困境,適當放寬嚴苛的認定條件,但不是無限放任防衛權的適用,而是將其行為結果放在社會的客觀環境下,只要防衛行為造成的后果能夠被社會公序良俗、道德倫理所接受,就不構成防衛過當。
二、我國司法實踐中防衛限度的認定困境
(一)司法工作人員存在錯誤觀念
正當防衛的防衛限度的認定困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司法工作人員的錯誤觀念造成的。司法工作人員的錯誤觀念主要有唯結果論和事后評價的觀念。唯結果論是指具體的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中,司法工作人員更著重將案件的結果放在行為認定的首位,而不是對整個案件的整體進行全面考量。事后評價,俗稱 “馬后炮式判斷” ,是指司法實務部門在認定防衛行為是否超過必要限度以及制止侵害的緊迫性時,沒有站在防衛人的位置設身處地地為其考慮,以一種 “理性第三人” 的角度對防衛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進行評價。
這種觀念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司法工作人員沒有換位思考地為防衛者著想。防衛者是一個普通又平常的社會人,不是一個圣人,更不是一個活在神話世界的神仙。防衛人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充滿著極度不確定性和危險性,這樣的客觀環境若是苛求防衛者保持鎮定,泰然處之,并且能夠冷靜分析該如何采取防衛措施以及如何使防衛手段的強度恰好合乎法律法規的要求,那么將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二)司法實踐認定標準模糊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知無論是刑事立法方面,還是在刑法學界都沒有對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的含義作出統一和明確的界定。因此,在具體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來界定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這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關于限度的認定模糊的困境的表現之一就是在武器不對等的情形下的同案不同判,即對于情形相類似的案件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近年來多起引起廣泛關注的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中,由于沒有清晰的限度條件認定的標準,一審法院經審查往往做出不適當的司法裁判。
(三)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不一致
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往往總能牽動社會敏感的神經,一旦加害人在防衛過程中出現重傷甚至死亡的情形,其親屬往往抱著 “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 的心態 “尋求政府主持公道” 。這樣的情形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威脅社會的和諧穩定。但如果徇私枉法,不尊重事實,將原本屬于正當防衛的防衛行為認定為具有危害性質的過當行為,同樣也違反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也失去了法律所應發揮的價值和效果。在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二者之間進行權衡,不能顧此失彼。如果僅僅是為了追求社會效果,而忽略了法律的基本精神,純粹地為了維護社會大局和諧穩定,那么在出現重傷、死亡后果的防衛案件中,法官偏向于將本該評價為正當防衛的行為評價為防衛過當。
三、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認定的完善
正當防衛制度設立的初衷是從立法的角度鼓勵公民與不法侵害行為做斗爭,不做沉默的羔羊。但是,該如何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值得司法界和普通民眾共同去深思。我們要用好正當防衛制度,喚醒 “沉睡的條款” ,最重要的就是對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認定的完善:
(一)更新司法觀念
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對于防衛限度的認定問題在思想上存在著許多陳舊落后的觀念,比如唯結果論的觀念、 “馬后炮式評價” 觀念、 “圣人標準” 的觀念、 “息事寧人” 的觀念等。這些觀念桎梏了司法人員對防衛限度的界定,不僅沒有創造良好的社會效果,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損司法的公正。為此,司法工作人員在處理涉及正當防衛制度的案件時不應當只是看到案件中出現的重傷甚至死亡的結果,還要看到與之相對應的行為,踐行行為到結果的分析判斷路徑,而不是本末倒置地通過結果分析行為。同時,兩者要兼顧,不能顧此失彼,即行為特征和結果程度兩個方面綜合判斷,二者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以普通社會人的角度看待防衛人,不能將案發時的防衛人看成是一個 “理性第三人” ,更要摒棄 “圣人論” 的標準。
司法工作人員的作用就是使得傾斜的天平趨于平衡,不使天平過多傾向于傳統思潮指向的所謂的社會 “弱方” 。如若不然,則會束縛防衛人的手腳,不利于對合法權益的保障。
(二)明確認定標準
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之所以會 “逢案必爭” ,主要在于正當防衛的案件如萬花筒般多樣又復雜,在司法實踐中很難找到普遍適用的關于必要限度的認定標準。為解決這種司法實踐的困境,筆者認為在界定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時,應當采納社會倫理許可的必需說的觀點,并引入二元論的比例性和必要性標準。
比例性標準是指在防衛過程中權衡防衛雙方的力量,使雙方不至于大比例地失調。這種力量的權衡不僅是防衛者個人權利保護原則的體現,同時也是法秩序確認原則所維護的從全體社會成員角度出發的社會利益。比例性標準所規定的雙方的行為包括高強度的行為和低強度的行為。高強度的行為是指對人身權益造成不可逆的危害的行為,如用刀具或斧頭將對方砍成重傷甚至造成對方死亡等,而低強度行為指的是經過彌補補償可以恢復的行為,如損害他人的財產性權益、人格名譽權等。如果防衛雙方二者的行為強度大體相當,那么就滿足了比例性標準的要求。必要性標準是為滿足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觀需要,防衛者有多種行之有效的防衛措施時可以實施時,防衛者應該選擇比較緩和的防衛措施保護合法權益,不能采取過于激烈的方式以制止不法侵害,如小偷甲在大街上正準備伸手偷走屠夫乙的現金,乙不能直接就用菜刀將甲手指頭剁下來。在司法實踐中,只要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能夠同時達到比例性標準和必要性標準的條件,就應該認定該案件不存在防衛過當。
(三)制定專門司法解釋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正逐步根據實際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選擇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案件作為指導案例,明確不同類型正當防衛案件的具體實踐標準,制定專門的司法解釋,使得各級法院在遇到類似正當防衛的案件時能夠有章可循,有案可鑒。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2020年9月印發的《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各級法院在審理關于正當防衛的案件時,要認識到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是一個區間段,而不是一個孤立的點,要運用整體的視角,堅持主客觀一致,堅持行為特征和結果特征兼顧,既要看到局部的一點,又要注重整體的效果。各級法院在司法實踐當中,看一個行為,不能夠孤立地,或者說割裂地把一個行為單獨放大來看,否則,就對當時行使正當防衛權利的人過于苛刻了,因此,必須聯系整個案件事實,綜合全局來分析,才不至于失之偏頗。
四、結論
只有在司法實踐中真正合理地適用正當防衛制度,才能真正發揮其真正的法律價值和社會價值。對于界定防衛限度的爭議問題,學術上百家爭鳴自然會推動理論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需要有統一清晰的標準解決具體問題。因此,筆者建議防衛限度的界定標準應當采用二元論的 “比例性標準” 和 “必要性標準” ,以解決在司法實踐中限度問題的認定困境。同時,不斷提升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擺脫陳舊觀念的困擾,不斷接納新的觀點和學說,就具體案件而言,試著傾聽來自不同觀點的聲音,敢于作出 “正當防衛” 的結論。此外,司法機關應該就正當防衛的條款及相關案件作出明確解釋,尤其是涉及典型案件、典型困境的認定問題,發布更多的指導性案例,使得各級司法機關有章可循,準確界定,從而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刑法學界的不斷開拓與前進,正當防衛制度一定能夠更好地保護合法權益,為經濟社會的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