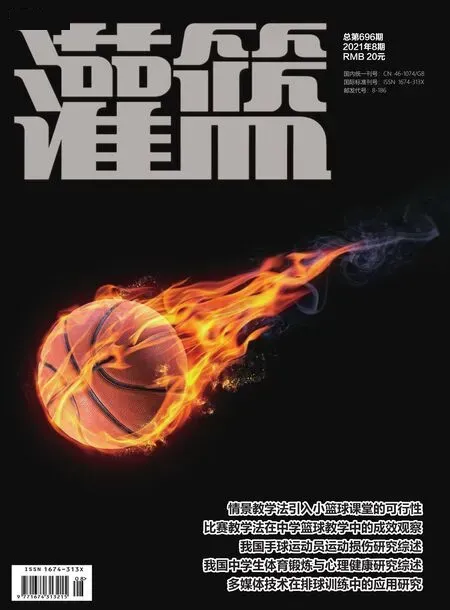參與式文化視角下社交媒體平臺中“體育迷群”的內容生產分析
李晨顏 山東師范大學
一、概念界定與研究方法
(一)“參與式文化”理論
在20世紀媒介技術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美國著名的傳播與媒介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他著名的《文本盜獵者:電視迷與參與式文化》一書中提出并深入探討了“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這一概念。參與式文化最早起源于迷社群,基于媒介技術的賦權,是一個普通受眾對流行文化進行解讀、評價、挪用、再創作、再傳播等行為的過程。受眾由以往的內容消費者轉身一變為內容生產者。[1]現在已經形成了以普通受眾為主體,以Web2.0時代誕生的社交媒體平臺為載體,積極創作媒介文本、評價媒介內容、強化虛擬社交為主要形式的一種新型媒介文化樣式。
(二)“體育迷群”
隨著國家號召全民健身、各種體育賽事在我國的舉辦,體育運動日漸成為大眾娛樂消遣的主要途徑。在一般的體育觀眾中,部分“迷”個體之間基于群體認同會組織一系列線上線下的交流與活動,這些人來自于體育觀眾但是又更具有認同感、組織性,他們會形成一種全新的群體組織——體育迷群。與一般的體育觀眾相比,他們樂于建立基于愛好的網絡團體,體育迷群對于他們關注的賽事、球隊、球員會有更強烈的情感態度,基于身份認同形成的群體更傾向于進行內容生產。
由于時間、地理和經濟原因,體育迷通常只能借助媒介關注喜歡的球隊、運動項目、運動員的相關信息。他們更像是生活在媒介化社會中的“電子體育迷”或“數字粉絲”,利用虛擬空間與偶像及其他體育迷互動交流。“大眾文化迷會把他們的著迷行為轉為生產力,激勵著他們生產屬于自己的文本”[2]。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使傳統的“球迷”有了新的消費與生產內容的渠道。
二、參與和創造:社交媒體中“體育迷群”的內容生產
(一)內容形式多樣 傳播渠道多元
技術的發展降低了為用戶生產內容的門檻,“體育迷群”在社會化媒體中生產的內容極具個人化風格。媒介素養的加持使一些較年輕球迷的媒介接觸行為更多元、更提前,內容生產呈現出高度專業化的狀態,具有較高的觀賞性和傳播性。此外,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和開放性,使“體育迷”生產的內容也有協作包容性,即便是技術能力較差的用戶,也可以通過評論、點贊等形式呈現自我與表達情感。
通過多樣化內容的生產,迷群的關注重心不再只局限于原先只看場上表現、鮮亮外形等事業層面,關注焦點更多元,有利于運動員塑造立體形象,從而從今體育粉絲經濟的興起。體育迷們能夠在內容生產者獲得群體身份認同,有利于個體在圈子內部進行交流與互動。
(二)生產內容含義多元
“體育迷群”在社交媒體中生產的內容含義具有多元性。不同的個體對內容的理解不同,這些不同可以幫助粉絲表達對體育運動或與動員的喜愛,也可以保持粉絲群體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在意象和情感投射的幫助下,粉絲構建了自己的意義。[3]值得注意的是,體育迷對“技術”的分析正在興起,尤其是在運動員的賽事得分統計和裁判判罰時,這層面的內容生產最多。
(三)生產內容獲得普遍認同
在開放自由的社交媒體中,體育迷的身份具有多樣化,他們基于同一個目標和愛好聚集在一個群體當中。當下很多的體育迷已經不再是為了滿足自己、娛樂自己去生產內容,而是已經成為工作室、官方媒體采用的內容。體育迷制作的“出圈”內容比比皆是,各大官方媒體傾向于通過轉載、點贊的形式來調動體育迷的積極性,從而提升自身賬號的影響力和傳播力。
三、認同與凝聚“體育迷群”內容生產動機
(一)獲取認同 融入迷群
根據詹金斯所言,粉絲之所以有較強的活躍度是由于“喜歡和彼此在一起的感覺,喜歡共享的這份熱情”。[4]傳統媒體時代,球迷更多是坐在電視機前觀看賽事直播,是單向的內容消費者。而在社交媒體時代,球迷身份更加多元,是內容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統一體,并且通過內容生產來獲得群體身份認同,提高群體認同感與凝聚力成為體育迷的首要動機。他們雖然也消費內容,但更多的是作為主動的內容生產者,想要融入群體。
在社交媒體時代,媒介早已超越了信息交流的基本功能,正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重構人們的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識形態,因此在虛擬社群中獲得身份認同,有助于其在社群中的生存與發展。
(二)提升地位 號召迷群
在“體育迷群”中,“迷”個體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職業和地位都無法決定他們在圈子中的地位。生成海報、分享圖片、制作視頻這些運用專業技術生產的內容,成為吸引關注和提升社群地位的最佳方法。“迷”個體生產高質量的視頻和圖片,制作精美的海報和壁紙,使其他無法擁有此項技能的粉絲投來羨慕的眼光,從而提升其在迷群中的地位,獲得別人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號召迷群的權力。
此外,體育場域一直對女性粉絲存在“刻板印象”,認為女粉絲只注重運動員的外形、不懂技術,是一種“偽粉絲”。但隨著女性粉絲在社交媒體中生產的內容獲得社群認可后,體育“迷妹”在體育場域內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完成了一種從“被看”到“看”的轉變,女性體育迷群通過自身的內容生產行為,逐步提升自身的地位,甚至成為“體育迷群”中的“核心粉絲”。凡是在迷群中獲得一定地位的人,他們會進行穩定的內容創作與輸出,來維持或提升其在社群中的地位,獲得更多粉絲的追捧。
(三)自我呈現 建構迷群
通常粉絲會利用大眾文化中的形象,建構自己的文化和社會身份,通過這種行為表達自己在主流媒體中無法得到反饋的想法和建議。普通的內容生產無法滿足普遍粉絲的需求,這時候的粉絲需要借助情感機制,積極主動地生產屬于自己的獨特意義。在“體育迷群”中,比賽是體育粉絲生產內容和資源和靈感。但隨著體育的娛樂化轉向,運動員的場下生活、綜藝節目、采訪等行程成為粉絲們進行“文本盜獵”二次創作的主要來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賽事本身給觀眾帶來的意義。粉絲通過內容生產來呈現自我的想象,從而進一步建構社群的想象共同體。
四、結語
隨著新型媒介的興起,體育迷由單純的內容消費者轉變為主動的內容生產者;隨著媒介的變革與發展,“體育迷群”的內容生產行為也在隨之變化,呈現出由“文本盜獵”向“自主創作”的轉向。[5]但是,自由的內容生產并不意味著肆意宣泄情緒、利用群體地位引導輿論。“體育迷群”自身應該具備一套合規的內容限制機制,社會化媒體也應當加強平臺管理與監視,還需要政府的介入,早日完善互聯網相關制度,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